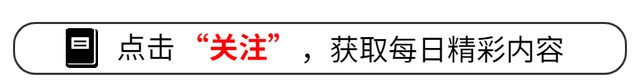

文|伊力瞎掰
编辑| 伊力瞎掰

●—≺ 里与聚落的关系 ≻—●
关于秦汉时期县下“乡里”族居的一般形态,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是“聚族里居”。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群体维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并具有十分强烈的延续性。

即使春秋战国以来实行日趋严密的户籍制和乡里制,因乡里制与旧聚落叠合在一起,并没有破坏原有的血缘性联系,宗族聚居的习惯也并未改变。
秦汉出土不少以姓氏命名的里,是过去血缘性聚落的遗留,汉侍廷里父老僤于姓约占40%,这对宗族聚居一里做了十分有力的证明。

另一种观点是 “里中多姓杂居”,战国秦汉以来的乡里,作为地域性行政组织,不断瓦解和消除原来的血缘亲族关系对集权政治的抵制力,新的非亲缘性社会关系得以强化。
里内大小的同姓宗族与没有宗族背景的单姓家族并存,无论是里耶秦简 “南阳里户籍简”、居延汉简“吏卒名籍”,还是“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其中记录的姓氏,均表明一里之中多姓杂居。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有二:一是对里与聚落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里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在原有聚落之上加上的新编组,里中仍然维持着原有的血缘联系。
后者将战国秦汉时期的里视作最基层的行政地理区域与居民行政组织,不断打破原聚落中的血缘亲族组织,里中居民成分混杂,异姓杂处,逐渐失去了血缘集团的特性。

二是对里中族姓家户在定性、定量上有不同的分析,前者关注大姓在里中所占比重,以一姓户数的多寡来衡量族居形态。
后者重视里中姓氏的数量,以多个姓氏的共存来否定聚族里居的形态,对里中大姓的存在却有所忽视。

分析、论证秦汉时期的族居形态,不仅要理清里与自然聚落的关系,也要制定聚族里居的标准。
只是,从目前的秦汉史料来看,里与自然聚落的关系,仍缺乏明确而有力的直接例证。

至于聚族里居的标准,当然不能仅以姓氏的个数作为衡量标准,大姓户数占里总户数的比重,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定性标准。
既然常以东汉侍廷里父老僵于姓家户,占比40%来衡量聚族而居的形态,就以此作为聚族而居的基准。
即一里之中,如果大姓户数占比 40%以上,就庶几可以反映大姓聚族里居的形态。


●—≺ 秦汉基层的族居形态 ≻—●
里耶古城北护城壕出土的迁陵县南阳里户籍简牍,经整理拼复缀合,得整简10枚,残简14枚(段),其中有10枚可释读户人姓氏,共计8个姓氏:黄姓3 户,其他7个姓氏均只有1户。
秦代一里户数约30户左右,可释读姓氏的南阳里户籍简遗存约1/3,这对里中族姓的统计会有影响。

一般而言,户数保留越少,族姓户数占比会相对偏高,即使如此,该里首姓黄姓也仅占可释读姓氏户数的30% (实际占比应低一些)。
由此约略可窥知,秦代迁陵县南阳里应当是多个族姓杂居,且大姓家户不占绝对多数。

江陵凤凰山10号西汉墓,二号木“记钱人名簿”,和东汉“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为考察汉代里中的族居形态提供了线索。
凤凰山汉简“记钱人名簿”记录了18个姓名,包括16位出钱者和2位“不予者”。
记录“不予者”,表明该牍应当悉数记录了某个群体,目前倾向于该牍的性质为“膊照名籍”,记录了墓主张偃所在的平里的全部家户 (包括张偃共计19户)。

根据岳麓秦简“识劫媲案”的记录,“里人不幸死者出单赋”,凤凰山汉简“记钱人名簿”的性质应与此类似。
如果墓主张偃所在的平里有“单”的存在,甚至设置可能与生死有关的“万岁单”“长寿单”,该牍所记的 18 个姓名有可能是这类“单”中其他家户的全记录。

不过,考虑到“单”的约束性比较强 (参“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出现“不予者”的可能性很低。
再者,张像生前担任里正,在地方上较有权势,“记钱人名簿”也有可能是平里人户的全记录,这也是学界的主流意见。

同墓所出“郑里原簿”记录的25户,可能就是郑里的户数,两里的户数相差不多,或可大致印证。
无论如何,凤凰山汉简“记钱人名簿”所记之姓名,能反映西汉文景之际江陵县下“里”或“单”的族居形态。

按学界的主流意见,平里当时19户,张姓4户(含张偃),王姓2户,其他姓氏仅1户。首姓张姓约占平里总户数的21.1%,远不足聚族而居的基准40%。
由此看来,西汉前期江陵平里应为“多姓均势杂居”形态,东汉建初二年“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具体铭刻了结“僤”的25人姓名。

25 户中于姓10户,单、尹、铸、周姓3户,左姓2户,丘姓1户,首姓于姓户数约占侍廷里父老佩家户的40%。
不过,这还难以直接作为东汉聚族里居的证据。据券文“即僵中皆些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侍廷里父老不一定由这些结佩之人出任,说明这 25 户只是侍廷里中的部分民户。


●—≺ 姓氏与平民族姓观念 ≻—●
秦汉三国碑简文献显示,乡里编户民“多姓均势杂居”,这一族居形态,不同于以往学界所认识的“聚族里居”或“里中多姓杂居”。
不仅如此,秦汉官文书中普遍书写编户民的姓氏,与西周以降很长时期内姓氏乃政治权力的符号,为统治集团所有而不为平民所得,也是不可同年而论的。

秦汉乡里编户民“多姓均势杂居”与姓氏的演变、王朝权力的规划应当有着密切的关系,兹予以申论。
西周利用本为血缘符号的姓氏为政治统治服务,将姓氏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并用来酬庸报功,以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左传》 隐公八年载: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周代姓氏来源于天子的“赐”“命”以及诸侯的“字”,象征着政治权力的分封与宗法的继承。
至于世代功勋卓著者,则以官名、邑名为氏 (族),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等级制度日益崩坏,下陵上替,姓氏不再为统治集团所独有,平民逐渐普及姓氏。

氏、族也从为宗法制度服务的政治符号逐渐演变为社会性符号,向血缘组织的标识重新回归。
事实上,平民得姓不仅是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巨变的结果,也有王朝权力的推动。

在秦王政十八年“识劫嫌案”中,所涉及的吏民皆只记“名”而不记“姓”,而且“宗人”的作证并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这似乎表明,此时秦的基层统治尚未全面利用族姓管控编户民,也未全面利用宗族作为治民的有效手段。


●—≺ 多姓均势杂居 ≻—●
般而言,自然聚落如果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随着人口的繁衍,在安土重迁的习俗和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聚落中的民户将逐渐发展为族姓聚居。
然而,秦汉乡里出现编户民“多姓均势杂居”,其族姓观念和宗族意识也很淡薄,这应当是国家权力介入、强制离散自然聚落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乡里制发挥若重要作用,秦汉乡里制是官方管控编户民和基层社会的行政工具,对基层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形塑”作用。
削弱地缘和血缘关系,摧折民间的自治权力,实现官方对编户民直接的控制和加强集权是其重要的功能。

秦汉“乡”“里”的组织原则和依据主要是户口数量,并随着户口的增减而不断进行调整。
“诸故同里里门而别为数里者”意味着秦曾析分里,可能是在原来自然聚落色彩仍然浓厚的旧里的基础上编制新里。

此新律则规定,原来析分之里又重新整合为一里。这并非全然对里的地缘关系的重新认可。
据“一里过百而可隔垣益为门者,分以为二里”,独立的户口众多的里依然要被拆分,将里的户数限制在百户以下。户数成为秦反复拆并里和聚邑的基准。

秦汉时期乡里平民“多姓均势杂居”的延续性和普遍性,与这一时期爵制、分异令、乡里制等的长期坚持密不可分。
秦汉以来,爵制先后规定五大夫或公乘以下的吏民比地为伍,县下之乡里只是底民群体的编伍,庶民宗族发育程度很低,难以发展成为大姓冠族。

乡里制在离散自然聚落的血缘、地缘等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乡和里的制度性反复拆并,不断离散长期以来维系自然聚落的血缘、地缘纽带,在排折乡里大姓的同时,努力营造乡里“多姓均势杂居”的形态。

不过,诸如秦迁陵县启陵乡诸里、西汉长沙国箭道波里那样,割裂和迁移丘落或乡里中的居民,在其他地域营造新的乡里或与他里合并,这类做法并不利于基层的稳定。
从吴简展现的情形来看,里可能主要作为形式上甚或是虚拟的分割单元,仅在文书层面,将丘落邑聚中的吏民分散地登记在,不同的乡里户籍之上,事实上却存在族姓聚居在丘落邑聚的状态。

东汉以后,乡里制离散聚落和族姓越来越形式化,以豪强为代表的宗族势力迅速发展,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
这时官方不得不转而招抚和利用地方宗族势力,或者将权势者及其组织纳入地方行政系统,或从思想层面主导宗族观念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