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别鹤近来新包养了一位北影的女学生。
女孩儿前卫摩登,喜欢趴在沈别鹤的膝盖上叫daddy。
爱至欲死之际,沈别鹤更是以她的名字捐了个金身佛像。
碰到同样虔心跪在佛坛的我。
女孩儿眉目张扬,挥手把我苦苦求来的护身符踩烂。
我笑。
也好,踩烂了也好。
这样我或许能死的更快了。

1
平安符摔落的瞬间。
我的心也跟着停拍了一秒。
那里面有块玉,是我妈生前留给我的。
寺庙的师傅说。
「要想符咒灵验,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放在里面,磕满三千个台阶即可。」
被癌症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我,没有犹豫。
因为我想要活下去,无论沈别鹤如何待我,我还是想要为他活下去。
可当我看到周幼京嫌弃不过瘾。
十厘米的水钻高跟朝着平安符狠狠碾压旋转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一切都没了意义。
包裹在里面的玉石传来咔嚓破碎的声音。
周幼京居高临下的看着我。
「这小小的破符有什么作用,不如沈先生,为我捐金身佛像的大功德。」
傲慢的态度,引得住持师傅先沉了脸。
「周小姐莫不要在这佛门境地中放肆,佛祖何来大小功德之分。」
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
大家不言而喻都朝正中央的话事人身上看了去。
沈别鹤神色寡淡,一双单薄的桃花眼敛去了所有的七情六欲。
他手轻轻一挥,跟在他身后的助理立马把西装外套披在了他的肩上。
「不过就是个符而已,这么上纲上线做什么。」
「更何况,我夫人一向有容乃大,一定不会跟幼京生气的」
他微笑的朝我望来。
好似我额头因为不断叩首而血迹斑斑的伤痕只是摆设。
寒侵心骨。
二月的京市下了茫茫大雪。
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不远处的姻缘树站了一对少年人。
男孩把一根红色丝带悬挂于枝头。
「阿酒,从前我们便算是在佛前发了誓。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就算百年归西之后还有下一个白年。」
「嗯!百年之后还有下一个百年!」
我弯腰咳嗽。
咳得双眼通红,嗓中冒血。
我忽然很想知道,如果有天沈别鹤知道,她摔的那个平安符。
会让我的生命终结在此年。
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2
那天黄昏,是保姆阿珍过来接的我。
看到我的瞬间,她便落了泪。
「怎么会这样……沈先生怎么会这样……」
她擦着眼角的泪,无措的呐呐自语。
不仅是她,沈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想不通。
从前沈先生多爱夫人啊。
爱到铭心彻骨。
爱到恐不消融天地万物的赤忱。
但自从三年前,两人在深夜大吵一架后,就什么都变了。
如今,夫人病入膏肓,先生竟然都还不知道。
阿珍握着我见骨的手腕,泪水涟涟。
我叹了口气,唤她去给我倒杯温水。
水还没到,极度疲倦之下的我,先睡了过去。
醒来后,窗台伫立着一个挺拔的人影。
我知道是谁,裹着被子,翻了个身。
沈别鹤咬了支烟,将长久注视的目光移开。
语气不咸不淡:「回来拿个文件。」
「嗯。」我有气无力从嗓子眼应了句声。
「幼京今天的事我替她向你道个歉,符我给你捡回来了,放在客厅了。」
「谢谢。」我没任何话想说。
空气静默一瞬。
沈别鹤垂头,指尖在烟头揉搓几下。
火星灭了。
烫人的高温,他仿佛毫无知觉。
他抬脚往门口走了几步,却又没了声响。
我心中疑惑,突然一股蛮力径直将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视线顿时被他生硬的正脸占据。
「梁酒,你他妈服个软会死?」
我极少看到沈别鹤骂人的样子。
记忆中,他好像永远是高岭之花的样子。
苍白冷淡,最气的时候也不过是独自站在一边忍耐。
直到自己消化完之后再和我说:「阿酒,你就是欺负我喜欢你。」
我曾经爱惨了他这幅模样。
所以此刻我才觉得心寒的陌生。
「沈别鹤,我服过软。这两年来,无数次,没有自尊,没有底线。可是有用吗?没用。」
黑暗之中,我们静静注视。
彼此眼中,都有痛苦的神色。
「阿酒,最后一次。」
「周幼京在楼下等我,只要你再向我保证一次,我马上就让她滚蛋。」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要了,沈别鹤,我不爱你了。」
寒意迅速的攀延进他的眼底。
一寸一寸,直到坚硬的再也照不进一丝光亮。
沈别鹤慢慢起身。
整理了一下领带,扯出我最为熟悉的漠笑:「梁酒,你不要后悔。」
说完,他转身离去。
我在窗户旁看见他快步走到周幼京面前。
周幼京本来还有点不开心,嘟着嘴朝他撒娇。
拉扯间,两人热吻。
我看了一会,起身走到电脑面前,开始写离婚协议书。

3
但我写到一半就晕倒了。
昏迷间,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里面我回到我们的少年时代。
也许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的商业巨鳄沈别鹤,在学生时代是个要领国家补助金,才能活下去的贫困生。
而我是梁氏集团的小公主,小说里的富家千金。
穿着高定的小洋裙,走到哪儿都是万众瞩目的目光。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我,喜欢上了那时的沈别鹤。
大家都说:「那小子又什么好的,一棍子憋不出半个屁。无谓就是会念点书,哪里比得上你围着你的富二代。」
但我不为所动。
拦住在食堂里打饭的沈别鹤,直接表白。
「沈别鹤,我喜欢你。」
那时的沈别鹤,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一双回力鞋。眼底带着淡淡的苍黄。
「梁同学,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一点。」
我以为他是脸皮薄。
笑嘻嘻又道:「那我下次等没人的时候和你说。」
他略微皱眉:「我没时间谈恋爱。」
「那你有时间干什么?」
「我要看书,学习,考试。」
他顿了顿,看向我手腕间精致的珠宝项链。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生来就拥有一切,我也不想做你无聊时间消遣的对象。」
这话说得有点难听,众人都投来戏谑的目光。
我也真是年纪轻,心大,想着不就是高岭之花嘛。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他要看书学习,那我也跟着他学。
后来大学毕业,沈别鹤一个项目需要资金起步。
两百万,不多。
我匿名投资,很快被沈别鹤知道了。
他脸色很是难看。
比我见过任何一次都要难看。
「梁酒,你这是什么意思?买我的身价?」
他无比反对,还说:「任何人都行,就是你不行。」
我有点疑惑,但还是改个了方式。照旧将钱投了进去。
与此同时,我爸妈也知道了这几年时间我都绕着一个穷小子转。
硬是安排了个与我家世相对的富二代相亲。
我坐在高级餐厅里,兴致阑珊。
沈别鹤就在此刻出现了。
他牵住我的手,胸膛不停起伏。
「梁酒,这就是你说的喜欢?」
我也不是个傻子,很快就明白过来沈别鹤是在吃醋。
追了半条命的少年终于缴械投降。
我们一路亲到了床边。
最后一刻时,少年为我破了戒,清冷的眼眸盛满了欲望。
「沈别鹤……」
我叫他,以为那就是一辈子了。
4
我在梦中最美好的时候醒来。
隐约闻到浓重的消毒水味。
我知道自己又身在医院了。
病房里的电视中正在播放沈别鹤和周幼京的八卦新闻。
两人刚下飞往夏威夷的私人专机。
好事的媒体将他们堵在机场追问
:「请问这次带周小姐过来是甜蜜旅游吗?」
「据我所知,沈先生家中已妻子,不知道这次高调出行会不会引家庭不睦呢?」
宛如抽了颈椎的周幼京,缩在沈别鹤怀里娇滴滴出声:
「沈先生早就和她貌合神离了,我们才是真爱……」
记者听这样直白的发言,更如嗅着味了。
拼了命的往沈别鹤面前挤。
「沈先生,真的是这样吗?听说你们之前感情一向很好,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境地。是和粱家没落有关吗?」
就在这时,沈别鹤突然接了个电话。
短短十几秒间,镜头放大了他接听电话时的不耐,烦躁,到冷笑。
「关于她的事以后不必跟我联系,要死就让她尽早死吧。」
显然,这通电话是关于我的。
医生这时恰好的走了进来。
他先检查了下我的脉搏,送来一个同情的眼神,婉转开口:「沈先生刚刚把夫人的卡停了,后续治疗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您看这要怎么办……」
阿珍一直在医院守着我,听到这样的话一下急坏了。
「这怎么行啊,夫人现在就等着治疗续命的。子宫癌啊,她疼起来可怎么办啊……」
她年纪大了,没什么朋友。
就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家里的亲戚说要去给我凑钱。
我努力的打起精神安慰她。
告诉她,我不想治了。
从刚开始得知患癌的害怕恐惧,现在的我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求生意志了。
加上我也明白,病到我这个程度。
死亡对我来说,是必然的。其它的外在手段,不过只是能将这终点延续一点点时间。
半个月?一个月?还是半年?
我觉得已没有必要。
我拜托陈延之给我定了去海城的机票。
自从两年前那场意外后,我们一直没联系。
他知道我已经穷途陌尽。
什么也没说,平静的给我转了五万块钱,让我好好玩。
我又转了一半回去,这钱我是要还的。
我不想浪费。
海城是我妈妈去世的地方。
我想在那儿死也挺好的。
离得近,或许我一闭眼,就能看到妈妈来接我了。
机场的登机声响起。
我拥抱阿珍,独自一人走进了机舱。
但飞机迟迟没有起飞。
佝偻着腰的空少谦卑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沈先生在停机坪等你。」
我楞了片刻,沈别鹤长身玉立。
身后是直升机旋转的机翼。
轰鸣声由远及近的传来。
他发了狠:
「梁酒,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连机票都是陈延之给你买的,你敢说你们没瓜葛吗!」

5
该怎么讲这个有点烂俗,却有关婚姻中信任与爱的故事。
当年沈别鹤因为有了我的第一笔投资。
很快在风口中发了家。
他本来就胸怀大才,成功对他而言是迟早的事。
在事业高歌猛进之时。
沈别鹤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为了报复他,
将我扒光了衣服和陈延之关在了房间整整两天两夜。
沈别鹤进来救我的时候,目睹了这样一副狼藉破碎的画面。
出来后我很快检查出怀有身孕。
沈别鹤便难以自控的怀疑我,是不是和陈延之发生了关系。
尽管我一再保证,孩子是他的,我是清白的。
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如同长满了刺的藤蔓。
将我和沈别鹤刮的鲜血淋漓。
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中,我气急交加,孩子流产了。
从那之后,沈别鹤便游走在不同的女人的腰间。
我低头了无数次,服软了无数次。
直到我彻底醒悟。
一个人如若从骨子里就不信任你,再做任何改变都徒劳无功。
他是高岭之花,是洁白无瑕。
他无法忍受我那一滴脏了他的爱意的血。
就像他可以为我截停飞机,却还在质问我和陈延之的时候。
我太疲倦了,疲倦到半点解释了力气都没有了。
「沈别鹤,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相信我。」
「你在吓唬谁,我已经问过你的主治医生了,他说你压根没病。」
沈别鹤抢过我的手机,把陈延之的来电摁掉。
「不要再让我发现你跟他有任何联系,不然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好像的确在走之前嘱咐过医生,让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生病的事情。
但只要沈别鹤仔细想想,我快要降到八十斤的身材,削瘦凹陷的脸颊,怎么又会是健康人的神态。
只是一切,都被他选择性的无视罢了。
像是为了刺激我,他还将周幼京接回了家中。
每天晚上,我听着他们的欢爱声无法入睡。
起先,心脏还会感觉到疼痛。
后来渐渐就麻木了。
偌大的房子里,只有阿珍时常会进来和我说些话。
她还是一再的劝解我。
「夫人,你就和沈先生说实话吧。他知道你真的生病了,一定不会做事不管的。」
「你们也是那么久的夫妻了,再大的事何苦用自己的生命来置气呢。」
我盯着天花板,犹如失了魂般的木偶一动不动。
直到几天后。
我精神突然好转起来,托人带了话给沈别鹤,说我有事找他。
阿珍看我的样子,以为我是想通了,兴奋的为我拿了许多漂亮衣裙。
我没拒绝,在镜子前认认真真化了个全妆。
先是粉底,眉毛,腮红,唇膏。
很好,镜子面前的女人再也不是虚弱如幽鬼。
莞尔一笑,足以和当初的梁大小姐媲美。
我按照沈别鹤短信里的地址。
走进了一个私人会所。
他正在应酬,几个妆容夸张的女人穿着性感妖冶,穿梭在各个卡座之间。
沈别鹤正襟危坐,手里把玩着一条柏木手串。
明明奢靡的光线打在他微微低头的侧脸,竟然生出洁净的清冷感。
我回过神,说出来意。
「我准备签署遗体捐献书,需要身份证等文件,你把这些还给我。」
6
沈别鹤眼中的诧异,比任何时间,都维持的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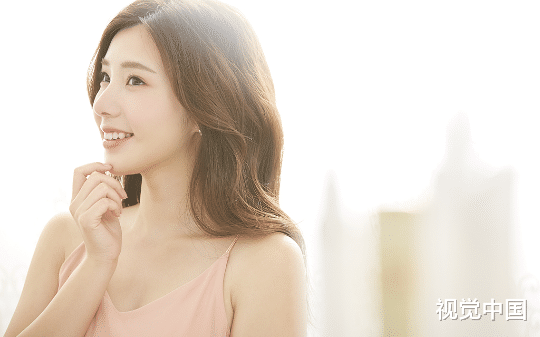



一对癫公癫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