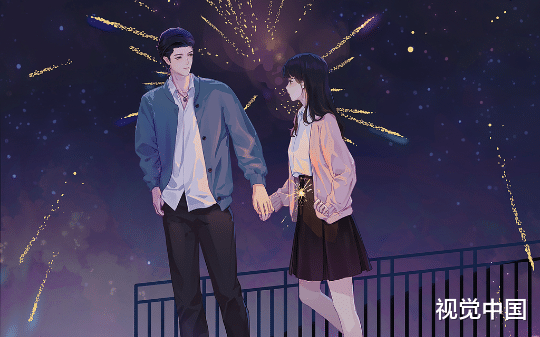沈严洲利落地剖开我胸腔。
作为法医,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具尸体,是他最爱的妻子。
他更没想到,只是忙着和白月光度假,没来救被绑架的我。
我就被烧成了一具焦炭。
时间回到那晚,歹徒让我给他打电话赎人。
他语气不耐烦:
「昨天要离婚,今天被绑架。」
「我就照顾下依依,你能少加点戏么?」
1
听说沈严洲的白月光回来了,但疯了。
因早年被人强J,精神失常。
沈严洲蹲在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依依现在离不了我,我要照顾她一段时间。」
「乖乖在家等我,好么?」
说完,在我额上印下一个吻。
我心中五味杂陈,他很少主动亲近我。
难得的温柔亲昵,竟是为了让我同意他去照顾别的女人。
我身子稍微靠后,与他拉开距离:
「你工作不是很忙么?」
他是A市最年轻有为的法医。
结婚三年,每日早出晚归,从没在家呆过一个完整的周末。
连答应我很久的海边蜜月旅行,也一直没能兑现。
「跟队里请假了。」
他低头,有点心虚。
上周,我让他请天假,陪我祭拜父母。
他一脸歉疚,说来了个急案子,上头下了死命令,这个月都必须加班加点,随时待命。
哦,原来不是工作重要,是我不够不重要。
我不着痕迹抽出手。
目光越过他,落在客厅的大幅结婚照上。
28岁的沈严洲一身制服,长身玉立。
我当时以为,我嫁了这世上最好的男人。
却因为太喜悦,忽略了他脸上勉强的笑意。
如今,才不过三年,婚纱照竟已渐渐褪色,一如我们摇摇欲坠的婚姻。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
「让妻子答应丈夫去照顾前任,你不觉得这有点残忍么?」
沈严洲愕然一瞬,显然没想到我会反对。
平时他说什么,我都百依百顺。
「阿宁,」他轻叹口气,压着情绪解释:
「我跟她没什么,就当帮一个老同学。」
「遇到这种事,依依她很可怜,你也是女人,能理解的对吧?」
我不理解。
要是我,我会去找医生,而不是找别人的丈夫。
我冷笑,心一寸寸凉下去:
「你要照顾她多久呢?」我问。
他显然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沉默一会。
「等她好了,我就回来。」
「那要是她这辈子都好不了呢?」
他脸上表情凝固,终于失去耐心:
「你就希望她永远好不了吗?」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大气的姑娘,什么时候这么斤斤计较了?」
说罢,他起身,捞起沙发上的制服外套,径直离开。
只留给我一声清脆的关门声。
2
偌大的房子只剩我一人。
我点燃蜡烛,独自吃掉了两块冷硬的牛排。
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他曾许诺,等结婚三周年时,一定带我去海边。
但现在,他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另一个女人。
电视里机械的女声,在这空旷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新闻里播,近期A市有罪犯连锁作案,绑架杀害年轻女性。
两个年轻女生痛失生命,她们的男朋友在镜头前痛哭。
悔恨没有好好保护她们。
不禁想,要是我死了,沈严洲会哭么?
他会后悔么?
僵坐太久,胃撑得实在难受,我出门买点药。
回来时却隐约感觉身后有人尾随。
我下意识想拨通沈严洲的电话。
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机。
后脑一阵剧痛,便失去了意识。
3
再醒来是在一间废旧仓库。
手脚被从后面缚住,脸蹭在粗糙的地上,火辣辣地痛。
想起新闻里的案情播报,今日恐怕凶多吉少。
蓦地,耻骨处传来一阵钝痛。
一双皮靴踩在上面,将我翻过身来。
「这娘儿们有几分姿色!」
另一个绑匪警告:「别特么精虫上脑,办正事!」
他们搜出我的手机,翻找一番。
然后拨通了沈严洲的电话。
他的电话在我通讯录的置顶,昵称是「老公」,还有专属的铃声。
他们把手机塞给我,示意我告知沈严洲,三天内带50万来赎人。
握着电话的手止不住颤抖,心跳因恐惧而超速。
此刻,我迫切想听到沈严洲的声音,才能安心。
但铃声响过两遍,他都没接。
到第3遍时,电话终于被接起。
他压低着声音,语气中透露出不悦:
「不是说了让你有事发信息?」
「打电话被依依听到会影响她情绪。」
心顿时凉了半截。
我听到自己因干涸而沙哑的声音:
「沈严洲,我被绑架了。」
「他们说,让你三天内带50万来赎我。」
他的不满更明显:
「你住着全市安保系数最高的小区,怎么可能被绑架?」
他们工作特殊,住所的确有24小时监控和自动报警系统,还有警卫执勤。
但世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的事。
我只能解释:
「沈严洲,我真的被绑架了。」
「如果你不来救我,我会死。」
对面一阵沉默,像是转移了个说话的地方。
良久,他轻叹口气,语气柔和下来。
「阿宁,」他严肃道,「我知道你不满我照顾依依。」
「但别拿这种事开玩笑,我会担心你。」
我呼吸一滞,竟有些哭笑不得。
一边弃我安危于不顾,一边担心我。
很好,沈严洲。
我还想说什么,却被一个娇俏的女声打断:
「阿洲,你怎么出来了?」
「穿这个小裙子去海边怎么样?」
沈严洲赶忙捂住听筒,撂下一句「以后再跟你解释」,便匆匆挂了电话。
4
绑匪说给沈严洲三天,他不来,就撕票。
我勾勾嘴角,疲惫地靠在生锈的架子上。
脑子里搜索着自救的办法。
但还是不可避免想到沈严洲。
他会怎么照顾姜依依呢?
其实,他刚找到她那天,我就去医院看过他们。
姜依依虽在病床上,但精神饱满,口齿清晰,依旧像大学时一样漂亮。
沈严洲就坐在床头,给她剥苹果。
他手指修长,一手握着苹果,一手执刀。
圆润的苹果在他指尖翻转几圈,便褪去了红润的外衣。
削完,他替她把颊边的碎发拢到耳后。
再将苹果切片,一块一块喂到她嘴里。
他们凝眸对视,眼神近乎拉丝。
那是我从未享受过的待遇。
婚后,沈严洲也待我很好。
会把全副身家全交给我,会给我买车,送我珠宝。
会在晚归后缠着我,享受极致的亲密。
会给我买苹果,买养胃的粥。
但他只会把苹果放冰箱里,叮嘱我记得吃。
不会仔仔细细削了皮,再切成小块喂我。
我懒,苹果便在冰箱腐烂。
他总是收拾干净,再买新的替换。
跟姜依依相比,所谓宠爱,实在算不上什么。
5
再醒来已是第二天。
如果沈严洲不来救我,这将是我生命的倒数第二天。
我不想就这么死了。
因为,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好不容易孕育的新生命。
我让绑匪再次联系沈严洲,告诉他,我怀孕了。
视频接通,沈严洲的脸出现在屏幕里。
一如既往地淡漠。
而我,衣衫磨破,浑身是伤,脸上无一丝血色。
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他终于先开口:
「阿宁,别演了。」
「我问了同事,A市连环绑架杀人案已经侦破,凶手全落网了。」
我沉默地看着他,更觉心凉。
只有那伙人会犯罪么?
其实,想证实我是否被绑架,对沈严洲来说再容易不过。
他是法医,有公安的同事,调监控一看便知。
甚至,只需回家一趟,看我有没有在家。
可是,他都没有做。
他在全身心地陪姜依依,治愈她的心理阴影。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见我不说话,他准备掐断视频。
「要是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沈严洲,」我打断他,「我怀孕了。」
是一周前知道的。
我不易孕,喝了无数碗喝着漆黑苦涩的中药,才迎来了这个孩子。
但知道消息那天,他刚找回姜依依。
那一晚,他没有回家。
我在客厅等他,从深夜等到黎明,从满心喜悦等到浑身冰冷。
他没有因这个消息而有太多波动,声音却放柔了些:
「阿宁,我知道你想要孩子。」
「但这事先放放,我先陪依依养好病,再陪你去看医生,行不行?」
又是姜依依!
我再也无法冷静,全身血液都冲到天灵盖。
「沈严洲,今天要是姜依依被绑架,你还会这么淡定吗?!」
「你那么爱她,跟我结婚干嘛?」
「孕检单在书房抽屉里,你不信自己回家看!」
近日的恐惧和绝望,在此刻宣泄出来。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沈严洲最见不得我哭。
每次见到我的眼泪,天大的事都会缴械投降。
「好好好,不哭了,你在哪里?把自己弄得跟花猫似的……」
「我现在就来接你回家,好不好?」
他还是觉得我在演戏。
我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委屈。
他根本不懂,我虽有时任性,但从来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人。
伤心之余,我找回理智,让他来救我比较重要。
我止住哭泣,「沈严洲,我在……」
话还未完,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
「啊!阿洲!」
「不要离开我!」
姜依依情绪失控,闯入视频里。
沈严洲再无心听说说话,只顾哄她:
「不走不走!带你去放烟花嗯?」
说罢,匆匆留下一句「阿宁,我们的事以后再说」便挂断视频。
看着黑下去的屏幕。
我知道,他不会来了。
他大概永远想不到。
「阿宁,我们的事以后再说。」
是他这辈子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6
夜幕渐渐降临。
绑匪见沈严洲还是不信我被绑架,商量着如何让他相信。
我在心底笑,他们不懂。
沈严洲不信,是因为我不重要。
我感知着小腹处的动静,安慰他。
「宝宝别怕,妈妈会保护你的。」
我必须想办法自救。
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
晚上绑匪不在这里。
我一个被缚住手脚的弱女子,被扔在人迹罕至的旧厂房里。
他们丝毫不担心我跑掉。
夜幕终于降临。
我确认绑匪已走远,才努力让自己坐起来,环视四周。
看到前方破旧的铁门露出一条两寸宽的缝。
缝隙中透进来影影绰绰的灯光。
外面有光,就可能有人!
我又看到了生的希望!
手脚都被绑住。
我担心伤到腹中的宝宝,我不敢站起来跳跃前行。
只能像只蚕蛹一样,侧着身体,在地上挪动。
衣服被磨破,肌肤蹭过布满碎石的地面,疼痛格外剧烈。
等挪到大门口,身子右侧早已血肉模糊。
我不顾身上的疼痛,伸着脖子张望外面的情况。
这个工厂废弃太久,又极其偏僻。
太久没人涉足,门口都长满了一人高的树丛。
我透过树丛的缝隙,隐约看到外面有两个人影。
真的有人!
我欣喜若狂。
忍着痛,竭力让自己坐起来。
透过铁门的缝隙往外望去。
那道熟悉的身影,不是沈严洲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