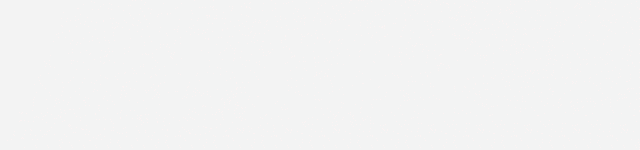
文/匹夫
编辑/匹夫
前言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故事发生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以主人公冉·阿让的生活作为样本,展现了拿破仑之战期间的法国,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生活状态。它以一种宽广的历史视野,以及精妙的叙事手法,对战争、和平、自由、人道等人类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着很高的价值。

这部作品从发表到现在,已经被改编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戏剧,一部又一部的电影。按照克里斯蒂娃的说法;每一部电影、每一部电视剧和每一部小说,都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叙事系统,但并不是所有的叙事都是独立的。
笔者将以2012版《悲惨世界》为例,对该系列影片中的“电影”与“话剧”进行对比,并探讨二者的关系。
电影和戏剧的关联
从视觉上讲,二者的区别:就是前者为荧幕,后者为舞台。这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
剧场,因为其所处的环境所限,本身就带有一种虚幻的意义。在舞台上,演员所做出的动作、表演等都是一种礼仪性的行为;因此,下面的观众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明白,这是一种虚假的,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一种代表符号和隐喻。

而影片作为一门动态艺术,更是打破了传统舞台限制,采用了现实主义方式来表现。在这个场景中,能指和所指是一体的,让人能够直观地看到电影要传达的信息,而不需要通过脑海进行抽象转换。
随着3D技术的普及,这种逼真感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欧阳予倩曾经这样说过:“戏剧是光与色的艺术,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对话剧与影片的区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

尽管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两者都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并且有着更为悠久的渊源。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与剧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个比方,影视与电视剧的关系可以用三个阶段来形容:“小媳妇”、“离婚”、合作。影片刚出现时,它很少被视为一种艺术,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再现,与今天的录像有些相似。
卢米埃尔曾经轻蔑地认为,影片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创造。他坚信影片之所以出现,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证明技术革新。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拷贝”,就不能算是一种“艺术”了。要想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就需要从其它艺术中汲取养分,使之成长。
在这个时候,电影是一种纯粹的再现真实方式,它所要吸取的就是叙述,也就是要学习说故事。而在这个时候,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剧场了。

戏曲起源于希腊,至今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作品。因此,在影片产生初期,可谓是把话剧当“小媳妇”,它的叙事技巧,艺术表现形式,常常对话剧有很多模仿。
即使是最初的电影剧本、演员、导演,也是从戏曲中衍生出来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思想家甚至将电影纳入了剧场,称之为“大戏剧观念”。
关于《悲惨世界》版本的选择
《悲惨世界》的影片有一些广为人知的版本。一部于1912所制作的四个片段的电影;英语版本,于1998年由比利·奥古斯特制作;2000年,英法联合制作,导演是何塞·丹扬。另外,在2012年,电视剧版本的《悲惨世界》也已经面世。因此,《悲惨世界》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像是一棵不朽大树苍拔挺立。
《悲惨世界》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翻拍,其在英国连续演出了18年,在美国也已经连续上演了16年。根据相关专家的估算,各种不同的《悲惨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观影人数大概已经突破了六千万。
 《悲惨世界》改编中电影和戏剧的关联
《悲惨世界》改编中电影和戏剧的关联可以说,在《悲惨世界》的故事情节上,作者做得非常好,并且把《悲惨世界》的精神意蕴表达得很好。
首先,2012的《悲惨世界》故事情节变得更有条理,也更紧密。它是一部很长的电影;但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由于拍摄时间有限,很多与主题无关的镜头都被删除了,而主题也只捕捉到了几个镜头,进行了重点描述;所以,电影拍摄方式,就是将所有镜头都集中到了一个镜头上,再将这个镜头放大。

在被拍成电影的时候,由于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以进行更为灵活的镜头转换,所以在尊重剧本的前提下,导演依据小说,在戏剧截取的这些点之间,在剧本中添加了一些过渡情节,并对其中的某些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刻画。可以说是连点成线,将主要情节演绎得淋漓尽致,讲述得比剧本更有说服力。比如,影片将冉·阿让在狱中举起旗帜;并在城里举起一辆马车来拯救人们形成对比,从而使沙威对冉·阿让的身份产生了疑问,使情节更为紧密,也更为符合逻辑。
这种对情节转折的处理,是话剧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悲惨世界》不仅保留了话剧强烈的情感,还加强了故事叙述;将整部电影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主线,这条主线并不是一条单独的主线,而是一条更加引人入胜的主线。

其次是对部分剧情的安排,影片《悲惨世界》吸取了小说中的各种优点,并在剧本中加以创新,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安排。比方说,那出戏里,管事生气地把芳汀撵了出去,冉·阿让也不去阻止。这一部分的剧情有些突然,与冉·阿让对弱势群体的怜悯和帮助不相称,而且,剧本里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合理说明。在这点上,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冉·阿让正被沙威的出现弄得心烦意乱,焦急地寻找着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看见芳汀。
这样的安排,既与作品本身的个性特点相一致,又显示出作品中命运的反复无常。就是由于沙威的出现,才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不幸的社会,女性和儿童的生活无法保证,灾难在任何时候都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形式发生。这种情况的设置,似乎是偶然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隐含着必然,与《悲惨世界》的书名不谋而合。最终,影片对高潮的处理达到了一个很宽泛的程度。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处,巴黎的一场年轻人暴动。那时候,七月革命虽然过去了,但政权还是被贵族把持着,下层民众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对于很多革命家来说,这就是对革命的一种出卖,由此引发了一八三二年巴黎的一场共和运动。电影里的铺垫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不同的角色在这个时候出现,将剧情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
作为“无”之学的戏曲,其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东西。由于场地限制,每个人的演出都是在台上进行的,而且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唱歌上,所以到了高潮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精彩了,没有那么多的冲击力。

影片通过将音乐和故事情节相融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一群人占据了广场,到一群人和一支部队对抗,再到冉·阿让把马吕斯从阴沟里解救出来,这一切都是圆满的。他们当中,有同学高唱代表激情的红歌,向代表腐败的社会发动战争。电影中的一些典型场景,比如部队轰炸了一座学校,这些场景直到今天还在被观众们津津乐道,鼓掌叫好。
在影片中,爱波宁的整体表现取得了一种文学与剧本的均衡。在这本书里,爱波宁是个很自私的人,也是个很坏的人。

她把柯赛特写给马吕斯的那封信偷偷地保存起来,又故意把马吕斯引向街垒去,目的便是要同马吕斯同归于尽。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化身。
话剧里,爱波宁被塑造成一个对爱情一往无前的女人。电影里,爱波宁把那封藏起来的那封信隐瞒了下来,这表明她是在吃醋珂赛特,但为了替马吕斯挨了一颗子弹而死,这表明爱波宁是个多情的人。尽管爱波宁和马吕斯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一种爱,而是一种青春年华里的姑娘对美丽的马吕斯一种纯洁的渴望,但爱波宁还是会为了这种渴望而献出自己的性命。

小说中,“妒忌”与“爱情”共存,小说中的角色更为丰富、生动,与雨果小说中“美与丑”的审美理念相吻合。雨果笔下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或好或坏,或丑陋或美丽,与真实的生活一模一样。由于其本身的艺术特点,电视剧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角色,可是在2012年度的《悲惨世界》中,这些角色却变得更加栩栩如生,让观众有一种亲切感。
这部影片也很好地塑造了沙威这个角色。由于剧本限制,沙威的身世并没有被写出来。影片中,他说:“我出生在监狱中”“我出生在你这样的败类中间。”可见沙威的出身也不是很好,正是由于低微的出身造就了沙威对于法律近乎偏执的信仰。在他看来,冉·阿让一日为奴,终身有罪,沙威追赶冉·阿让,与其说是因为私人恩怨,不如说是因为他内心的公正。但冉·阿让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超出了他的预料,即使当他被革命武装俘虏时,冉·阿让也没有像他所希望的一样,为自己报仇。

恰恰相反,冉·阿让把他放走了,并以德报怨。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公道?此时沙威内心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坚持发生了深深动摇。他所依赖的信念动摇,使他的生命走向了终结。影片在刻画“沙威”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他对“时空”的认识。
举例来说,沙威在这两个单独的场面里,都运用了一个不同的地点比喻:“边缘”。沙威在这两幕戏里都表现出他自己的地位崇高;但是当他心里感到孤独时,他却在崇高的边界上游荡着。这种高度的边界状况,是沙威精神上的挣扎与生命上的境遇比喻。
结语
《悲惨世界》这部2012年度的影片获得了极大成功,成为影视与话剧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一个例子。电影与戏曲的配合,既继承了戏曲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又与电影本身善于构筑实景的视觉效果相融合,以其视听兼备、雅俗共赏的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
戏剧与电影之间并不是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学习的关系。希望通过这两种方式,能够给对方带来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他们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卡努杜(意)《电影不是戏剧》
【2】安德烈·巴赞(法)《电影是什么》
【3】郭学文《《悲惨世界》,从小说到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