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植物人后,被老公拿各式各样的管子吊了两年命。
我以为,他是舍不得我离开。
直到他的白月光回国时。
他当着我的面,指着我的眼睛,对白月光极尽温柔的说,为了能让她的眼睛恢复光明,这对眼睛已经保存两年。
说完后,老公付司俞便吩咐医生护士,将浑身插满管子、已是植物人的我送往手术室。

只因付司俞的白月光双眼失明,需要我的眼角膜才能恢复光明。
我妈拦住付司俞,死死揪住他的衣角,哭得肝肠寸断。
“小付,我求你……蕴蕴身体素质太差,如果真的进行手术,可能就熬不过去了啊……”
“白小姐,白小姐她一定能找到更适合她的眼角膜的……”
付司俞的白月光,白悦人,闻言惊慌失措,好似小鹿一般急促地抓住付司俞的胳膊:“司俞哥,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虽然很想看到这个世界,也很想看到你,可是……”
她话已至此,却突然停住,反倒两行热泪自眼角滚落,低下头去,更显得我见犹怜。
“家属到底考虑好了吗?这个手术是做、还是不做?”
护士可怜地看我妈一眼,将手术同意书递给付司俞,眉头紧皱:“付先生?”
付司俞没有丝毫犹豫地拨开了我妈的手。
我妈整个人往后倒去,瘫软无力倒在地上的刹那,付司俞冷声开口道:“做!”
我妈发出一声哀嚎,扑向前,径直跪在付司俞的身前。
“咚咚咚”——
她极其用力地朝他磕起头:“小付、付总……我求你了,放过我的蕴蕴……”
付司俞却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语气漠然至极:“我和周蕴容是夫妻关系,有权替她签字。”
他大手一挥,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下自己身为丈夫的大名。
转过身,护住白悦人,语气极尽温柔:“悦人,你放心,你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了。”
“这双眼睛,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两年。”
母亲痛苦的哭声犹然在耳,我麻木地透过门缝,看向里面那被各种医疗设备续命两年的躯体。
她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像一只破烂的玩偶,安静地等死。
那是我可悲的肉身。
从出车祸开始,我的灵魂就被困在了这个不过二十多平米的单间病房中,无法逃脱。
我一直苦苦支撑,只因为付司俞竭尽全力地挽回我的性命。
他几乎骂遍整个科室的医生,要求他们不计一切代价留住我的生命体征。
哪怕余生我只能成为一个植物人。
他总是来看我,一看就是一整夜。
对我的一丁点问题都紧张得不得了。
我真的以为他爱惨了我,舍不得离开。
直到三天前。
付司俞带着久未联系的白悦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病房。
那天,我激动万分地扑向付司俞,因为他已经有半个月没来看我了。
我开心至极,绕着他的身体打转,直到我的主治医生皱眉道:“付先生,请您考虑清楚,手术是存在一定的失败率的。”
“失败率多少?”付司俞淡淡问。
医生说了一个最保守的数字:“50%。”
“做。”付司俞回过身,温柔地握住了白悦人的手,轻声道,“反正她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也用不上眼角膜了。”
“倒不如把它捐给更需要的人。”
医生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忍:“可是……”
“万一有朝一日,周蕴容小姐醒了呢?”
“那就等她醒了再说。”
那一刻,我突然福至心灵地意识到了什么。
付司俞,这是要把我的眼角膜,捐赠给白悦人?
让我做瞎子?
我怔怔地飘着,逐渐飘离了付司俞。
看到他们浓情蜜意的模样,一股森寒冷意自心头汹涌扩开。
恍惚间,我突然意识到。
付司俞与我结婚,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
那时候,因为意外成为盲人的白悦人与付司俞提了分手,从付司俞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我闯入了付司俞狼狈落魄的人生之中,陪他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
他向我求婚时,只字未提爱。
只是问我:“蕴容,如果有朝一日,我需要你的帮助——那帮助可能是你身上的某个脏器、器官,你会愿意吗?”
恋爱脑的我点头便说愿意。
他深深地凝视我的双眼,仿佛在透过我看向其他人。
最后,温柔地吻上我的眼角,说:
“你的眼睛,很美。”
可现在想来。
是不是那个时候,付司俞就开始打我眼睛的主意了?

我死了。
手术很成功,但我术后出现不良排异反应,身体的各项指标降至最低点。
在我抢救的时候,我妈向付司俞打去电话,几度哽咽:
“小付,蕴蕴她、她快不行了……”
付司俞极度不耐烦:“不就是做了个小手术么?周阿姨,我见您是长辈,平时才对你诸多容忍,但请你不要得寸进尺,撒这样的谎来欺骗我。”
“悦人刚做完手术,身边又没人照看,现在很需要我。”
“反正周蕴容躺在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不管我去了还是没去,都影响不了什么。”
“别再来打扰我!”
他没给我妈任何再说话的机会,径直挂断电话。
甚至当我妈再次拨打他的电话时,那头传来“正在通话”的冰冷女音。
他把我妈拉黑了。
可我妈哪懂这些,还一味执着地不停拨打。
直到抢救室的大门拉开,满脸沉重的医生走出来,脸上写满抱歉:“家属请节哀,我们尽力了。”
“病人身体本来就熬不住了,又做了一个手术,导致免疫系统彻底崩溃……”
我妈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情绪完全崩溃的瘫软在地,从嗓子眼里挤出我的名字来:“蕴蕴,我的蕴蕴……”
我的尸体,被盖着白布推出来。
我妈竭尽全力地支撑着自己,掀开白布,用自己的额头抵住我的,双眼猩红:
“蕴蕴,你怎么就那么傻?”
“车祸发生时,你怎么就那么奋不顾身的,挡在了他付司俞的身前呢?”
“他根本,一点都不爱你啊!”
脑中惊雷劈开,我头痛欲裂,骤然惊醒。
是啊。
我本来可以,不用成为一具尸体的啊。
是因为,恋爱脑的我在车祸发生时,奋不顾身的挡在了付司俞的身前。
所以,付司俞只是轻伤,我却全身多处骨折、重度脑震荡,彻底陷入昏迷。
我以为我的真心换来了真心。
可现在才意识到,倘若不是我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恐怕在两年前。
我就该死去了。
大概是因为彻底死了,我突然可以离开那个束缚我的病房。
我跟着我妈,眼睁睁地看着她处理我的后事。
她一个极度爱美、看上去绝不像五十多岁的妈妈,竟在一夜之间白了头,苍老了至少十岁。
看着我妈颤颤巍巍地背影,我的心痛到几乎窒息。
给我办销户那天,是个大晴天。
烈日照得我妈的背愈发佝偻。
在街上,我妈遇到了白悦人。
都说爱人如养花,白悦人和刚回来时瘦瘦小小的她截然不同了。
她全身穿着价值不菲的私定,背着限量版的名牌包包,走起路来时昂头挺胸。
那双明亮的双眼落在我妈身上时,难免嫌恶地皱起了眉头。
看到她的瞬间,我妈冲了上去:“白、白小姐!”
我妈局促不安地搓着自己的衣角,哑着嗓音问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周蕴容的母亲,您的眼角膜就是她……”
白悦人伸手就甩开我妈的手,将她往前一推。
“砰”地一声,我妈手上那张轻飘飘的死亡证明坠落在地。
白悦人不由分说地踩了上去:“哪来的疯婆子!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妈瞪圆双眼,扑上前:“你让开!”她握住白悦人的脚踝往上抬。
她明明没有很用力。
可白悦人,却突然倒了下去。
再抬眼时,双眼涟涟:“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这就把眼睛还给您——”
她伸出手,狠狠地摁在了自己的双眼上!
下一秒,一个结实的巴掌,狠狠落在我妈的脸上。
付司俞只抬手一挥,我妈便狠狠倒在地上,手肘被冰冷坚硬的水泥地蹭出一条长长的伤口。
鲜血淋漓。
付司俞却对血色置若罔闻,反倒轻捏住白悦人的手腕,往下一按,痛惜道:“悦人,你别这样对待自己,我会心疼的……”
“你就是太善良心软了!眼角膜是我签字要求捐赠给你的,与你无关!”
他回过头,满眼写满对我妈的憎恶,瞳孔幽深、戾气十足:“周阿姨,我看在你是蕴容母亲的份上,才给你一分薄面!”
他声音发寒,一字一顿道:“但这不是你欺负悦人的依仗!”
“你女儿周蕴容之所以活到现在,全靠我每个月用七位数的金钱给她吊命,没有我,她早就死了,要她一双眼睛,怎么了?!”
“你如果再得寸进尺,我会停掉她所有的续命药物和昂贵的医用器材!”
我妈死死地盯着白悦人脚底踩着的死亡证明。
她不停地摇着头:“那是我的,那是我女儿的……”她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凄惨的哀嚎,“那是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的心疼得快要窒息了。
我伸出手,努力地抱住我妈,可怎么都碰不到她。
我好想说,没关系,妈妈,不过是一张死亡证明而已。
我还在你身边呀。
可我,为什么怎么都碰不到你了啊。
我妈情绪彻底崩溃,再次扑上前,一口咬在白悦人的手上。
白悦人发出一声低叫,抬脚便将我妈踹开。
我妈终于得到机会将那张纸抢了过来。
她抖着手,想把我的死亡证明收回包里。
谁知下一秒,付司俞伸出手,将那张薄薄的纸“嘶”地一声,扯成了两半!
他拿走的一半,很快被他“哗啦”撕成了无数碎片。
“什么鬼东西!”他皱眉不耐道,“有什么好闹的?”
我妈浑身抖如筛糠,猩红着双眼朝付司俞吼道:
“那是蕴蕴的死亡证明!”
一张碎片,飘到了付司俞的手上。
他低下头,白纸黑字,赫然写着“死亡证明”四个大字。
还有,我的名字。
付司俞有瞬间的愣怔。
我妈跪在地上捡着那些纸张碎片:“我不能让蕴蕴连死亡证明都没有,不能让蕴蕴连家都回不了啊……”
很快,付司俞眯起双眼,极尽嘲讽地笑了:
“说吧,周阿姨,你想要多少钱?”
我妈僵住了,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他。
她的嗓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付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在我面前装出这样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不就是想借着你女儿的眼角膜,在我这里多捞点钱吗?”
付司俞嘲讽道:“确实,这笔钱,我该给你。”
“但你不该骗我说你女儿死了!怎么,你是觉得她一条命,跟眼角膜比起来,能换更多钱是吗?”
我妈疯狂地摇着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
付司俞掏出了一张支票,“啪”地一声扔到我妈的脸上。
他居高临下、极度冷漠道:“这张支票,你想填多少钱都可以。”
“就当做是,你把你女儿的命卖给我了。”
“从此以后,她这个人,她全身上下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与你再无关系!”
“就算她真的死了,那她的骨灰也是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给谁,就给谁!”
我妈僵坐在地上,双眼空洞地盯着那张支票。
付司俞的身影逐渐远了。
我妈胳膊和腿上的血,已然凝固。
炙热的太阳将她浑身烘得发红,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动了一下。
然后低下头,发出如兽之将死一般绝望的哀鸣。
“蕴蕴,你怎么就,爱上了这样一个男人啊?”
烈日之下,我也凭空出了一身冷汗。
心如刀绞地陪在我妈的身边,我只恨不得将她紧紧抱住,护在我的身后。
可为了保护这样一个男人……
我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葬礼前夕,我妈来医院收拾我的所有东西。
一个小小的盒子,就能全部放下。
就像我的人生一样,贫瘠、乏味,最后什么都不剩下。
我妈在抽屉里,翻到了我出事前,特地为她买的生日礼物。
一个黄金的镯子。
她一直不舍得带,放在抽屉里。
这一次,她泪流满脸地拿出来戴上了,嗓音沙哑:“我的蕴蕴……”
那是我留给她,唯一的念想了。
我妈抱着小小的盒子,在走廊上碰到满脸心疼焦急的付司俞。
他像对待珍宝一样抱着白悦人。
匆忙吼道:“医生呢!赶紧过来!”
“她说她的眼睛不舒服,怎么回事?”
从我的角度看去,白悦人脸色如常,双眼却十分空洞地看向前方,神色惊恐道:“怎么办,司俞,为什么我又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乖,别害怕,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他满脸的焦急,像是火一样将我灼烧。
我出车祸时,付司俞异常镇定。
第一时间拨打110和120,冷静地将我送往医院,处理伤势,缴费、等待,一切一气呵成,他连一滴泪都没有掉。
那时候,我以为他是被吓到了,也以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毕竟,他一直都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可,原来不是。
他不是没有情绪。
只是,我不是那个让他心疼的人。
将白悦人送到护士那里,他叼起一支烟,烦躁不安地吸了口气。
这时,他看到了我妈。
他情绪不佳,像抽风似的,立马发了癫:“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女儿都已经卖给我了,你没有资格再来看她!”
付司俞此话,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走廊上的人都围过来,对我妈指指点点,议论着她卖女儿这件事。
我妈慌张无措:“不是的,那张支票我没有……”
“支票?她还真为了钱把自己的女儿卖了啊,好恶心。”
“以前我只在网上看到过这种当妈的,现在长见识了……连自己的女儿都舍得卖,太贱了。”
我妈的脸色越发苍白,只顾着不断摇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下一秒,付司俞看到了她手上的黄金镯子。
眼神转戾:“怎么,支票上的钱还不够满足你的贪婪,连蕴容的金镯子,你都要偷走?!”
他伸出手,直接握住那金镯子一撸!
我妈的手臂,因为他的粗暴,而直接被蹭下了一层皮,血肉模糊。
在我妈的嘶吼声中,他抬手一挥,将那金镯子直接扔往窗外。
而我妈,竟然猩红着双眼,同样往窗外扑去!
“妈——”我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

伸出手,竭尽全力地,我想要将我妈的身体抱住。
可妈妈只是穿过了我透明的双臂。
“咚”地一声,坠落到草地之中。
走廊中瞬间一片哗然!
付司俞难以置信地冲到窗边,惊出一声冷汗:“不、不就是个金镯子吗?至于吗?”
无数护士鱼贯从他身边经过。
他伸手捞住其中一个人的胳膊,下意识开口道:“把她安排到VIP病房,就住在周蕴容的病房旁。”
“她的治疗费用,我全部负责!”
那护士一脸厌恶地甩开了他的手,发出一声哂笑:
“付先生,您还不知道吗?”
“周小姐术后出现不良反应,已经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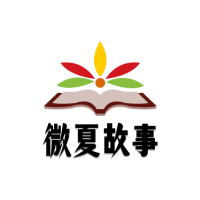
胡说八道毫无逻辑,为虐而虐
又是一个法制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