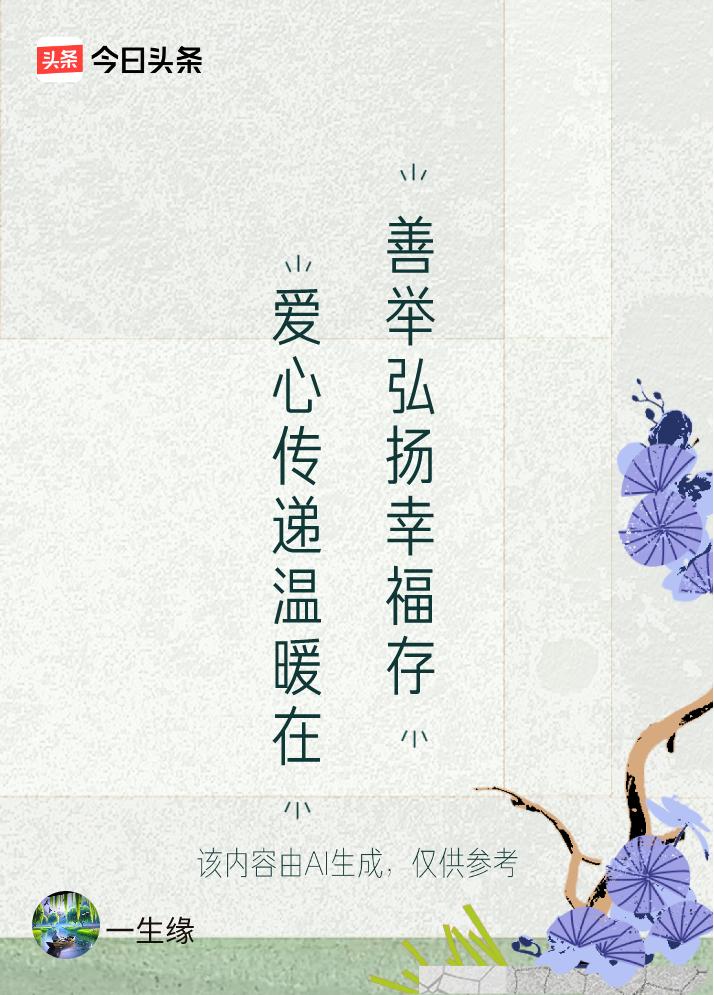《一盏灯的温度》 暮色四合时,老巷口的杂货铺总会亮起一盏竹编灯笼。暖黄的灯光透过竹篾缝隙,在青石板上织出细密的菱形光斑,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 店主周伯总爱在灯下摆张藤椅,膝头摊着本发黄的《诗经》。那天傍晚,我抱着被雨打湿的快递箱躲进檐下,他起身递来温热的姜茶时,我才发现他左手小指缺了半截。"那年矿难,工友把我推出井口…"他摩挲着旧搪瓷杯,杯壁映着跳动的灯火,“后来攒钱开了这铺子,夜里总得亮盏灯。” 这盏灯渐渐成了迷途者的路标。外卖小哥常来借充电器,流浪猫在灯下吃周伯备的猫粮,连巷尾总冷着脸的刘婶,也会在雨天悄悄把伞挂在灯钩上。直到那天暴雨倾盆,我看见穿校服的少年蜷在灯下,周伯正用旧毛巾给他擦头发,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矿难报道里,那个用身体挡住落石的年轻矿工,右手无名指戴着刻"平安"二字的银戒。 如今周伯的铺子挂满了灯笼,都是街坊们送来的。竹编的、纸糊的、玻璃的,每当夜幕降临,整条巷子就流淌着暖色的星河。刘婶的孙子考上大学那年,在灯笼上画了朵木棉花,花瓣里藏着工整的小楷:“光在处,春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