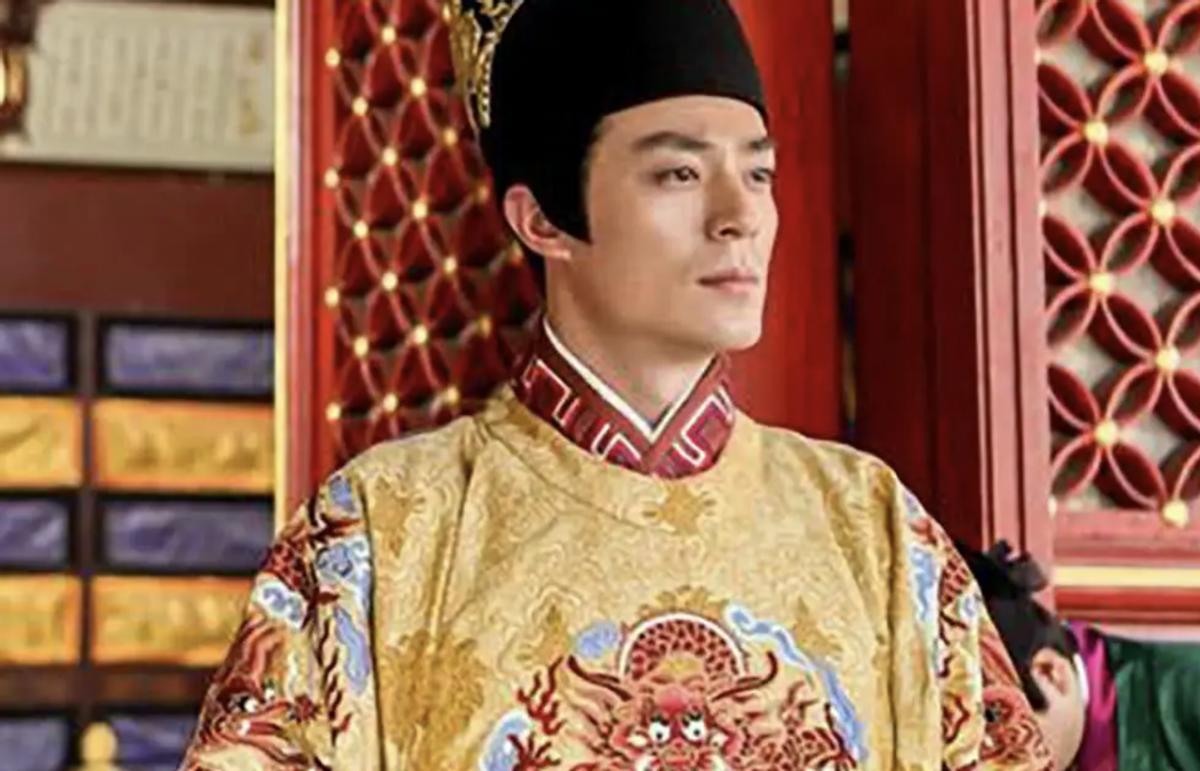暴动、群殴、致死,牵连几乎所有京官,堪称大明天字第1号血案 那是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 按干支纪年,是己巳年,属蛇。 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一大早,一封从河北府送来的加急文书,风尘仆仆,转送到了京师内阁之中。 这文书的封皮已经有些褶皱,还带着战场特有的硝石味道,以及尚未干涸的血水。 内阁的值班大臣打开文书,只看了半晌,全身却开始止不住地发抖,然后一个踉跄,“哐当”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那薄薄的两张信纸从大臣的手里缓缓飘落,在空中划出一道十分优雅的弧线。 信纸上的内容十分简单,简单到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 明军溃败,几近全军覆没,君威不屈,以至于被瓦剌俘虏。 瓦剌,是蒙古诸部之一。 自从太祖高皇帝建立明朝,元政权败退漠北之后,蒙古内部就开始分裂。 我们知道,元朝在结束全国性的统一政权之前,最后一位皇帝,叫做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元顺帝) 妥懽帖睦尔,中文翻译过来,意思是一口铁锅。 而那时节的蒙古,就是一口千疮百孔的大铁锅。 当年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横扫欧亚大陆时多么雄浑豪迈,而如今北元政权仓皇逃窜的模样,就有多么狼狈不堪。 那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王朝已然不见,到如今,只剩下在捕鱼儿海仓皇逃窜的背影。 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建立一个王朝十分艰难,但毁灭一个王朝却是很容易的。 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并非没有道理。 而在这样的悲惨境遇之下,蒙古内部很快出现了分裂,并且逐步演变成了鞑靼,兀良哈,瓦剌三大游牧集团。 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经多次派遣名将远征鞑靼,而成祖朱棣在位时,更是五征漠北,打得兀良哈抱头鼠窜。 挨过收拾的鞑靼和兀良哈十分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他们宁愿窝在漠北整天吃沙子,也不愿意再触明朝的霉头,独独剩下这个瓦剌部,野心昭昭,平时在边境地区多有滋扰,到正统十四年,瓦剌部在其太师也先的指挥下,居然纵马深入明朝腹地,实在是猖狂至极。 瓦剌部飘了,时任大明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很生气。 生气之余,年轻的小皇帝也十分兴奋。 自己九岁登基,主少国疑,万事全靠内阁和大臣,这个皇帝当的,实在是没有牌面。 内阁大学士们拿自己当幼主,整天跟哄孩子似的对待自己,而六部的官员大多依仗为官多年,更是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过。 作为帝王,朱祁镇十分不喜欢这种被人瞧不起,被人夹裹和保护的感觉。 他想要向大臣们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虽然年轻,但同样是一个优秀的帝王。 而本朝皇帝想要证明自己的方式,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北方建立军功。 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都曾经巡视北边,在北方战场上建立了帝王的功业,自己又何尝不想缔造属于自己的功名? 皇帝也是要脸的,皇帝也是爱现的,皇帝没有军功在身,他在大臣面前,他也抬不起头来。 而现在,机会来了。 骄纵蛮横的瓦剌人犯我大明疆土,朕身为天子,理应御驾亲征,保卫我朝臣民,扬我大明国威。 朱祁镇兴冲冲地告诉了大臣们自己想要领兵北上,御驾亲征的想法,但大臣们只对他说了三个字: 想屁吃。 大臣们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事儿听起来虽然刺激,但刺激的同时,往往就代表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 小皇帝自小长在宫闱之中,学的都是帝王礼仪,皇家规范,对领兵打仗一窍不通,真要让他上了战场,万一有个好歹,怎么交代?谁能负责?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满朝文武都坚决反对皇帝亲征,只有一个人,高举双手,表示赞成。 这个人,叫王振。 王振河北蔚县人,永乐年间入宫为宦,是英宗皇帝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内侍。 英宗皇帝唯王振之命是从,王振让他向东,他绝不向西,王振让他吃苹果,他绝对不吃鸭梨。 帝王如此威仪扫地,朝臣们为求自保,更是纷纷投身于王振门下,相互勾结,形成了势力庞大的“王党”。 所以就算诸多大臣都反对亲征,但只要王振投了支持票,这事儿就算是成了。 大事已毕,皇帝十分开心,立刻带着由王振统领的二十万大军屁颠屁颠地出发了。 结果,大军到了战场,由于皇帝不懂兵法,王振又胡乱指挥,明军队伍阵型涣散,瓦剌军队抓住机会,全力冲锋,明军无力招架,兵败如山倒,很快全军覆灭,王振身死,而年轻的小皇帝犹如待宰羔羊,居然被瓦剌人给俘虏了。 年轻的朱祁镇把自己当成了横扫漠北的朱棣,但此时的瓦剌太师也先,却不是当年那个被朱棣打得鼻青脸肿的马哈木了。 朱祁镇留学瓦剌的故事我们容后再议,现在,皇帝被俘虏的消息传回京师,大臣们算是炸开了锅了。 皇帝被俘虏,这还是有明以来头一回。 大臣们连夜开会,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于臣子们而言,皇帝被俘虏,堪称奇耻大辱,但此刻他们必须忍辱负重,尽快议定接下来的部署。 因为击溃了明朝军队的瓦剌部没有停下脚步,数万大军已经越过河北,直奔京师而来。 既然是要开会,那么必然要有主持会议的人,大臣们临时抱佛脚,把英宗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拉了出来,暂做主理人,主持这次紧急会议。 会议一开始,大臣们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逃,一派主战。 徐侍讲表示,他昨日夜观天象,发现白虎星动,紫微南移,实在是不祥之兆,恐怕是预示我朝天命已尽,到如今只有放弃京师,退守南京,才可以度过此次劫难。 而主战派,则如兵部侍郎于谦,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说了这么一句话: 京师是天下之根本,是王朝的核心,如果放弃京师,那么咱大明就算是玩完了,何况宋室南渡的厄运还历历在目,我朝又岂能重蹈负责? 徐珵胡说八道,搞封建迷信,而于谦痛陈利弊,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所以主战派的意见很快得到了支持,由是群臣议定,要死战不退,誓死保卫大明。 是战是逃的问题已经议定,但会议并未结束,因为大臣们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办,这件事儿,就是清算王振余党。 都很清楚,大军覆没,皇帝被俘,宦官王振是罪魁祸首,虽然他随军出征,不在京师,但朝廷里王振的余党还是很多的。 这帮自甘下贱,投身于王振门下的官员们,甘做王振的爪牙,沆瀣一气,多有不法之事,十分可恶。 这帮大臣们商量完了是战是逃,算是落下了胸口的大石,精神稍有放松,便一个一个开始声讨王振,要求郕王处理王振余党。 有些大臣神情悲愤,捶胸顿足,有些大臣暗自伤神,涕泪横流,有些大臣振臂高呼,声泪俱下,更有几位老臣,以头撞柱,好悬没死在大殿上。 大家如此作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处理王振余党,以泄臣僚们对王振的愤恨之情。 通过史书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知当时这帮大臣们咬牙切齿的心态,他们越闹越凶,越闹越厉害,甚至开始出言威胁朱祁钰,表示如果你不处理,我们死也不会离开。 郕王朱祁钰平日里只不过是个养尊处优的王爷,他哪儿见过这等场面,当下不知所措,但皇帝身边的一位锦衣卫指挥使,名叫马顺,却十分镇定,快步走到殿中,厉声呵斥诸位大臣有失体统,要求他们赶紧散朝而去。 马顺之所以越级指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表现得如此积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正是大臣们口中的王振余党。 并且,马顺已经不能说是王振的余党,而应该说是王振的死党。 王太监在朝中贪赃枉法,党同伐异,残害忠良,多是这位马指挥使出谋划策,充当爪牙。 在事态没有发展得更为严重之前,马顺认为,自己有必要挺身而出,斥退群臣,避免事件升级。 不得不说,马顺这位小兄弟,别的没有,勇气倒是大大的有。 此时的大臣们,群情激愤,他们恨不得生啖王振肉,豪饮王振血,对“王党”的愤恨也已经到了极致,他们就像即将冲毁的堰坝,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 而马顺,即将成为这个出口。 率先发难的,是户科给事中王竑。 王竑离马顺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在马顺下场之前,他正哭天抢地地诉说自己对英宗皇帝的担忧,以及对王振余党的愤恨,此刻他泪眼婆娑,用宽大的袍袖擦了把眼泪,目光往前这么一看,正看到马顺在趾高气昂的呵斥大臣。 马顺,马顺...王竑不住地在心里念叨。 不一会,他想了起来,这位锦衣卫指挥使是王振极为要好的同党,多少忠臣志士遭到王振的打击迫害,都是由马顺派人逮捕,投入到诏狱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