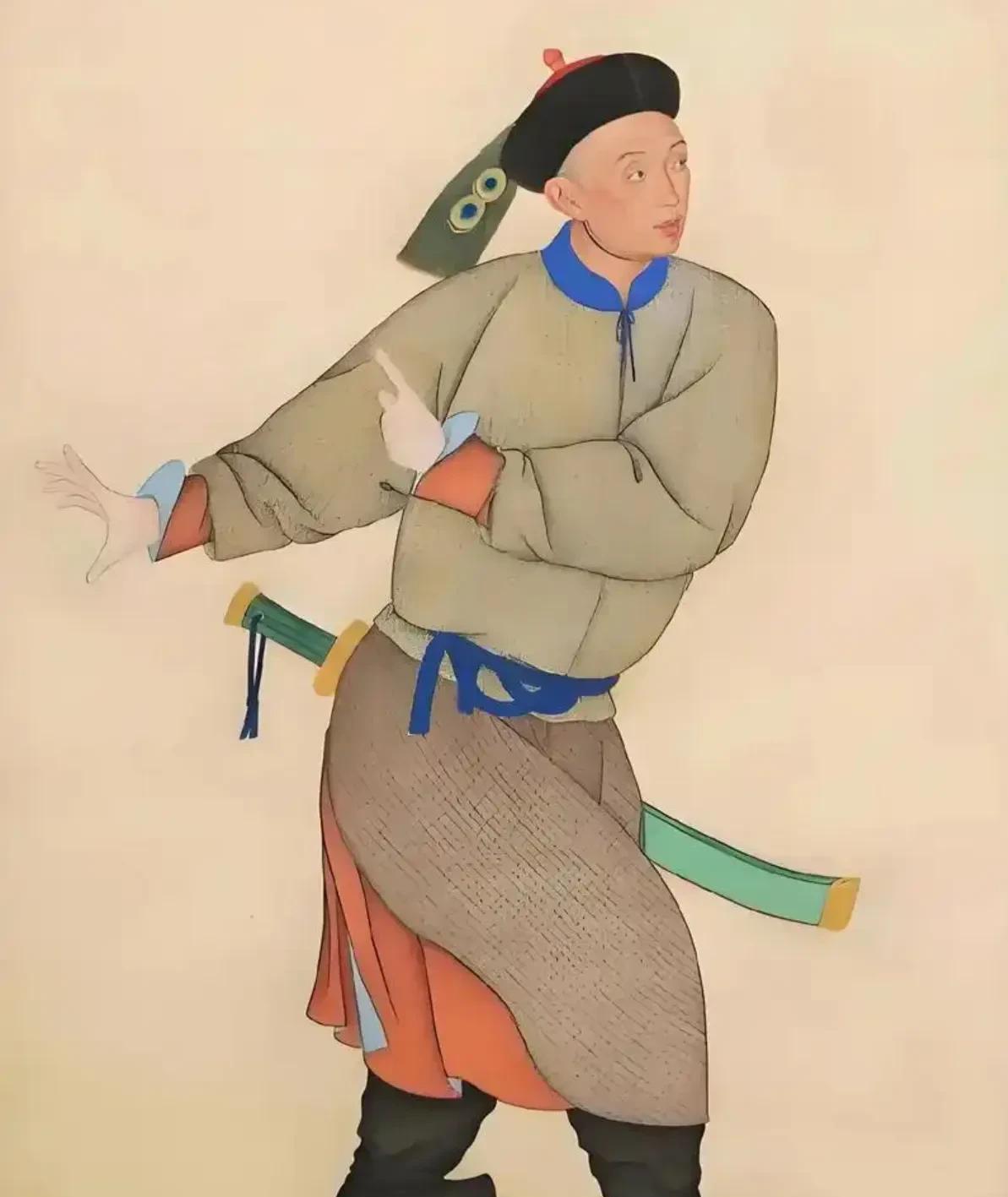1949年冬天,湖北石首的一个鱼贩王光尧,突然被人拿着一张报纸找上门,说他失联十八年的儿子,成了解放军青海军区的副司令员。
这一听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事,可纸上白纸黑字,名字是“王尚荣”,他不信,说他儿子叫“王尚寅”,还以为是来逗他的。
可也就是这一张报纸,把一个老人从漫长的等待里拉了出来,也把两代人命运的断线,一点点重新连了回去。
王光尧是地地道道的石首调关人,靠卖鱼养家糊口,家里清苦,但人硬气。
上世纪三十年代,家里孩子多,饭都吃不饱,大儿子王尚寅十三岁就被红军的人拉去做童子军,穿草鞋背干粮就上了山,说是去“跟部队吃公家饭”。
家里人开始不拦,觉得小子出去混一混也好,反正家里管不了,可后来消息就断了,再没音讯。
王光尧一开始还跑去问村里识字的人写信、打听,可到了抗战打得正紧那几年,信是完全断了,他心里其实早就有准备,觉得儿子多半是在战场上没了。
时间一晃十八年,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天下打得翻天覆地,王光尧也老了。
他还在鱼市上摆摊,每天骂骂咧咧卖几条鱼,没人提儿子的事他也不提。
可那年冬天,调关镇来了个熟人,李乔,当年是县里的干部,现在还在县委干事,走路带风,说话冲得很,一来就把报纸摊在他摊头,说:“老王,你家九斤成将军了!”
“谁?”王光尧眯着眼问。
“九斤啊,你家大儿子。”
王光尧一听这话,脸就冷了,他不认这个名。李乔赶紧说,“不是说他原名王尚寅吗?这报上写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我一看这名,地方也对,八成是他。”
王光尧不信,说你看错了,我儿子要是活着,怎么这十多年一封信也没有?可李乔是当年他儿子的团组织介绍人,两人是旧识。
他说得斩钉截铁,还劝王光尧写封信去青海军区碰碰运气。
王光尧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让女婿帮忙写了封信,只说“九斤这个名你还记得吗?当年你走时穿的破衣服,还记得吗?”,信纸上没写多少,但句句是当年家的事,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过了将近一个月,真的有回信了,是青海那边寄来的军用信封,封面写得正儿八经。
王尚荣在信里认了父亲,说自己就是王尚寅,那年刚参加红军不久,部队里都鼓励化名,怕是家里出事,他才改的名字。
他说:“我一直记着家里,说不想回,是不敢。怕牵连你们。”他还提了母亲送的两块银元,说抗战时救了他一命,被子里挡住了子弹。
王光尧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哭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就说他要去青海,他不识字,也不看地图,但认定青海在哪都不怕。
他扛着老棉袄,带着女婿,从湖北一路坐船、挤车,走了二十多天,到了青海西宁。
到了军区门口,岗哨一开始不让进,他掏出那封信,手抖得不行,一边哭一边喊:“我是他爹,我是九斤他爹。”岗哨赶紧报告,部队里一查,真有其人。
那天晚上,王尚荣在司令部见到了这个白发苍苍、满脸风霜的老人。
王光尧一见他,愣了半天,最后喊了一句:“九斤!”那声音哽住了,王尚荣一身军装,快步走过来抱住他:“爹,我是九斤。”一句话说完,两个人都哭成了泪人。
旁边的军人都围着看,没人说话,那一夜,他们说了整整一宿的话,从调关的小巷说到红军的山头,说到抗战里的鬼子炮火,说到家里那口破锅。
可时间紧张,第二天部队要剿匪,王尚荣又得上前线,临走前他跪下给父亲磕了头,说:“这十八年,我欠的太多。
”王光尧也没多说,只是摸了摸他肩膀,说:“好好活着,比啥都强。”
一年后,1950年底,贺龙特批王尚荣回乡探亲,他带着妻女回到调关,刚进村口就被人认出来,乡亲们炸了锅。
谁能想到那个当年穿草鞋的九斤,现在成了解放军的大官,村里敲锣打鼓迎接他,他穿着军装,左手牵着女儿,右手扶着老父亲,一步一步走进家门。
那天晚上,村口摆了几十桌饭,大家一边吃一边听他讲部队的事,王光尧坐在中间,听儿子讲自己打马家军、抗日时中弹,脱下军装给他看伤疤。
老汉看着那些坑坑洼洼的疤,眼睛直掉泪,说:“你要是真死在战场上,我认了。可你活着回来,我这命也值了。”
可好景不长。王尚荣部队任务重,探亲只有一周,之后他回到西北,再没能常回家,王光尧身体越来越差,1958年冬天去世。
儿子那年正带队在边境清剿土匪,没赶回来送终,1959年,他回家祭拜,站在父亲坟前久久不语,后来有人听见他小声说:“我连送爹一程都没赶上。”
这事在调关一带传了很多年,有人说是命,有人说是担当,可对王尚荣来说,他一直把那封父亲当年寄出的信,夹在皮夹里随身带着。
他说,这封信,是他命里的一道光,让他知道无论打到哪,总还有个“家”字,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