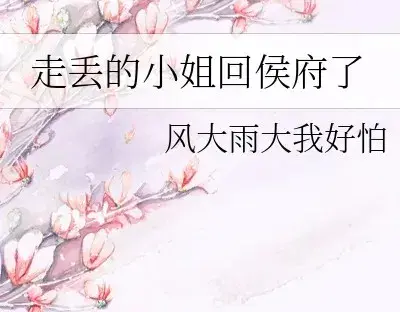男友患上了渐冻症。
我为他不分昼夜奔波筹钱治病。
直到我兼职时,听到他不屑地对别人说。
"温聪聪就是一条最听话的狗罢了。"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
1.
推开包间门前一秒,我还在为丰厚的小费而暗自欣喜。
可当我看到程金驰被一群公子哥簇拥在中央时,我笑不出来了。
此刻的他,一身定制西装,贵气逼人,且看起来精力充沛。
哪里有半分病榻中需要我精心照料的虚弱模样?
他优雅地晃动着手中的威士忌,整个人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贵气。
我不敢置信地盯着他又看了看,耳边传来女人撒娇的声音。
"驰少,灰姑娘的游戏好玩吗?"
"那个叫温聪聪的到底给你下什么迷药了,值得你花这么多心思演这出无聊的戏码。"
程金驰没有立即回答,他轻抿了一口酒,眼底藏着令我心悸的笑意。
他伸手轻抚女人的脸颊,随后低头吻了上去。
包间里一片暧昧的气氛,衬得我的存在如此格格不入。
女人咯咯笑着,娇嗔道。
"驰少,别这样,今晚去我那里吧,我保证让您尽兴。"
程金驰这才收回手,戏谑地说。
"这就是为什么温聪聪好玩。"
"她多纯啊,不像你骚成这样,看到个男人就往上贴。"
女人扑到他怀里笑得花枝乱颤
"讨厌!您可不能这么说人家嘛。"
我感觉到窒息,努力咽下心头涌上的酸涩。
此刻,我终于确定。
眼前这个衣冠禽兽,就是我朝夕相处一起穷了四年的男友程金驰。
六个月前,程金驰红着眼眶跟我提分手。
"聪聪,我们分手吧……我不想拖累你。"
那一瞬,我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为什么要分手?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死死抱住他,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他。
程金驰沉默了片刻,然后拿出一份诊断书。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渐冻症)"几个大字。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坍塌了,声音带上了哭腔。
"怎么会这样……"
程金驰没说话,只是紧紧回抱我。
我感觉到肩膀上传来湿意。
"聪聪,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渐冻症晚期后那么狼狈丑陋的样子。"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带着绝望。
"明天我就搬出去,在我还能动的时候,让我再好好抱抱你……"
我气得眼睛通红,狠狠地拍打他的背,哽咽着说。
"你把我对你的感情当什么了!"
"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承担痛苦,我们当然要一起面对。"
但程金驰的治疗费用高达数百万,对于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半晌,他有些沮丧地松开我,声音低沉沙哑。
"聪聪,我不想治疗了,我只想在这最后的时间……好好陪陪你。"
望着他那脆弱的神情,我强挤出一抹微笑,柔声安慰。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我存款只有几千块,对治疗费就是杯水车薪。
我静坐在床上,盯着柜子发呆。
那里放着妈妈的遗物,一套珠宝首饰,也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
一边是相爱四年的男友,一边是妈妈的遗物。
我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那晚,我蜷缩在床头,紧紧抱着,泪流满面,嘴里不停地自责。
"对不起,妈妈,女儿没出息……女儿不孝。"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程金驰将我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现在他遇到困难,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第二天,我卖掉了遗物,带着程金驰搬进了潮湿的地下室。
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
为此,我不得不放弃了刚找到的实习工作,一口气接了三份兼职。
每天起早贪黑,在酒吧、便利店和家教补习班之间来回奔波。
累到快要虚脱,只为了能多攒一点钱。
2.
为了让我能好好工作,程金驰总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那时候,我只恨自己没能力,不能将他照顾周全。
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一条没有尊严的狗。
从众人对他恭维的态度,不难猜出程金驰的身份非富即贵。
明明包厢里暖气很足,我却感觉浑身发冷。
"喂,傻站着干什么,有没有点眼力劲儿?"
"还不赶紧给驰少倒酒,真是个废物,活该一辈子给人打工。"
一个公子哥不耐烦地喊道。
我从回忆中惊醒,僵硬地给这群纨绔子弟倒上酒。
经过程金驰身边时,闻到他身上熟悉的味道,我一时恍惚。
一个手抖,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他的西装上。
他身旁的女人立刻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脑子有病吧?驰少身上这件西装顶你半辈子工资,你赔得起吗!"
我慌忙爬起来,想用抽纸为他擦拭酒渍。
却被那女人狠狠甩了一巴掌。
她将我从程金驰身边扯开,轻蔑地将剩下的香槟尽数浇在我头上。
"贱人,看看你什么德行,外面站街的都你比能看,就你这小手段还想勾引驰少?"
众人哄笑成一团,我难堪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香槟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晕开了我的廉价化妆品,我现在的脸一定丑得没法看。
我看见卡座中央的男人似乎心情愉悦地轻笑了一声。
我曾经很迷恋程金驰的声音。
尤其是他抱着二手吉他,在我们那间小出租屋的阳台上为我唱歌时的样子。
然而,此刻熟悉的笑声却刺痛了我的耳朵。
我正想端着托盘默默退出,却听见程金驰冰冷的声音响起。
"站住,得罪了我还想走?我看你也赔不起。"
"这样,你把这瓶酒喝了,今晚的事就算过去了。"
说着,他将一瓶未开封的烈酒推到我面前。
我站在原地,迟迟没有接过那杯酒。
声音颤抖地说。
"对不起,我对酒精过敏。"
然而,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淹没了我的声音。
程金驰皱了皱眉,似乎没有听清我说什么。
刚才泼我酒的女人听到了,她冷笑道。
"酒精过敏?装什么装?不就是想吸引驰少的注意吗?"
程金驰摆了摆手,指着地上被打翻的果盘说。
"既然不能喝酒,那就趴下去把这些水果吃了吧。"
我的心一沉。
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被人按倒在地上。
"别耍花样了,快吃!"
一个男人粗暴地抓住我的头发。
我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人死死按住。
有人抓起地上的水果,强行往我嘴里塞。
"不...我不能吃芒果..."
我含糊不清地说,但没人在意我的话。
冰凉黏腻的果肉沾满了我的脸颊和嘴唇。
有人掐住我的下巴,逼我咽下口中的水果。
我感到喉咙开始发痒,呼吸变得困难。
我蜷缩在地上,剧烈地咳嗽着,感到呼吸道开始肿胀。
恐慌和绝望淹没了我,我知道过敏反应正在快速发作。
程金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似乎对我的反应感到意外。
但他很快就移开了视线,仿佛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
我的尊严,被我最爱的男人踩在脚下碾压。
心底那股酸涩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住。
我蜷缩在地上,好不容易缓过气来,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艰难地站起身。
颤抖着腿准备离开,却又被程金驰叫住。
"你表现不错,这块表赏你了。"
"卖了它,够你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
我漠然地看着他,试图在那张熟悉的脸上找到一丝我认识的程金驰的影子。
可惜,一无所获。
正当我伸手要接过那块手表时,他忽然轻笑了一声。
"你很像我女朋友,连对酒精和芒果过敏都一模一样。"
"不过她可没你这么势利,如果是她,肯定不会收下的。"
女朋友?
我在心里冷笑。
多么讽刺啊。
我默默收回手,程金驰却将手表扔到我怀里。
"脏死了,赶紧拿走滚吧。"
这手表光是看着就知道价值不菲。
绝非我这种底层人能企及的奢侈品。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一块手表,就能顶我努力一生。
我转身离开,还未走远,就听到有人问道。
"驰少,说真的,那女的为了你,连她妈留下遗物都舍得卖。"
"你真一点都不心动吗?"
3.
程金驰没说话,只是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
他轻笑道。
"一条狗而已。这世上能让我爱上的女人还没出现呢!"
我的呼吸愈发急促,过敏反应让我感觉随时可能窒息。
"我就说,驰少一直不都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嘛。"
"那女的是不是特别会伺候人,要不等您玩腻了,也让兄弟们尝尝……"
话音未落,程金驰一脚将他踢翻在地,抄起桌上的酒瓶往那人头上砸去。
酒瓶碎片划伤了他的手,鲜血直流。
程金驰眼神冷漠,仿佛在看一具尸体。
"你也配?"
无人敢上前阻拦。
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
"驰少,别动怒,您受伤了回去不好交代……"
闻言,程金驰冷静下来,示意众人闭嘴,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在寂静的包厢里格外刺耳。
我慌忙按下挂断键,正欲离开,却被他喊住。
"等等。"
我心跳如雷,血色尽失。
"把头抬起来。"
程金驰冷冷地命令道。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头来。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因过敏反应而肿胀,黏腻的果肉还粘在脸上,狼狈不堪。
程金驰皱着眉头,仔细端详着我的脸。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中闪过一丝困惑,但很快就被厌恶取代。
"真他妈难看。"
他厌恶地说:"滚。"
我刚推开门走出去。
就听见有人问程金驰是怎么看我的。
他嘴角微扬,漫不经心。
"我就喜欢看她为我当牛做马的样子。"
"让她对我情根深种,然后再将她推下深渊,多有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