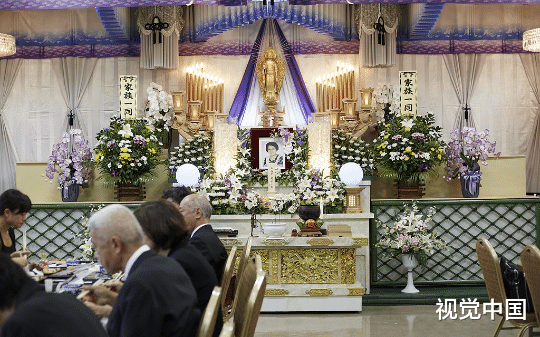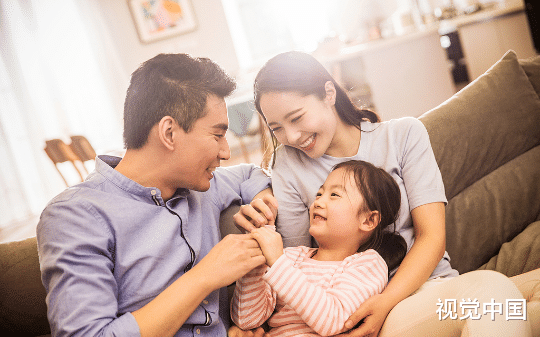60岁生日刚过,我就和老伴提了离婚。
可我说出“离婚”两个字后,一家人都疯狂嘲笑我。
老伴说:臭婆娘,就你这样还学人家离婚。到哪离婚你都不知道!
儿媳说:妈,今天的衣服别忘了洗,我们房间的四件套换一下,在家多做点事。
儿子说:妈,我们出门了,你自己在家别开空调,太费电!
这一刻,我忍了几十年的委屈,爆发了。
婚,我非离不可!
1
他们笑过之后也没人当回事。
儿子和儿媳匆匆忙忙赶着上班。
儿媳叮嘱我“妈,今天的衣服别忘了洗,我们房间的四件套换一下,晚上我可能回来得晚,你去帮我接浩浩放学。”
儿子摸了两块面包揣兜里。
开玩笑对我说:“妈,别赌气了。早上我没吃到早饭,晚上你可要做好吃的补偿我。”
孙子也跟着附和。“奶奶!我要吃大餐!”
临了出门又黏黏糊糊抱了我一下。
其实还是吩咐我做事。
“奶奶,在家要给小白兔喂吃的。你再给我买两只小乌龟吧,好不好。”
浩浩被儿媳妇揪出去。
刘建伟也跟着优哉游哉地晃出去。
又回头露出一个恶狠狠的表情。
“臭婆娘,中午我喊三伯来家里吃饭,你把昨天钓的鱼给我红烧了。弄不好我打死你。”
“还离婚,就你这样还学人家离婚。到哪离婚你都不知道......”
门关上了。
屋子都空了,一下都安静下来。
我却觉得烦极了。
昨天的饭菜我没吃上一口,现在被搅和得乱七八糟。
一夜过后,发出难闻的酸味。
白花花的纸巾像小山一样堆着,满桌都是要清扫的垃圾。
每个地方都有脏衣服,臭袜子藏在沙发的缝隙,找到了一只,另一只找了半天发现在昨天穿的鞋子里。
饭粒子硬邦邦地黏在锅里。明明说了好多遍,吃完的锅要马上泡水。
满眼都是忙不完的活。
管了大半辈子,我不想管了。

2
我回房间,空调遥控器就扔在床上。
我试探地摁了电源键,空调开了,冷风吹出来。
没有异响,空调好好地在运转。
我突然想笑。
这是我第一次开空调,以前不管多热,只要我一个人在家都不能开空调。
刘建伟说我不会开,只会瞎弄,弄坏了换个空调要大几千。
我去问我儿子,我儿子不耐烦地说:“妈,以前没空调的时候你怎么过来的,怎么现在一定要开空调呢。你知道电费有多贵吗?”
后来我就不问了。
但我心里想说,他们只要在家,空调就从早开到晚,没人说电费贵。
孙子怎么摁那个遥控器,他们都乐呵呵地在旁边看,没人说空调会坏掉。
我观察了好多年,明明只要摁下电源键,空调就会运转。
但我习惯了不和他们争执,所以从来都不说。
热得难受了也就开个小电风扇吹吹脸。
原来开空调这么容易,制冷效果这么好。
满身的汗一下子就干了,我就坐在空调底下一张一张翻存折。
我想离婚。
就算离婚也要有钱。
邻居家媳妇闹离婚的时候就说财产要一人一半。
我觉得我和刘建伟也要一人一半。
3
存折的钱我拿一半,其他的钱,宅基地,田,家里养的牲畜我都不要。
儿子也不要,这么大了,也自己成家了。
孙子也不要,孙子是他们刘家的命根,我争不过也不想争。
我自己拿一半钱,我要出去住,顺便治治病。
女人那里的病,医生说叫宫颈。
我妈因为这个死的,大姐上个月做了手术,把整个属于女人的地方都给拿掉了。
我在医院照顾了一个礼拜,刘建伟天天指桑骂槐地说我是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现在这个病找上了我,我不知道指望谁,只能拿点钱自己给自己治。
医生说我有可能会死。
其实我一点都不怕死。
我妈生了姐妹四个,我排老三。
生下来瘦瘦小小的,小脸揪着乍看就是个苦着脸的小老太。
有些事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我这张没舒展过的面皮。
家里太穷了,赚工分的年代,家里有四个女儿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身体又不好,我爸找半瞎的郎中抓中药,一碗一碗灌下去,流的血都透着苦味。
乡下的孩子在田垄上疯跑,疯叫,我孤零零坐在昏暗的房间,吹不了一点野风。
人家都说我爸妈养了个金疙瘩,风吹不得,太阳晒不得。我妈总是没好气地翻个白眼。
我自己缩在那,不敢看旁人。
小妹的学费,又成了我的医药费。

4
我小妹倒不在乎,她性格和我们家的任何人都不像,爽利又麻溜。
我爸妈没生儿子抬不起头,都靠我小妹和人家硬犟。
那时候过年,村长挨家挨户去蹭饭,我家最穷,最好的菜就是一条红烧鱼。
村长吃的只剩鱼头鱼尾和鱼刺。
就算这样,我爸妈也不舍得倒掉,第二天就有香喷喷的鱼冻。我们都挺开心,只有小妹气得面红脖子粗。
“我们一家6口人,三个病殃殃地歪在那,一年到头吃不到一块肉。”
“他倒好,一来就给吃光,也不见平日给什么好处。”
“我不服,我找他理论去!”
谁都拦不住愤怒的小妹,小妹穿着旧袄子在村长家门口打滚,村长捱不住,掂量出一块大肥肉。
小妹拿回来,又催我妈炼了油,巴巴给村长送了大半海碗。
村长也不气了,直说这小姑娘灵得很。
后来,小妹成了我们家的保卫神,所有人都站在小妹身后,看着矮小的她强硬地应付每一个上门找茬的人。
别人都说,我小妹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
可是啊,最有出息的小妹被我给拖累了。
每每我爸攒了点钱,我都正好生场病。
小妹的学费一拖再拖,我在家缝补着衣服想自己干脆死了算了。

5
小妹总说,刘建伟就是欠收拾,当这么多年夫妻怎么就不能强势一点。
我都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计较这些干嘛呢。
刚嫁人的时候,他不这样。虽说算不上什么温柔小意,但是下工回来还记得带上一些路边的鲜果。
后来他爸妈病得重了,人渐渐瘫了。
两个老的就这么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
他问我能不能在家照顾两个老的。
我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钱不多,但有的攒。
为了那两个老的,我一咬牙辞了工作。
一照顾就是20年。
他态度也变了。
他嫌弃家里臭烘烘的,嫌弃赚的钱不够花的。
嫌弃到家半天饭菜还没端上来,还嫌弃每天翻来覆去都是那些菜。
两个半瘫的老人要翻身,要擦身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屎啊尿啊就弄在身上。
我照顾完这个照顾那个,面对他的冷脸,我累得不想说一个字。
好不容易送走两个老的,我生孩子留下的病根也显露出来。
每到阴天,浑身都彻骨地疼。像是那些雨变成鳝鱼,在骨头缝里游来游去。
没了两个老的,屋子空得吓人。
我愁苦着脸给自己贴膏药,刘建伟抽着烟说我装腔作势卖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