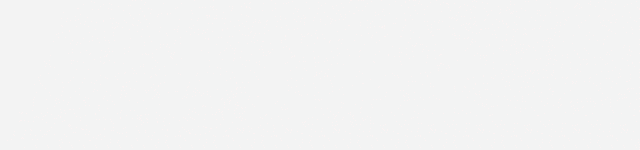
文/匹夫
编辑/匹夫
前言在中国众多的优秀导演中,顾长卫绝对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他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师”。
不得不说,顾长卫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不管是在商业上,还是在各大影视节的认可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然而,顾长卫作为一名导演,却成为了我们讨论他在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对艺术的追求,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一、“非常慢”的镜头形态
一、“非常慢”的镜头形态路易斯·贾内梯在其著作《认识电影》一书中,曾将世界各地的影片从镜头形式上进行了快
慢的划分。
在这些影片中,美国影片以“快”著称,欧洲影片以“慢”著称,亚洲影片以“非常慢”著称。这样的划分虽非绝对化,却也生动地反映了三大类型影片的审美特征。
“快”就是美风格的商业性影片,比如好莱坞,这种影片的速度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美感,而“慢”就是欧洲的艺术性影片,比如法国的影片,比起单纯的为了满足受众的视觉需求,欧洲艺术性影片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宁静美好的境界。

亚洲的电影,就像是日本的小津安二郎,中国的贾樟柯,侯孝贤,都是“非常慢”的类型。他们的影片中,有很多的长镜头,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几分钟。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顾长卫并不想按照安德烈·巴赞的说法,去还原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他想要通过长镜头来为自己营造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在影片的表现形式上,顾长卫一直在追求“非常慢”的审美,让观众看到一种极慢的、静止的画面。

比如《孔雀》里顾长卫的那两个长镜头,至今仍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之作。第一个是一个三分钟左右的场景,是妹妹高卫红一家五人在一起玩煤球;
顾长卫用一个水平的角度,给了大家一个高卫红一家五人生活的场景,比如楼道里的煤球,晾在那里的衣物等等,而五个人则分工明确地参与到打煤球的工作中。
因为下雨,一家人都在楼道里忙着遮掩,连晾着的衣物都被拿走了,一家人开始作画,这时候摄像机还站着,然后就是一群人开始作画,高卫红一脚踩空,从这一脚踩空中,就能看出她以后的悲惨人生。

这个长时间的拍摄,充满了生活的味道,几乎可以用一部纪录片来形容,这一幕,对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同时,对较年轻的观众来说,这部片子也呈现出一个人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所处的中国北部小镇上的真实人生。
长镜头平静,但在缓慢的时光流逝和固定的空间里,人们可以感觉到他生命中的平淡和麻木。还有一个经典的,就是母亲给那对兄妹下毒的那一幕。

杀死这只鹅的过程,从母亲取出药物,倒在杯子里,随后出画再入画手提大白鹅给其喂水,然后是拍打着翅膀,伸长着脖子,抽搐着,直至死亡。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逼真,让人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短短两分钟内被杀死。
更残忍的是,毒死白鹅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正在吃饭,这对兄妹被吓得不轻,这一点,旁观者都能理解。

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有杀死自己弟弟的想法了。在顾长卫的影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立春》中的王彩玲和她的养女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快地嬉戏。
即便是《龙头》这种只有17分钟的小电影,顾长卫还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将一个正在嗑药的女人默默地抽泣着,将她的伤痛深深地传达给了观众。
二、有意味的视觉符号拉康等人提出,幼儿在早期阶段具有对镜子的喜爱,但是这个阶段的幼儿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我”之间的联系,反而把自己所见到的人当成了“我”。这是一种将真实和虚幻混为一谈的情境感。

当孩子长大后,这样的感觉就会慢慢淡去。然而,在人的生活中,对于真实与幻想的混淆,或者对真实的抗拒,更倾向于逃离到幻想的环境来获得自己的满意,这是一种长久的心理状态,有时候连人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顾长卫很会利用镜子这个象征,为观众带来一种不同于现实的幻觉,一种虚假的幻觉。镜中的世界或者暗示着主角的主观幻想,或者暗示着主角的一厢情愿,或者暗示着主角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水月镜花,会迅速地消逝。

顾长卫的影片里,主角通常都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群体,他们被束缚在了这个社会的规则之中,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孔雀》里面,妹妹高卫红为了讨好一位拉手琴师,拜对方为“干爸”,这样的举动,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非常惊人的,在外人看来,两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之情。
在影片中,高卫红演奏了一支手风琴,义父跟着音乐跳了一支朝鲜舞,顾长卫用一个旋转的画面,将义父分成了两个,一个在镜中,一个是镜子外的。

虽然两个义父都在舞蹈,但意义却完全不一样,镜子意味着二人暂时地沉浸在一个美好的世界中。
而在镜子外,则有两个女人在门口看着跳舞的他们,眼神充满怀疑,这意味着在现实的眼光中,两个人是与美好无关,应该被否定的。
最终,义父触碰开关的悲剧下场,基本已经成了定局。再比如《最爱》里赵得意与琴琴相拥而眠的情景,就是用一面镜子表现出来的,这就说明了这种美丽而温暖的情景也只是昙花一现,极易被打破。

由于他们在一起,爱滋病并没有终止他们的生活。这对快乐的情侣就是他们所期望和幻想的完美形象。
除此之外,《最爱》里的那辆小列车,《孔雀》里的那只大锅,也是如此。《最爱》里,赵得意与琴琴走在轨道上,当一列列车由远方开来时,赵得意非但没有避让,还大胆地冲在列车前面,直至列车停下。
赵得意点燃了一根香烟,以示自己的狂妄。列车在此代表着对爱滋病病人的不平等的看法。它们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向赵得意、商琴琴二人穷追猛打,虽然赵得意一时半会儿也占了上风,但毕竟不可能比得上一辆列车,最后不得不脱离轨道,任由列车疾驰而去。

再比如《孔雀》,当高卫红弹奏一首曲子时,茶壶中的水沸腾起来,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甚至把茶壶的盖子都给顶起来了,可是高卫红听得太入神,根本就没注意茶壶。
这把大茶杯,象征着高卫红也站在了这个世界的烈火上,只不过,她终究会被自己的烈火焚烧殆尽,所以,她所说的话,在别人听来,实在是太渺小了。在这种形象中,客体自身的生存状态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呼唤着观者去分析它。
 三、个性化的镜头技巧
三、个性化的镜头技巧萨杜尔在描述希区柯克的时候,说希区柯克的影片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技术,而不是那些无聊的花哨的技术。用来点评顾长卫的片子,再合适不过了。
在视觉美学上,顾长卫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是一个与“第五代”导演一同长大的人,曾为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著名作品掌镜。
但当顾长卫以一个导演的姿态主宰影片的所有细节,甚至是影像特效的时候,娄烨、管虎等“第六代”导演却早已跻身中国电影界。

仔细研究一下顾长卫的电影,就会知道,他与“第五代”,“第六代”的电影,不一样,顾长卫的电影,不管是在故事上,还是在视觉上,都融合了前两代电影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顾长卫被誉为“姗姗来迟的五代导演”的原因。
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长镜头,顾长卫与贾樟柯等人都有相似之处,但从技术上来说,贾樟柯等人都是近乎“零度写作”的,跟巴赞的纪实影片相比,顾长卫的技术更多的是一种偏激,这说明了他的个人立场和价值观并没有出现任何缺失。

在这种情况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两段式的透镜。双层场景,就是将两个不同的场景组合起来,形成一种视觉冲击。
从构图上来说,它是一个“极致”的概念,以全景式展现大面积,以近距离展现小面积的细节。就像是远景和近景之间的转换,而长焦和短焦之间的转换,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最爱》一开头,就是赵小鑫的灵柩所在的院子,里面有柱柱,有赵齐全,有赵得意,还有赵小鑫的脸,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种悲伤的氛围。

另一个则是颠倒图像,也就是头部朝下的图像。顾长卫经常会用一种颠倒的手法,来展现一个人的表情。
比如《最爱》里的赵得意,生病住进了小学,一到了夜晚,他担心郝艳的安危,让他的父亲装模作样的走过来,看看她在做什么。
顾长卫就是用了这种颠倒的手法。同样的画面,也经常在电影《孔雀》、《微爱之渐入佳境》等电影里看到。

可以看出,顾长卫的影片让人感觉到了“在场”,而这一点,顾长卫和张艺谋等同时代的大导演有相似之处。除了以上的摄像技术,顾长卫对画面的构图和颜色等,也有严格而精确的要求。
例如,《孔雀》运用了许多冷淡的蓝灰色,以表达“十年浩劫”后仍未摆脱心灵的伤痛,仍在郁郁寡欢的状态。
顾长卫善于用阴郁的基调,来刻画一个人物所处的环境,然后用极少的几个鲜明的颜色,来展现这个角色在生活的边缘,却又对自己的宿命充满了不屈的意志,同时,也能让人体会到这种被生活所吞没的悲伤。这里就不多说了。
 结语
结语不得不说,顾长卫在美术方面很有天赋。顾长卫曾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家,他给电影带来了更多的可能,那些杂乱、混乱、模糊的真实世界,在他的作品里,变得井然有序,明亮而又暗含深刻。
尽管顾长卫并非从从事摄影这一电影拍摄基础性工作转为执导筒的个例,其影片在主题、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也并非独一无二。
但是,就在视觉上的艺术思维与实现导演本人意图之间的关联来看,顾长卫的影片是具有个性的,他是自己电影当之无愧的“作者”。

总之,说顾长卫在处理视觉美学方面有着不容小视的借鉴作用,一点也不为过。
参考文献:
[1]刘宏球《电影学》
[2]张晓峰《电视编辑思维与创作》
[3]林亚斐《主观镜语下的小人物形象建构---以《立春》《孔雀》《最爱》为例解读顾长卫电影》
[4]王子.云遮处《寻找阳光----顾长卫三部曲的影像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