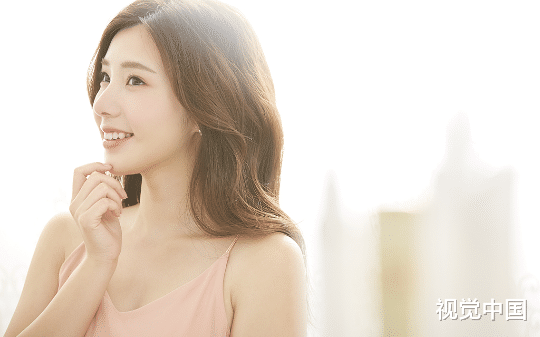哥哥三岁时生了场大病需要脐带血,所以我带着使命出生了。
我十岁时哥哥病情复发,爸妈强行将我按在手术台上捐骨髓。
再后来,哥哥恶化需要换心时,遭遇车祸碾压的我被送进了同一所医院。
我听见妈妈掩面而泣。
「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我宁愿活下来的是儿子。」
那好,心脏给他们。
连同生命,一同还给他们。
1
我被送到了哥哥所在的医院,那具被车碾压过的身躯掩盖在白床单下,红霎时成了花。
面容被拖行到失去辨识度,鲜血顺着指尖滴下,身体冷到发抖。
担架的推拉声,路人的悲鸣,小孩的嬉闹声,在耳边交织缠绕。
医生趴在我的肩头,用最大的声音在我耳边吼:「你有家人吗?你现在的情况很危急。」
红色的视线中,我明明看见担架擦过妈妈的身边,艰难伸出手指试图勾住她的手指头。
然而妈妈只回头瞥了我一眼,并未认出我。
她踮起脚尖,「哎呦」一声,慌忙躲闪,生怕我的血手脏了她昂贵的裙子。
一如小时候的我无数次踮起脚尖,试图用脏兮兮的小手牵住她,都被她无情躲掉。
医生剩下说的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
隔着几米,我和妈妈的距离越拉越远,手指摇摇晃晃举起,指着他们的方向。
妈妈情绪崩溃地再次和爸爸陷入争吵。
她捂着脸无比痛苦。
「那儿子怎么办?他心脏衰竭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心源,他就死了。」
我有些疲惫地想起,哥哥刚继承家业病情就再次恶化,需要心脏移植。
然而纵使在海市一手遮天的爸妈也找不到匹配的心源。
那时,他们用十分纠结的目光看向我,犯了难。
毕竟这次哥哥需要的是心脏,不是像脐带血、骨髓一样可以随意在我身体里透支的东西。
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直接将我按在手术台上,任由钢针穿透我的骨头,无视我恐惧地哭喊,只叫我别矫情,坚强点。
心脏只有一个,摘掉会死人的。
可最终,我还是难逃一死。
烟圈淹没了爸爸的情绪,他声音嘶哑。
「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我又何尝不希望活下来的那个是儿子。」
妈妈从悲痛中片刻挣开身来,难得想起我了,却尽是些污言秽语。
「还有何昭月那个白眼狼,养她有什么用,他哥都成什么样了!我们在医院急得要死,她说不定还在外面快活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一滴血顺着床沿滴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触地有声,心尖冰冷。
最后一丝求生欲彻底消失,连视线也清晰了几分,恐怕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
医生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他们是你家人吗?还是有什么话说?」

2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交代清了三件事。
「我是...孤儿。」
「别报警了...就是意外。」
「把心脏...捐给她儿子吧。」
在即将进入抢救室的前一秒,那只倔强指向他们的手终于垂下。
我的灵魂逐渐脱离残破的肉体,亲眼目睹自己蓄满血泪的瞳孔逐渐涣散,变得雾化失色。
一行血泪顺着眼眶流下。
死了真好,以后不用哭了。
由于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容貌也尽毁,最后医院也只能按照我的遗愿,正常走捐献流程。
骄阳依旧暖人,院外那棵梧桐树上的燕巢,雏燕叽叽喳喳依偎在燕子妈妈的羽翼之下。
爸妈得知有车祸死亡的年轻人愿意捐出心脏,并且配型意外地很成功时,两人相拥而泣。
妈妈眼中都是庆幸和欣慰的目光。「我能见见那位好心人吗?」
妈妈,你不会想见到我的。
生前你就嫌我恶心,如今死的这么难看,更恶心了。
只是一瞬间,心里起了几分肖想。
我想,看到我的遗体时,他们也许会认出我吧。
也许。
最终他们只匆匆瞥了一眼,眼中有恐惧,有惋惜,也有本能的呕吐反应。
唯独没有认出我。
不一会,他们在我的遗体前欢呼雀跃,为哥哥的新生雀跃。
我的灵魂像个局外人一样凝视着他们,嘲笑自己的天真。
也是,生前他们都未曾正眼看过我,更何况是死后这个鬼样子。
兴奋之余,妈妈还不忘咬牙切齿,咒骂着记忆夹缝中偶然想起的我。
「一个陌生人都能伸出援手,那个死妮子呢!自私自利!只顾她自己,还不如死外面算了。」
她就是这样,总是喜欢在高兴之余,将我单独拎起来贬低一番。
习惯了。
她哪天不骂我呢?
骂吧,骂吧,反正也真的骂到死了。
想着想着,我的灵魂不免看着妈妈发笑。
为了给哥哥提供脐带血,自私自利的我被迫出生了。
五年级时,上一秒还在认真写试卷的我,下一秒被他们按在医院冰冷的手术床上,打入麻药。
我浑身发抖,好怕好怕,但怕向来是最没用的。
得知哥哥病情恶化需要心脏时,我趴在桌子上哭了好久,哭到纸页都被鼻涕黏在了脸上。
我甚至算着日子,爸妈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在我的房里,语重心长地劝告我。
「囡囡啊,你哥哥需要心脏,你不能不帮他。」
3
可我看着他们依旧忙碌,依旧愁眉紧锁,在我房前走来走去,这话始终也没说出口。
但出生时我就明白了,医生能宣告的不是哥哥的死期,是我的。
我特意挑了一张樱花信纸,认真地写起了诀别信。
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信纸上泛了花,甚至幻想着自己献出心脏后,哥哥恢复了健康,而我也终于久违地等来了爸妈的懊悔和爱。
我多想他们注意到我啊。
然而出门时差点和妈妈撞了个满怀,她嫌恶地看了一眼我肿地像核桃的眼睛,声音尖锐。
「哭什么哭,天天装那个死样子给谁看!」
窗台是妈妈很喜欢的小雏菊,我为她种的,她觉得碍眼,路过时一把推倒在地。
花盆碎了一地,连同我那颗心。
我跪在地上,合起掌心一把把捧起地板上的土,泪水浇了花。
我将那株小雏菊挪到了墙角。
妈妈不是觉得小雏菊碍眼,而是觉得我碍眼罢了。
我和她那如同散沙的母女情,风一吹,就散了。
彼此最后一面,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喊她一声「妈妈」。
哥哥的手术前流程很顺利,我的灵魂也关切地游荡在哥哥周围。
他侧着脸躺在病床上,即将要被推进手术室。
俊朗的容颜在若有若无的病气下倒添了几丝破碎美感,稀碎的黑发也遮不住那双如星辰一般的眼眸。
苍白的薄唇轻启,他左右张望,几分心慌的语态。
「哪里突然来的心源?男的女的?」
妈妈不在乎的语气:「女的。」
哥哥的额头立刻拧作一团,强撑着起身,情绪激动。
「昭月呢?这不会是昭月的吧!?」
爸妈脸上浮现几抹嘲笑,慌忙安抚哥哥的同时,一副尽在掌控的高姿态。
「淮安你就放心吧,这心要是你妹的,我把老命给你,就是一个车祸死亡的女人。」
说完妈妈好像是想起了那天目睹那女人惨状时的嫌恶,强忍着恶心。
「也不知道那女人造了什么孽,身上被碾的啊,脸上都看不到完整的肉了。」
爸爸也连忙附和。
「对啊,你妹那个死女子,她怕我们再打她主意,早不知道逃哪潇洒去了。」
哥哥紧绷的身体终于松懈下来,大大舒了一口气。
将哥哥送进手术室之后,妈妈就一直在哭。
爸爸有意无意看向手机通话界面,神情有些烦躁。
「昭月也不知道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干什么?」
4
妈妈不耐烦地勾过头看了一眼。
「要不打过去问问?」
突然又烦躁地否认。「算了算了,打个屁,一天天就她事多。」
「总是那副死样子,我们生她养她还生出过错来了?」
「别管她,要死要活都随她,我看她还能反了天不成?」
爸爸摇摆的半点担心也终于消失。
「也是,真有事等会肯定又打来了。」
可他们不知道,我的电话再也不会打过去了。
爸妈事业成功的背后其实结了不少仇,要报复他们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他们原本要找的人是爸妈,只是我赶往医院的那天,正巧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我被逼到巷子的角落里,面对他们的狞笑。
「这不是何家的小公主吗?别怪我们,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稍微教训你一下。」
黑暗笼罩我的头顶,我背过身去,后背重重挨了一脚。
我手忙脚乱地拨打爸爸的电话。
一次,两次,三次,都被爸爸绝情挂断。
我认命般放下手机,剧痛中,无时无刻不期盼着哥哥出现,救我于水火之中。
可我知道,哥哥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命悬一线。
所以拳脚重重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只是想,再重一点,再快一点。
快点打死我,爸妈就如愿了,哥哥也得救了。
直到那一闷棍,不偏不倚地打在了我的后脑勺上,鲜血顺着眼眶喷涌而出。
那些人慌了,他们将我随意地扔在马路上。
一辆飞驰的汽车将我二次碾压,地上拖出了长长的血印。
而我的父母呢?正在肆意的咒骂我,不如死了算了。
从记忆中抽离,我的灵魂看着医生将我的心脏缓缓放入哥哥的胸腔。
可我对哥哥没有恨,只有眷恋和不舍。
甚至难以想象哥哥如果得知我的死讯,会变成什么恐怖的模样。
回顾我这短暂的一生,我的出生也许只是起到一个工具人的作用。
唯独在哥哥眼中不是。
……
我也曾猜想过,爸妈是不是生下我之后就后悔了。
是不是会想过「要是能只生脐带血就好了。」
是不是觉得我就像是一个不能抛弃的医疗废品。
那我也许就不会遗憾我这一生。
可我也曾短暂地拥有过爸爸妈妈的爱啊。
刚出生时,肉嘟嘟的小奶团儿,妈妈抱在怀里怎么看怎么稀罕。
两岁时,哥哥又开始频繁住院。
我已经学会不哭不闹在儿童围栏里一坐就是一天,日复一日。
爸妈走之前,积木在左边,洋娃娃在右边,我在中间。
天黑时那扇紧锁的大门打开,积木在左边,洋娃娃在右边,我哭累了睡在中间。
直到体检的时候医生警告我已经严重营养不良时,不习惯外人伺候的爸妈终于想起来请一个保姆。
为了人情,保姆请的是妈妈的远房表姑,满脸横肉的女人,惯会看人下菜碟。

5
我饿地直哭的时候,她就抱着我使劲摇晃,猛拍后脑勺,摇晕了我就不闹腾了。
家里没人的时候,她最喜欢一边抠脚,一边用指尖掐我肩膀的嫩肉恶狠狠咒骂。
「你妈摆的什么女主人架子,要不是她嫁得好,轮得到她吃香喝辣吗?」
「你个贱丫头就算好命投胎到这么有钱的家庭又怎么样?你爸妈只管你哥,根本就不爱你,贱命!」
姑奶经常一睡就是一整天,做饭的闹钟响了,她就关掉闹钟翻身继续睡。
我靠在床边,透过高高的窗台望向外面树枝上的鸟巢。
鸟妈妈衔着小虫一只只喂着嗷嗷待哺的鸟宝宝们。
我也有妈妈,可我的妈妈在哪里啊?
那天,我发了高烧,直到惊厥抽搐过去嗑瓜子的姑奶才发现,慌忙给爸妈电话。
那晚,原本照顾哥哥已经很累的爸妈抱着我又大吵了一架。
哥哥稳定之后,晚上妈妈还是搂着我睡的。
姑奶看不得妈妈平日贵妇的作派,故意将头发茬子塞我脖子的衣领处。
我又磨又疼,于是不停哭闹。
妈妈身心俱疲地翻身起床,将头发揉成一团。
「吵死了,已经够烦了。」
爸爸同样也没了曾经的包容劲儿。「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生二胎啊。」
「你现在倒怪起我了,不是你说配型遥遥无期吗?」
「我也说可以再等等啊,现在好了,难道你照顾吗?我够累了。」
又是无休止的争吵。
最后,他俩一致决定将我的婴儿床挪到了客卧,离他们比较远的房间,由姑奶晚上照顾着。
晚上又冷又饿没人管,哭得嗓子都哑了。
那扇紧闭的门撕开一片光,微弱的月光下只看见穿着蓝色条纹睡衣的哥哥。
他背对着我,略带生疏地学着姑奶的模样手指摸索着奶粉罐。
罐子太紧,盖子打开后猛然一抖,奶粉撒了他一身。
哥哥偏过头轻轻咳了几声,伸出指尖简单抖了抖,便继续捧起恒温壶倒入温水。
他那时也才六岁,却已经会有模有样地拍着我的肩膀哄我入睡。
见我笑,指尖试探性地戳了戳我的脸颊,声音小小。
「昭月,我是哥哥呀。」
我从未睡的如此安稳过。
他就这样半跪在我床边睡了一夜,第二天妈妈看见时心疼坏了,一边轻手轻脚抱起哥哥一边朝我用嘴型咒骂。
「要死啊!肯定是这死妮子晚上哭,吵到淮安了!讨债鬼!」
6
哥哥密密的睫羽缓缓张开,在眼下投了一层阴影,他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无论爸妈看得再紧,晚上他还是会摸到我的房间,守在我身边就是一夜。
直到哥哥因受寒肺炎住院,爸妈坐不住了,将姑奶臭骂一顿。
妈妈又对我恨,又对哥哥无奈,索性将我的小床搬到了哥哥房间。
隔着床栏杆的缝,哥哥伸出食指摸着我的手指头,露出一双小鹿般清澈的大眼睛。
「昭月,哥哥在。」
我知道,这就是哥哥保护我的方式。
小学时哥哥就已然像个小大人,经常像包饺子一样把我包在他怀里走路,任何人靠近我他都像贼一样提防。
初中毕业时哥哥继承了爸妈的优良基因,身高远超同龄人,窜到了183。
那堪称漫画般标志的神颜加上一身素净白衬衫,还被人偷拍上了热搜,把学校的女生们迷得五迷三道的。
要么说老天不公,哥哥不仅模样长得好,学习成绩还十分优异,霸榜年级第一。
因为常年与医院和药物打交道,哥哥的性格孤僻怪异,也不曾和爸妈交心,也没什么朋友。
明明温润如玉的性子,除了在我面前,永远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在他面前,我就像颗移动小地雷似的,学习中游,模样也在人群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可他看我就像看女儿一样,怎么看怎么稀罕。
晚上,我被好几页变态的数学题折磨地直蹦跶。
「怎么办?怎么办?写不完了哥哥,我怎么那么笨啊!」
哥哥单手支在书桌上,笑着将我按在他坚实的怀里,下巴磕在我的头顶轻轻蹭着。
「要是妹妹也聪明的话,要哥哥有什么用呢?」
说完捏起我圆嘟嘟的脸蛋,带着浅笑的帅气脸庞表情认真。
「好了,哥哥再讲一遍,要是听懂了,哥哥有奖励。」
他伸手将我揽进臂弯,头倚在我的肩膀上。
「你仔细看这道题型……」
鼻尖都是哥哥淡淡的香,和温柔的嗓音。
他不厌其烦地将题型揉烂,喂进我脑子里,在我终于想通笑出声时,他会从兜里摸出一颗大白兔递给我。
数学难题对于哥哥来说不难解,他最想要的是在妹妹心里满分。
我也一样。
在哥哥身边,我才有被保护的安全感。
直到哥哥病情不稳定再次住进了医院,爸妈没留下任何交代将我一个人扔给了姑奶。
他们总是说:「昭月你身体健康,还能活很久,但你哥不一样,你要让着他。」
我一时竟分不清身体健康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7
当天姑奶盘算着回乡下照顾孙子,将我锁在家里,等爸妈回来前再回来敷衍敷衍。
她如同零元购一样将家里搜刮一空,全塞进行李箱拿回去给小孙子。
冰箱里,只剩下一颗烂了一半的洋葱。
一直到下午,实在饿到不行,我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洋葱。
避开烂掉的那半边,咬了一口,腐烂的臭味中刚尝出一丝清甜,就被呛地满脸是泪。
不知是委屈还是辣的,我嗷嗷哭着,将洋葱扔进了垃圾桶。
这时候要是哥哥在,他一定会给我做好吃的。
他会先往烤箱里塞一块面包,再在平底锅上浇上几滴油,铺上咸香的培根,不一会香味就出来了,再卧上一颗晃悠悠的溏心蛋,简直香迷糊我。
可现在哥哥躺在医院里,我饿地咕咕叫的肚子根本不值一提。
生怕错过他们回来,我趴在上锁的大门地板前一睡就是一晚。
小时候,是趴在儿童栅栏里睡。
黑夜是会吃人的巨兽,一点点吞噬小孩勇敢的心。
我开始怕黑。
但晚上数次惊醒都只有冷和黑,无尽的冷和黑。
等到朝阳透过窗台,还是没一个人回来。
嗓子干痛,我打开水龙头仰头往肚子里汩汩灌。
喝完了又冰地肚子痛,蹲在岛台下捂着肚子哼哼唧唧。
下午的时候,我还是向饥饿举起了白旗,跪在垃圾桶前,去翻那颗被我咬了一口的洋葱。
一边生啃,一边闭着眼睛想象着这是哥哥给我做的美食,哭着吃着。
傍晚,百无聊赖。
我搬了张椅子靠在高高的窗台边向外张望。
小时候只觉得那个窗台好高,高到望不到外面,望不到未来。
回头间,发现花瓶旁的玻璃杯里还有半杯牛奶,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我如获至宝,摸着椅子下去,捧起玻璃杯三两口便将牛奶全都灌进肚子里。
饥饿让我完全无视了牛奶里悬浮着预示变质的絮状物。
一晚上,我上吐下泻,头晕目眩。
等妈妈推开门的时候,客厅里都是我吐的烂洋葱味儿,东一滩西一滩。
而我虚弱地歪倒在沙发上,肚子里翻江倒海。
她嫌恶地捂住鼻子,跺着脚大发雷霆。
「何昭月!你就不能省点心啊!吐得哪里都是,你去马桶里吐能死吗?真是恶心!」
「在医院累的像只狗,回来还不得安生。」

8
她谨慎地避开我的呕吐物,急着给姑奶打电话,问她去哪儿了,赶紧来收拾。
电话那头的姑奶声音谄媚,骗她说自己去买菜去了。
我耷拉着身体,来到妈妈卧室门口的时候,发现她正拿着卷发棒整理自己一丝不苟的发型,完全无视我的窘态。
「妈妈,姑奶走了,她不给我吃的。」
妈妈手上动作一顿,她明明听到了,却又继续若无其事地卷着头发。
还是这样,其实不止一次跟她说过姑奶对我不好。
她都是这样无视。
我扯着因失水而紧绷的嘴唇。
「妈妈,我要找哥哥。」
这句话好像莫名触碰了她某根紧绷的弦,她粗暴地拽起卷发棒就朝我砸过来。
我根本无力躲避,卷发棒砸在我的额头,「呲啦」一声。
高温之下,我额头的皮肉瞬间焦了。
她一瞬地紧张,好像意识到自己过了。
半晌又恢复了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找你哥做什么?你还想告状吗?何昭月,我们哪点亏待你了?」
「你不知道你已经很拖累你哥了吗?你怎么那么自私!」
「你就是不想让你哥好受是吧,我看你就是故意膈应我们。」
我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干脆往床上摊成一张,硬生生靠命扛过去,人都瘦了一大圈。
哥哥出院时,一眼就注意到我头上已经结痂的烫伤,和我瘦削的身体。
他坐在轮椅上明明虚弱地都快撑不住,细长的指节却认真在我额头摩挲着。
「怎么回事?」
瞥到妈妈威胁的眼神,我低下头,有些心虚。
「我自己不小心烫的。」
性格使然,哥哥虽然没说话,却总是一副什么都知道的眼神。
那天做完饭的妈妈推开门刚准备喊哥哥,就看见哥哥正拿着卷发棒按在他光洁的手臂上,嘴角带着嘲弄的笑。
皮肉滋啦作响,哥哥苍白的嘴唇紧咬,渗出血丝,硬是一声都没吭。
然而更恐怖的是,他卷起的裤腿下,大大小小已经烫了好几处。
妈妈几乎要疯了,拽住他的手臂,顿时哭出了声。
「你在干什么啊!你疯了吗?」
哥哥眼神有些疲惫地瞥向妈妈,笑容癫狂。
9
「以后昭月身上但凡有一处伤痕,我就在自己身上还十倍,反正我这条命也是她给的。」
「她是你亲女儿,你的罪,我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