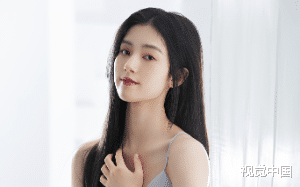监控画面上,灰暗的教室里有两个香艳交叠的肉体。
那女生因极度兴奋而狰狞的脸转过来时,清晰可见,正是全校唯一的寸头女生。
一
2016年,我因焦虑症退学一年后,决定重新参加高考,确定了柳光这所私立高中。
父母提前去考察学校,回来开玩笑似的说:
「小雨肯定喜欢这里,她不是讨厌公立学校紧张的氛围吗?」
从他们的口述中我得知,学校是一个三层小楼改造的,教室后面还有彩色灯球和拆掉的卡座,很显然以前是个类似KTV的娱乐场所。
据说倒闭后废弃已久,前年被校长买下,改造成了高中。
父亲说,从后院看,这里像精神病院。
「我们过去的时候,隔着防盗门往里看,那群学生就在院子里打闹,玩累了就坐成一排,在水泥牙子上唱歌。」
言下之意,是里面氛围轻松,与严格的公立高中大不相同。让我不必担心这里有令我复发焦虑的因素。
我忍不住疑问:
「这种学校不会是骗人的吧,师资能行吗?」
「没事,我们替你问过了,学校是从南岛市那边的高中建学籍,有高考资格,老师都是一中的。」
母亲握着我的手,委婉道:
「小雨啊,这是咱们县仅有的私立高中了,也是你唯一的指望,无论如何,你可得好好待下去。」
自我生病退学以后,她忧郁已久,我不想再让她担心。
我只得点了点头,掩饰住心中的疑惑与忐忑。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了学校,它在县城最北边的商业街,往里拐了好几次才看见,是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
仰头,一个并不显眼的塑料牌匾挂在上面:
柳光学校。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约莫三十出头的胖男人,他不是老师,而是校长雇佣来24小时看管学生的人。
学生们都叫他老许。
「家长不用进去了,你,跟我上来吧。」
老许掐掉了手里的烟蒂,吐出一口烟气,领我向后院走去。
我听到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
跟着老许来到后院,一股柴米油薪的气息混合厕所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不禁皱了皱眉,看到了院落一角狭小的厨房,挨着厕所。
「这边是食堂,」老许指了指与厨房相对的南屋,「还有小卖部,可以刷饭卡。」
我探身看到了那个仅有六七张长桌的食堂,问他全校有多少人,我所在的高一又有几个班?
老许似乎很惊讶,干笑了一声说:
「全校五十来个人吧,每个年级各一个班。高一……今年招的多,差不多有二十人了。」
这么少?
我不免讶异,与其称之为学校,说是补习班还差不多。
抬头看向楼上,有完整窗玻璃的窗口只有八九个,剩下几个都是腐朽的窗框,和黑洞一般有些可怖的房间。
高一在三楼,他带我进去时,里面正在上英语课。
我低声问老许现在学到哪里了。
他说,这里同学基础差,正在补音标知识。
音标……现在已经是开学第二周,按理说第一单元单词都该学完了。
「你坐那边吧。」
老许随手指了倒数第二排的空位给我,就转身回去了。
我顺从地过去,把书包塞进桌洞里,慢慢翻看课本,一边目测着整个教室。
同学们看起来都很文静,也没有烫染纹身的,有几个在后排睡觉。
下课铃骤然响起,老师最后一个音标还没讲完,就撂下粉笔匆匆离开了。
下一秒,我的旁边突兀的多了一个人。
一时间,我竟没分出这个人是男是女,只听到了粗噶的声音:
「新来的?」
我迟疑了片刻,迅速打量着眼前人。
她顶着一头短寸的头发,戴着一架鹅蛋形粉紫色塑料眼镜,皮肤黝黑,穿着断带的豆豆鞋,嘴里还叼着一根棒棒糖。
她冲我十分热情地笑了笑,翻出白眼珠(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的习惯性动作):
「你好,我叫焦欣,是从谷窦屯来的,住校生。你是哪个庄里的?」
「我就在附近住。」
她恍然,「噢,城里人啊。」
本着与邻为善的原则,简单自我介绍之后,我从书包里掏出一盒饼干送给她。
焦欣立刻高兴起来,眼睛精明地转了转,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
手却很诚实地接了过去。
「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希望与你成为好朋友。」我客套地说。
她小鸡啄米般点点头,笑得露出两颗微黄的虎牙。
看起来应该是好相处的。
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却没想到这是一段噩梦的开始。
二
父亲说的没错,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师资不错。
这里的学生普遍都是没考上高中,又不想去职高才来的,因此基础都较差。摸底考试后,各科老师就毫无悬念的都任命我为课代表。
听起来非常夸张,可事实上,这里压根就没有想要学习的学生,大部分是被父母强制送来的。
开学几日的热情很快就被浇灭下去,他们又故态复萌,每每上课都睡倒一大片。
由于没人听课,作业自然也收不上来,渐渐的,二楼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日日去交自己的作业了。
「你是一中以前的学生?难怪只有你能听懂。」
数学老师在我面前叹息着说。
这里的老师并不常驻,只是在有空的时候来上上连堂,有时候在职学校有事,不等下课就提前走了。
「还有一个学生,叫张升驰我记得,那回课上还能纠正我讲错的一个题,可惜就是不学啊。」
我愣住了,有些惊异于老师的话,并开始迅速回忆起这个男生。
张升驰比我来的早几天,一直在最后一排睡觉。
我甚至很少见他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外,有醒着的时候。
他从来不跟其他男生打闹,也没有人跟他说话,显得十分格格不入。
摸底考试时,张升驰并没有来参加,焦欣说,那天看到他父亲来接他请假离开了。
我回到教室时,恰巧看到了他正在吃饭。
桌面上,一个豆酱瓶子里塞满了炒豆芽,他左手拿着一个馒头,右手不知捧着什么,正不时往馒头上撒一撒。
我有些好奇,凑近瞧见,他手里居然是一捧白花花的盐。
他抬头注意到我。
这回,我看清了他的脸庞,是一个有着小麦色皮肤、狐狸般狭长的眼睛,面容温善的高个子男生。
我有些尴尬,第一次跟他搭话:
「张……张升驰,你怎么吃馒头就盐啊?」
他摇了摇头,露出憨厚的笑。
「你说错了,应该是吃馒头就馒头。」
他指了指塞满炒绿豆芽的豆酱瓶子,「这是中午给我妹妹送的饭。」
我听着他这似乎有些对不上前门楼子的回答,没有继续问下去,只是点点头:
「噢,我想起来了,你走读是因为还得给妹妹送饭。」
听班上的同学讨论过,张升驰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平日里都是他在照顾。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回到座位前,忽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对他说:
「数学老师夸你很有天赋,我觉得,你应该多在学习上下些功夫。」
他怔了怔,旋即微笑:
「知道了。」
上课了,老师还未到来,我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同桌居然一反常态,按时来到课堂。
她喘着粗气在我旁边坐下,显然是跑上来的,悻悻地说:
「老许在教室后面安了摄像头,以后逃课不好逃了。」
我眉头一挑,转头果然看到了后黑板上方的摄像头。
「那以后在教室里一举一动,岂不是都暴露了?」
虽然这所学校里管的并不严,只要不是男女生明目张胆的勾肩搭背、玩手机即可,上课睡觉都不算违规。
但一想到有监控窥视着自己的一切,我还是有些不自在。
焦欣向我勾了勾手,示意我凑近一点。
她呵出一口气,我敏锐地捕捉到了淡淡烟草的味道。
「你抽烟了?」
她发出有些妖冶的笑声,十分得意:
「这你都闻到了,我漱了好几遍口了。」
我并没有感到稀奇,因为平日里上厕所的时候,早就见识过一群女生在旱厕里聚众吸烟。
她偷偷将桌洞里一盒蓝色的烟盒露出一角,炫耀给我看。
我轻轻颔首,说:
「藏好吧,别被老许发现了。」
「来一根吗?」
「不了。」
我无意卷入这里的一切,来此之前,我就决定跟所有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没有必要合群,这所学校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时的我还天真地相信,只要我不惹事,事就不会找上门来。
焦欣自觉无趣,看到老师从后门进来,她连忙放倒了自己的板凳。
她突然对我说:
「同桌,你知道上课睡觉怎样做到胳膊不麻腿不酸吗?」
我摇摇头。
她自顾自地把凳子放倒后,抽出一本课本垫在了板凳的空格处,然后坐上去,把胳膊放在桌子上。
「这样,就不麻了。」
我敷衍的嗯了一声,手里已经翻开了课本。
焦欣耸了耸肩,「哦,我忘了你是学霸,上课不用睡觉。」
说完她就趴在了桌上,用厚厚的书立挡着,不消一会就睡着了。
我用余光偷偷睨着她,羡慕她优渥的睡眠。
自从得过焦虑症后,我就多了一个失眠的毛病,每晚睡得都很艰难,需要一两小时才能入睡,还浅到一丝动静就能惊醒。
她发出轻微的呼噜声,不足以打扰到其他人,却足以在我耳边形成蚊蝇般持续的噪音。
我无法专注听课,放下书正想推醒她。
侧过头时,却猛然注意到,她睡着不经意间撸起的长袖下面,露出了一截黑瘦的胳膊——
那上面长满了星星点点的粉色疮疡,有的还泛着破溃的脓液。
三
我浑身一凛,皱起眉头,第一反应是:会传染吗?
趁她未醒,我调开智能手表,悄悄给她的疮疡拍了张照。
我打算回家后咨询个线上医生问问。
难怪她桌面上经常放着一支青霉素类的药膏,却从不告诉我用途。
这时,她醒了,看着我从她胳膊上骤然离开的眼神,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慵懒地将手插进油腻的短发里,手肘支在桌子上。
「你看到了?哦,这就是普通的过敏,我过敏性体质。」
焦欣见我不说话,又补充道:
「不传染,没事。」
我表面上点了点头,实际心中疑云更甚。
这时,胃突然袭来一阵抽痛,痛得我弓起身子来。
由于早上起晚了,来学校之前没来得及吃早饭,我的慢性胃炎受不住了。
「焦欣,我能用一下你饭卡买点吃的吗?我忘了带钱。」
我艰难地咬字说。
她瞟了我一眼,犹豫片刻,还是将饭卡递给我。
我自以为平日予她的恩惠也不少,每天晚自习前母亲给我送饭,她跑下楼去接饭盒,比我还亲昵积极,就为了蹭我的饭吃。
我母亲也是变着花样给我做,有时照烧鸡腿,有时小酥肉,她都吃得不亦乐乎。
大部分时候吃得比我都多,以至于后来,她都不再去买晚饭了。
到了小卖部,我看到了一堆三无垃圾食品,还有一些我吃不了的长棍面包。
我皱了皱眉,只买了一瓶五元的瓶装酸奶。
当我拿着酸奶上楼,将饭卡还给她时,她看着我手里的东西,面色一沉。
「你买的安慕希?」
「嗯。」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奇怪的,旋开瓶盖喝了几口,胃里稍稍舒适了一点。
却明显注意到她眼神里亮晶晶的,吸了吸鼻子,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仿佛埋藏了千般委屈。
哭了?
我大脑有些短路,本想问问她怎么了,要不下午就把钱还给她。
她幽幽地说:「五块钱,够我一天的伙食费了。」
说完,老师就大踏步迈入教室,直接点了我去拿回学案来发。
我未曾在意她的神色,起身就去了办公室。
回来之后,她在前半节课一直自虐式的挑脓疮,挑完之后则用余光瞟着我,盯了整整半节课。
终于,下课后我闷声说:「你一直看我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她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平添了几分诡异。
我没有继续搭理她,兀自整理着课堂笔记,然后起身,拿着水杯准备下去接水。
「李泽雨。」
焦欣忽然拽住我的袖口,她力气极大,拉我一下子坐回位子。
接着,令我三观震碎的事情发生了。
她居然用那只刚刚挑过脓疮的手,一把攥住了我的脸,将整个手掌都覆在我眼鼻口上面。
我惊慌失措,「你干什么?」
「我就想让你把酸奶吐出来。」
焦欣毫无感情地吐字。
我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
她的手沾满了脓液和污血的腥味,直冲我鼻尖的一刹那,我推开她,跑到垃圾桶旁不住地呕吐。
早饭只喝了一袋酸奶的我,胃部经不住折腾,疯狂分泌着酸水,恶心到几乎连黄胆都要吐出来。
远远的,我在头晕目眩中听到她哈哈大笑,笑声都带着哆嗦的颤音。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配合啊!」
当我难以置信的回过头,对上她那恶作剧得逞的表情时,我明白了。
恶心吗?无比恶心。
不是那种呕吐过后就能消解掉的恶心。
一旦厌恶的种子在心底深深埋下,就再也不会有转圜的余地了。
班里其他人都冷漠地看完,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
只有张升驰过来帮我拍打后背,递来纸巾和我的水杯。
「你没事吧。」他低声问。
「谢谢,我……」
一时委屈涌上心头,我有些哽咽,回头对他报以一个感谢的眼神,漱口之后擦了擦嘴。
张升驰平时沉默寡言,却也只有他对我还存有一丝善意。
其他人呢?不过是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旁观者。
「她是体育生,我跟她是初中同学。以前她经常参与打架斗殴,你尽量不要招惹她。」
他轻声慢气的提醒灌入我的耳道。
我几乎怒极反笑,问题是,我何尝招惹过她?
那天在学校,我整整一天没有再搭理焦欣。
晚上回到家,我迅速打开手机,在某宝付费咨询了一位皮肤科医生。
「医生,请你看看病人这是什么情况?」
我把智能手表拍下的那张疮疡图发给了他。
对方沉默了一会,问我:
「Ta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同桌,开学到现在才被我发现,还涂青霉素类药膏,但不知道她长了多久了。」
我忧心忡忡地回复。
然而我并未意料到的是,接下来医生的回答,差点令我当场晕厥过去。
医生说,是梅毒。
「看图片,是很典型的玫瑰疹,说明已经到了二期的程度,涂药膏已经没用了,需要肌注青霉素。」
「而且这张图上的胞疹已经被挠破、化脓了,如果旁人密切接触过这些伤口,很容易造成传染……」
医生后面的嘱咐已经看不下去,我的视野仿佛被雾气蒙住,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她挑完脓肿的手抓着我的脸,一脸邪笑的表情。
一种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如数九寒天的噩梦里庞大的鬼魅。
密切接触……
会不会传染给我?
一段记忆迅速冷冰冰地浮现在脑海。
初中跟同学比赛骑自行车时,我曾意外摔倒,以一种劈叉的姿势扭曲卡到了车座上,直接导致了处女膜破裂。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裤子上那些血,也是后来自己上网查才得知的。
一旦我感染了梅毒,所有人只会认为我小小年纪不洁身自好。
连证明的机会都不会有。
十七岁就感染了性病……将会成为我终生无法洗脱的一个污点。
我捂住嘴,浑身颤抖,在黑夜里无声地大哭起来。
凭什么?她的浪荡行径,还要拉上我承担毁掉一生的风险?
四
1
第二天,我趁上午的大课间,向老许提出了换位的要求。
「我觉得,和她不是很合得来……」
他皱着眉头打断我,不以为意:
「才开学不到两星期换什么位?你是好学生,更要做好团结同学的表率……」
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下来,就把我噎了回去。
我知道自己此刻更不能说出她有梅毒的事情,只会被当做诬陷,说不准还会闹得人尽皆知。
毕竟,这个抠门的学校不可能花钱让她去医院做检查。
调位被驳回之后,我麻木地回到座位坐下。
而老许刚刚的话中还说,拢共就这么二十人,调来调去多麻烦。
也就是说,我将要忍受这样一个同桌,整整三年。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耐下心。
「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学习,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费心。」
在表面寒暄中,我又度过了几天。
每当她凑近我,我都下意识的不与她进行身体接触,并在她走开后,快速用酒精消毒液进行消毒。
然而,心中不免还是对那天的事情耿耿于怀。
好在我应该并没有被传染。
日子一天天过去,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她偶尔在耳边絮叨一些封建迷信,我也是左耳进右耳出。
不过今天晚自习,听到她像模像样的跟前桌描述一个故事时,我还是不免好奇,听了一下。
焦欣说,那年她们屯里淹死过一个怀孕的女人,好像是给人当小三,两家人都不认这个孩子。
此后经常有人看到一个长头发翻着白眼的女鬼在河边逛荡。
生前女人懦弱胆小,总是被欺负。可死后,以前欺负过她的人不是遭火灾就是车祸,竟都离奇地家破人亡了。
焦欣一边用唏嘘的语气谈论这些时,一边习惯性地翻起白眼。
仿佛和故事中的鬼女人形象重合。
我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收回耳朵,翻开了数学题。
「啧啧,看吧咱学霸吓得。」
她在我耳边发出尖尖的笑。
过了一会,我完全没有做题的心思,遂放下笔,扭头看向别处。
右后方的一角,张升驰正认真地修着一只修正带,当然不是他自己的。
认识了快一个月,我发现他就是那种所谓“老好人”的形象。
每天帮班里十几个住校生无偿买饭不说,还要接受他们的各种要求:
什么煎饼果子不要炸腐竹、烤鸭肠七分熟加辣子,甚至要每天早上跑好几个地方才能买到。
在学校里,大扫除最脏最累的刷厕所,大家永远都是甩给他干;连宿管大爷要他给热水管包保温棉,他也能立刻从数学课上撂下笔,积极地下去帮忙……
什么忙都帮,无怨无艾。
说好听了是乐于助人,说难听点,自轻自贱都不为过。
这时,乱哄哄的晚自习课堂突然安静下来。
我悄悄回头,看到老许正板着脸站在后门。
「闹什么闹,一群废物。」
他的语气似乎有些愠怒和急促,「行了,今天条子要来突击检查,都去对面先躲一躲。」
「抓紧时间,我不想说第二遍。」
我一时愣住,突击检查?
什么意思,难道这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违法乱纪事情?
见其他人都见怪不怪,默默地背着书包,从教室里鱼贯而出。
我抓住了后面张升驰的肩膀,问他这是什么情况。
他刚帮老许搬完资料,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水,压低了声音:
「你赶紧搬书,一会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告诉你。」
我的疑心更重了,连忙收拾好书包,跟他下了楼。
2
外面的天空飘起了雨,还有不时的电闪雷鸣。
在我们学校这座三层小楼对面,有一个叫“贝塔熊”少儿音乐培训学校的地方。
白日里,经常见有戴着红领巾的小孩来上课。
然而此刻是晚上七点,卷帘门都关起来的音乐学校,只有门口一盏血红的灯亮着,配上雷雨的天气,看起来有些阴森。
旁边走出来一个负责人,老许过去递给他一根烟,两人低语了片刻,最终对方点了点头。
他招手示意我们从后门进楼。
培训学校里面没有开灯,他让我们随便找地方先躲起来。
二十号人于是分头行动,几个男生似乎还特别兴奋。
我有些害怕,脚步紧紧跟在张升驰的后面。
直到跟他走到二楼,一个房间的门口,他停了下来,有些无奈地看着身后的跟屁虫。
「那,你跟我在这里躲躲吧。」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借着闪电带来的瞬间光明,我看清了房间上面的标牌:钢琴室。
里面有两架钢琴,其余地方堆满了杂物,几乎插不进脚。
我和张升驰放下沉重的书包,靠在窗帘下面,偷偷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果然如老许所说,有两辆车在尧光学校门口,里面下来了一批人。
我倚靠在墙边,推了推张升驰:
「张升驰,你还没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
他扭过头,在昏黑的房间里,他的眼睛分外明亮。
「你没跟这里的高二高三的交流过吗?」
我迷茫地摇了摇头。
通过他的解释我才知道,柳光学校是违规办学,对外其实是宣称卖培训资料的。
每次教育局来突击检查,学生们都要被迫搬到对面的少儿音乐培训学校里躲藏。
这样的戏码,每年都要上演好几次。
「一旦被那些人发现,不仅学校要查封,我们在南岛市那个学籍也泡汤了。」他叹了口气。
我想起当初缴付的高额学费,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可正如这里五十多个心知肚明的学生一样,在这座小县城,我们除了这所私立学校,根本无处可去。
在雷雨交加的窗口下,突然,一种漂浮的焦虑感慢慢蔓延上来。
这种紧张导致我心跳加速。
我比任何人都熟悉这种感觉,那是焦虑症发作前的躯体反应。
但我并没有慌乱,而是习惯性地摸向裤子口袋。
我经常在口袋放一个小药盒,里面装着我的抗焦虑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现在,里面意外的空空如也。
我愣住了,手脚和脖颈明显都僵硬起来。
「你怎么了?」
许是察觉我半晌不再说话,张升驰忽然问。
我强行压制着这种感觉,声音不免还是有些抖动:
「我……没事,我只是感觉有点,冷。」
「冷?」
张升驰闻言,立刻把自己外套脱下来,打算披到我身上时,又迟疑道:
「我不大常洗衣服,今天这外套又吸了潮气,不知道你是否嫌……」
我吸了吸鼻子,闭目脱口而出:
「不嫌。」
彼时,对面楼上检查的人出来了,却径直向音乐学校走来。
「去那个音乐培训学校看看吧。」有人提议。
没想到,一向老油条的他们看大门紧闭,竟然顺利找到了后门入口。
很快,我听到了鞺鞺鞳鞳的上楼声,心里咯噔一下。
「快躲到钢琴后面去。」
张升驰低声提醒。
我慌忙点了点头,正要钻进钢琴下面时,一时没有站稳,手倏然摁到了钢琴键。
陈旧的钢琴发出悠长又沉闷的响声。
在空寂诡谲的雨夜里,和雷声一起被吞没进滚滚云端。
「什么声音?」
有个男人在走廊尽头顿住,突然问。
我莫名其妙又想起今天焦欣讲的那个鬼故事,幽闭的恐惧顿时蔓延开来。
内心轰然崩塌,那种急性焦虑发作的濒死感,久违的侵袭上身。
大脑一片空白,心率骤然加快到迫于崩溃的速度。
我甚至清晰的幻听到,有人挣扎溺水的声音。
缺氧的窒息感,死神般紧紧扼住了我的脖子。
还有塞满身体的绝望。
我快死了。
五
1
「刚才是雷声吧,你听错了。」
是老许的声音,过了一会,两个男人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了楼梯口。
我拼命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惊魂未定地蹲下去。
鼻尖却正巧撞到他膛前。
他明显身体有些紧绷,惊讶地看着我。
「李泽雨,你怎么了?」
我没有说话,摸了下酸痛的鼻尖,脸微微发烫,却不是因为羞赧。
而是刚刚九死一生的窒息。
在急性焦虑患者发作时,通常会感受到强烈的濒死感,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接触到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诱发条件有很多,对我来说,幽闭缺氧的空间、紧张的氛围……通通可以成为杀死我一次又一次的利器。
虽然不会真的死,但每每劫后余生,都像普罗米修斯被鹫鹰啄食后重新生长的内脏。
那种心理阴影,久久无法抹去。
我再也控制不住那根随时可以崩断的弦,蜷缩起来,浑身发抖。
「我,我害怕。」
或许是我此刻的状态有些可怕,像极了一个失心疯。他不知所措,下意识的用外套围住我,一边拍打我的肩膀:
「好啦,都走了,不怕……」
那天之后,回归正常的学校生活,我再也没有忘记过在口袋里装小药盒。
我和张升驰的接触多了一些,偶尔会拿有难度的数学题和他一起讨论。
如数学老师所言,他真的是学数学的天才,总能另辟蹊径,给出一条我从未设想过的解题思路。
我曾问他,为什么中考会落榜。
他说,自己不喜欢文科,上文科课睡了三年,于是中考在数理化生都A的情况下,以其他的五门全D而落榜。(我们这边公立高中最低的录取规则是2A3B3C1D)
他说好在,家里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学习很好,有望考上一中。
「将来就让她光耀门楣吧。」
他说得很云淡风轻。
我突然想起了他每天给别人无偿带饭的事,于是问道:
「我一直有个疑问,你为什么要对那些毫无干系的人好?」
甚至卑微到了尘埃里。这一句我没有说出口。
「你指的是什么,像傻子一样给所有人无偿带饭么?」
他轻笑。
「呃,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那么无私奉献。」
我心想,可不止是这一桩傻事。
他看了我一眼,喝了口掉漆保温杯盖里的水,向我讲述起他的经历。
「我成长的环境不是很好,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我妹妹小婷,基本是被我一手拉扯大的。因此从小我就很忙,很忙,以至于很少与别人打交道,甚至还不修边幅。」
「初中的时候人人都玩手游,玩卡牌,而我对那些从来都不感兴趣——其实是为了省钱。由于不合群又沉默寡言,他们就经常欺负我,我中午带饭盒吃饭,出去洗个手的工夫,回来打开饭盒,就发现里面被灌满了泥巴水搅成一团。」
他默默道。
我已经开始生气了,「那你为什么不反抗?」
张升驰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反抗过一次。结果把别人的鼻梁骨打断了,还赔了很多医药费,我爸回去之后把我吊在树上,扒光衣服,用皮带抽了我一晚上。」
「从那以后,我的自尊也随着那夜的鞭打消失了。」
他抬头,似乎非常释然,对我露出无所谓的笑容。
他连半分恨都没有表现出来。
我莫名感到鼻头一酸,我与他虽是萍水相逢,却又那么巧合的相似。
曾经的我,何尝不是这样谨小慎微,处处小心,却还是遭受了他人的欺凌和羞辱。
后来,也一度变成了同样的讨好型人格,同时也经常焦虑不安,直到后来彻底诱发了焦虑症。
我犹记,那个大雨倾盆的下午,几天几夜无眠的我像个毫无力气的蜗牛,缓慢又笨重地拖着书箱,狼狈地退学。
像个还没征战沙场就宣布自己死亡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