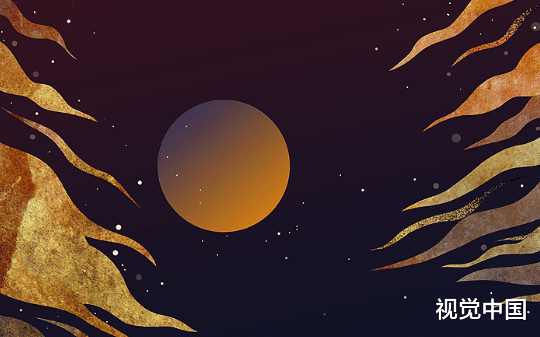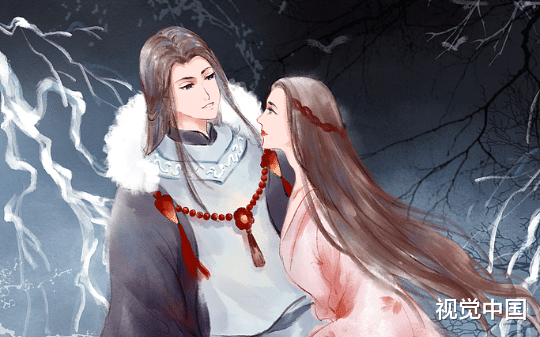作为寄人篱下的孤女,我刚满十五,便被姨母塞到表哥身侧,做了他初尝人事的通房。
表哥瞧不上我自甘下贱。
每日与我贪欢都是草草了事,眸光低垂,看也不肯看我。
随后,便叫下人给我灌下避子汤。避子药性寒,喝得我月月腹痛难耐。
这日我葵水刚过,痛意牵扯着身子发抖,竟不小心吐出刚喝下的汤药。
他眉头一蹙,冷道:“再熬一碗,掰开嘴灌下去!”
“别妄想,你可不配怀我的孩子。”
苦涩汤药灼烧胸腔,也烧灭了我最后一点幻想。
我自请离去。
他片刻愣神后,不屑地冷声哼笑:
“忘恩离家,当受叩首游街之刑。我们侯府对你有七年养恩,如今想走?没门!”
后来,京城百姓都瞧见那寄宿侯府的孤女一步一叩首,满面鲜血跪走长街,还了姨母表哥收养之恩。
恩已结清,我不要他了。
1.
被灌了一碗滚烫避子汤,我喉咙灼得生疼。
癸水未尽的痛楚又紧随着阵阵袭来,逼得我蜷缩在床脚,轻声呻吟了几句。
“矫情什么?不就是喝了碗药吗?”
表哥顾修竹沉沉眸色中,闪烁几分鄙夷。
跟了他两年,我不知喝了多少碗避子汤。
药汤苦口,入腹寒凉。
彻底伤了我作为女子的根本。
月中葵水的阵痛次次加重,以致于蔓延上了胸腔,激得我呕出避子汤。
顾修竹不关心我咳嗽,只皱眉吩咐下人快熬一碗新药。
不等热气散,掰开我嘴灌了下去。
“别妄想,你可不配怀我的孩子!”
心痛身痛笼紧神经,我茫然睁眼,咬牙挨到天色泛白。
2.
清晨,我还得去姨母身边请安奉茶。
她是我世上唯一血亲,五官与娘亲一般无二。
每每伺候她,我总觉着是在给早逝娘亲尽孝。
可她一见我却怒气冲冲,怒骂道:
“跪下。”
昨夜我呕出避子汤的事,顾修竹来告状了。
“陆见微,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已经承了侯府养育之恩,怎么还不知本分?竟还想有孩子?!”
她冷言说着,将一碗滚烫茶水放在我手上。
开水灼得我手指又痛又痒。
看我哆嗦,姨母眉头一皱,又吩咐人加水。
“再烫点!”
“一个通房,若连敬茶的烫水都受不了,日后可怎么本分伺候主母!?”
我咬牙忍下疼痛,头垂得更低了些。
期盼做小伏低能换来姨母的一丝垂怜。
不知跪了多久,却瞥见顾修竹神色匆匆自屋外赶来。
我以为他是来为我解围,欣喜抬头,却发现他正满面春风牵着一位红衣姑娘。
一眼都没看我。
“母亲,我把文清带回来了。”
柳文清。
名动京城的第一才女,是顾修竹在宫宴上一见倾心的白月光、心上人。
更是我未来要跪拜伺候的主母。
方才冷面待我的姨母满脸堆笑,拉着柳文清坐上主座。
寒暄许久,柳文清目光才落到我身上。
“这位姑娘是?”
顾修竹眸子中渗出些不耐烦,轻声道:
“一个贱妾罢了。”
“母亲要跟文清说说话,你别在这碍眼。滚出去。”
跪到双腿酸麻,我一瘸一拐扶门出去。
听着身后他们欢声笑语,抬眼再看四周下人不加掩饰的讥讽目光。
忽然觉得疲惫。
我这一生都要这样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吗?
天下之大,我偏要在顾修竹身边耗费终身,苦求一份施舍吗?
我不想。
早前不走,不过是想报答姨母养育我的恩情,现下顾修竹要迎心上人进门,我若还死赖着不走。
恐怕恩还不完,反倒结仇。
回到阴暗逼仄的住处,我收拢好为数不多的行李。
下定要走的决心。
3.
侯府内张灯结彩,红绸满天,不日便要迎柳文清入门。
我知晓姨母忙前忙后,身子支撑不住。
细心熬了一碗汤药,送到她院中。
顾修竹来开门,一看是我,立刻不耐烦侧过身去。
却不料闪身勾住了我衣衫,将我整个拽倒。
黑漆漆汤药泼洒出去,落在了院中铺陈的聘礼上。
“对不住,我是不小心……”
我急得拿身上衣衫擦拭污痕,可几件绸缎粘上热汤后竟破了洞,越补救扯得越大。
顾修竹郁色越来越重,一席掌风扇得我踉跄倒地。
“陆见微!”
“什么不小心?我看你是妒忌成性,故意在文清进门前一日来找不痛快!”
我怔怔捂上红肿的半边脸。
怎么也想不明白。
原以为悉心伺候了这么多年,即便顾修竹不爱我,也能换来几分惜我,护我。
可他偏偏像个无底洞。
无论我怎样付出,都被划为理所应当。
吵嚷声招来姨母,她还想骂我,却被我三叩九拜的大礼堵住了嗓子。
此次上门,我本就想借着送药由头来跟姨母辞行。
见他们绝情,我更无意纠缠。
磕头道:
“姨母给见微一个容身之所,又养育多年,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为了这份恩情,我甘愿屈身做妾,伺候表哥饮食起居。”
“可如今柳姑娘要入府,我再没有颜面继续叨扰姨母表哥,也不敢给未来主母添堵。”
“恳切姨母表哥开恩,允我离去。”
字字掷地,发自肺腑。
本以为顺了顾修竹的意,一拍两散各自欢喜。
他却久久没说话。
四周静可闻针,忽的听他冷哼一声,讥讽道:
“一个被我玩过的破烂货色。离了侯府,谁还会要你?”
他越说越得意:
“讲花销,侯府这几年养育你的银子,你还得起吗?”
“论律令,忘恩离家者,当受叩首游街之刑。我们侯府对你有七年养恩,如今想走?没门!”
我没有例银,吃穿用度都要仰仗顾修竹恩赐,如若他强逼我还钱,我还不起。
我体虚气弱,若要磕头游街十里才能与侯府断绝关系,更做不到。
所以顾修竹不信我能舍下依附他的日子,不信我能还清这份养育的欠账。
更不信,我有能耐跪着走完叩首游街之刑。
4.
可我并非生来就欠他们。
八岁前我也有父有母,可惜爹娘在岭南从医救人时染上瘟疫,撒手人寰。
他们临终前放不下我,颤颤掏出一本泛黄的合亲庚贴。
告诉我,曾帮我和姨母家表哥定了娃娃亲,我可以拿着婚约凭证投奔倚靠。
姨母不认这门亲事。
却怕我对外指控她背信弃义,干脆一碗迷药,把我变成了顾修竹的通房。
还假惺惺抹眼泪:
“让修竹收了你,姐姐在天之灵也能安息。”
“今后我们还是一家人。修竹正妻进门之前,你该谨守规矩,好好伺候他的生活起居。”
我怔怔望向四方天地之外,跪到院外的大红灯笼烧熄。
从床下拖出娘亲留给我的遗物。
有我满月时打的金项圈,有她备好送我出嫁的双玉镯……
物亮如新,可我再没有娘亲了。
我狠心绞碎金器,掰出一块买通后院看守,找了间当铺。
爹娘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念想,被我换做几张薄薄银票,买一份未卜的自由。
管家账簿写得明晰,我花了一夜,整理所有其中涉及我的开销金额。
七年来,我衣食跟下人同等,不允出行,不让读书,首饰脂粉一概没有。
只花了侯府五十两。
原来顾修竹高高在上要我还的账款,只有五十两。
5.
翌日,我早早扣开府衙大门,将账簿与银票交予府尹公证。
“这,这。”
府尹满头大汗,刚想叫人去通知顾修竹,却响起今天正是他迎娶柳文清的大喜日子。
“夫人,您要不再等等?今天长街估计满是顾侯爷接亲的人马,您当众叩首受刑,恐怕……”
我摇头。
“不,就今日。”
“我一日也不想多等。”
衙役已经就位,只等着为我引路受刑。
我敛袖跪倒,在长街人海中,对天地重重叩下响头。
石子路粗糙。
没几步,我额间鲜血淋漓。
围观路人越来越多,知晓我身份后窃窃私语。
“侯爷娶正妃,小妾在这上蹿下跳!我看她是想以退为进,跟正头夫人争宠啊!”
“我听说这妾室身份不一般,是老夫人亲姐姐的女儿。”
“亲侄女怎么只给了个通房身份?老夫人忒不地道。”
“要我看,这孩子瘦如枯柳,不知遭了多少虐待。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啊。”
……
我磕到街尾,鲜血淋漓而下,淌进眼睛刺痛酸痒。
可自由的曙光却越来越近。
先前质疑我做戏的人闭嘴不言,府衙在一旁直叹气。
“好了!”
他递来写着“陆见微”的户籍凭证,上面以重墨涂去了“客居侯府”标识。
此后,我和他们再无半点关系。
我只是陆见微。
正当我艰难起身,将凭证收好准备离去之时。
一阵喜乐飘然而至,刺耳非常。
“你在这里干什么!?”
顾修竹沉着脸,涨得比身上喜服还要红。
“来人把她拖回去!别在大喜的日子丢人现眼!”
自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自视甚高。
自然也想不到,我不惜磕到满头鲜血也要和他划清关系。
我冷笑:
“侯府养育我的账款已经还清,背弃养恩的刑罚已受,你我现在毫无关系。”
“让开!”
顾修竹满不在乎,还要上前:
“养恩结清,还有夫恩!你与我同床共枕两年,身子早就归我了。”
高傲如他,从来都只是将我当成一个玩物。
玩物的归属权不能由自己定夺。
可我是人。
我笑了,摊牌道:
“我从没有真心想当你的妾室。几年做小伏低,不过想偿还姨母养育恩情。”
“你恨我爬床毁了你清誉,我更恨你道貌岸然,既贪图我伺候,还要作践我来发泄私欲。”
“当年纳我入府并未过明路。”
我不是侧室,不是姨娘,只是个连名分都没有的通房丫头。
“我和你,从没有夫妻之恩。”
他轻蔑一笑:
“原来闹来闹去,是想要个名分。”
“好吧,明日我会求母亲出面,正式将你聘为姨娘。”
“你可满意?”
可笑。
四周围堵水泄不通,顾修竹人马步步紧逼。
僵持下,花轿中忽的传来娇嗔女声:
“夫君?外面怎么突然停住了?”
“再不走可就赶不上拜堂的好时候了。”
一听柳文清撒娇,他眉目郁色一展而空,回头冷冷看着我。
“今日你在接亲路上添堵,我不计较。马上给我回去,我可以按诺言给你名分。”
“不然你一个身无分文,又被我破了身子的贱人,在外面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我释然一笑,“我要如何,和侯爷无关。”
屋檐下,路缝中,钻出点点绿意野草,顽强自在生长着。
野草尚可绝境中求生。
我凭什么要对他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