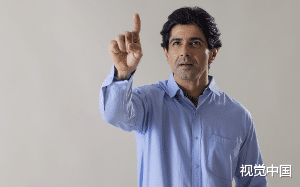1
临近年关,小小乡村里,已经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
就在万家团圆之际,我却收到了哥哥传来的噩耗。
“弟啊,妈妈去世了。”
忍着巨大的悲痛,我们打算将母亲留下的遗产——12万元全部取出,好为母亲操办丧事。
谁知,另一场“浩劫”正在等待着我们哥俩。
“办不了,那么大笔的钱,一定要本人来的。”
柜员满脸不耐烦,银行卡被她斩钉截铁的扔了出来。
“已经去世的人,怎么能亲自来呢?这简直就是为难人!”
我和哥哥又悲愤又伤心,我握紧拳头,心生一计。
第二天,我和哥哥披麻戴孝,一人捧着骨灰盒,一人手握灵幡,一路撒着纸钱,来到了银行大堂。
“妈妈啊,我们也不想折腾您,但是不请您来,事情就办不成啊。”
我们一路撒纸钱一路哭丧,有好事者已经拿出了手机,将这奇葩的一幕拍摄下来。
一场“好戏”开演了。

2
我叫刘小海,今年24岁,是一名泥瓦工。
我家在西南边陲一个小乡村,那里土地贫瘠,路不好走,村里能干的后生成年后几乎全部外出打工——没办法,家中土里刨食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我也不例外,17岁差5分没考上高中,我毅然决然决定进城谋生。
走的那天,母亲拄着拐杖,惦着跛得厉害的两条腿,将仅仅带走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床补丁摞补丁旧被褥的我,送了一程又一程。
母亲是个伟大的女人。
她自幼因为小儿麻痹落下残疾,长大后说亲也因为腿脚不便而不顺利,外公为了尽快摆脱这个“累赘”,将她嫁给我爹——一个远近闻名的酒疯子,生下了我和哥哥刘小山。
父亲嗜酒如命,暴戾且自私,家中大小活计,都靠残疾的母亲操持,她佝偻着背,将我们两兄弟拉扯大。
记忆中,父亲总是向母亲要酒钱,不给就是一顿暴打,哪怕是给了,晚上喝得醉醺醺回家的父亲,仍旧要殴打母亲。
母亲娇小的身体,跑不远,跑不快,只好默默承受着这一切苦难,还要小心翼翼的将我们兄弟俩护在身下,以免被父亲误伤。
童年的一幕幕,苍白,苦涩,等熬到我和哥哥上了小学,能帮着母亲干点活了,意外袭来,醉酒的父亲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深夜,走到村头大槐树下,被一辆面包车撞死了。
噩耗传来,尽管多年受尽这个男人的折磨,可母亲还是悲伤的哭嚎了几天,反而我和哥哥,暗暗松了一口气。
转眼间,我和哥哥都长大了,母亲身体不好,时常病痛,需要人照顾,哥哥将外出看世界的机会留给了我,自己继续守着家中两亩薄田和的母亲。
直到今天凌晨,我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响铃一声急过一声,像是一道催命符。
“母亲,母亲不行了,弟,你快回来!”

3
坐上最快的一班高铁,我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
年关将至,临近村口已经传来了零星的鞭炮声。
老屋还是我离开那年的样子,灰白的瓦片上挂着冰凌,场院边的柴垛摞得整整齐齐,家中的黑狗冲过来亲热的舔我的手。
走进堂屋,迎面而来的是母亲的遗照,身旁是泣不成声的哥哥。
“弟,你可回来了!快,来给妈磕个头。”
听哥哥说,前两天他因为二姨家嫁女儿,早早前去帮忙,说好晚上吃席的时候,将腿脚不便的母亲用三轮车接过去,谁知下午回家接母亲,母亲独自一人栽倒在灶台边,已经没了气息。
“我们哥俩不孝,谁都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母亲也没能留下只言片语。”
带着巨大的悲痛,我们开始商量母亲的身后事。
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腊月里去世的人,需要在过年前办完丧事,而母亲在世时说过,身后事不要大操大办,更不要与当初土葬的父亲埋在一起。
“把我烧成灰,埋在后山那片橘子林附近就行,我最喜欢橘子的味道。”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为母亲擦脸、梳头、穿鞋,戴帽。
一套按部就班之后,我和哥哥赶紧联系了殡仪馆,一把火,母亲真的变成了灰烬。
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我和哥哥相顾无言。
“哥,我有话对你说。”
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开口。
“我也有话想说。”
“你先说吧。”
“不,你先说。”
我咬咬牙,率先说道:
“办葬礼这些天,我已经把积蓄花的差不多了,这些年在城里,学技术要钱,吃饭要钱,租房要钱,手头不宽裕。”
哥哥低下了头,满脸愁容。
“我知道你难,我这边也不乐观啊,家里妈当家,我手上的钱很有限,都交给妈替咱们攒着呢。”
“这么说,妈那边应该有遗产?”
我俩合计着,开始到母亲的房间翻找,这么一找,果然有收获,在一个掉了漆的就饼干盒子里,我们看到一个信封。
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