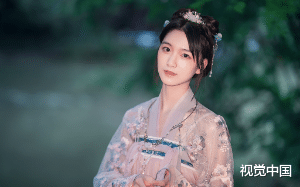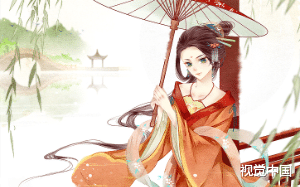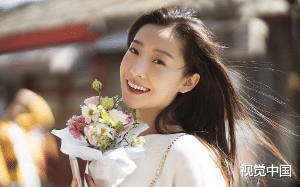江府的二小姐要和杜家二郎成亲了。
大婚当日,十里红妆,满街飘香,送亲队伍从城东排到城西,据说新郎官丰神俊朗,新娘娇俏可爱,实乃一对璧人。
没人记得,这婚约的原主是一年前被扔到乱葬岗的大小姐。
所以也没人注意到,大小姐从乱葬岗里爬回来了。

1
我回到江府时,杜泽正牵着新娘子,对我父亲敬茶。
杜泽笑着躬身,我妹妹江盈雪也跟着俯身,我的父亲接过茶轻抿一口,眼里含泪说了些什么,一派其乐融融。
我闲庭信步地走进堂前,打破了这份阖家欢乐。
「父亲,好久不见了。」
我身后跟着数十个侍卫,他们手中剑一出,那些想拦住我的下人纷纷止步,不敢上前。
听出我的声音,堂上堂下、跟着我进来凑热闹的众人皆惊愕地看着我,活像见了鬼。
想来也是,毕竟我可是早在一年前就“死了”。
一片沉默下,江盈雪失了体面,不顾形象地掀开盖头,见我活生生站在眼前,笑颜如花地看着她,她吓得小脸煞白,配上大红的嘴唇,更像个女鬼。
「柳……柳明珠?你是人是鬼?」
我朝她森然一笑,「你说呢?我的好、妹、妹?」
「当初你一刀刺进我的心口,如今,我这里还会隐隐作痛呢。」
我抚上心口,满意地看着她颤抖了一下。
「不知妹妹午夜梦回时,可否记得那天,我倒下时还朝你伸出手,你拔出刀,双手沾满我的血——」
我的话还没说完,江盈雪浑身战栗,惊惧之下,她白眼一翻,直直朝地上倒去。
“砰”的一声重响,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杜泽手忙脚乱地扶起江盈雪,一边差人喊大夫,一边心疼地轻唤江盈雪的名字。
「站住。」
我缓缓开口,身后的秋雁立刻上前,一鞭子抽在下人脚下,清脆的鞭声炸雷般响起,几个下人腿一软,跪倒在地。
杜泽强忍着害怕,声音颤抖地质问我:「柳明珠,你这是何意?无论你是人是鬼,都不该害你妹妹……」
有侍卫搬了把椅子过来,我施施然坐下,才不紧不慢道:
「这是我柳府,我让谁干什么,谁就得干什么,你杜泽有什么插手的余地?」
「你胡说,这明明是江府——」
杜泽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他。
「明珠,你还活着?」
我抬眼望向说话的人。
我的父亲站起身,正双眼含泪地看着我,肥胖的脸上混杂着激动、狂喜与不可置信。
若不细看,谁能看出里面的不甘心呢?
我看着这个道貌岸然的虚伪男人,不禁开心地笑了。
「对呀父亲,我若不活着,又怎么回来讨债呢?」
2
我是柳府的大小姐。
柳家世代做官,当今圣上还是太子时,我的外祖更是做过太师,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外祖母也是高门贵女,两人成婚十年,才得了我母亲这一个女儿,自是千娇万宠着长大。
我母亲及笄后,外祖不舍得她嫁人,便与外祖母合计,从当年进京赶考的学子中挑选一个相貌端正、家世清白、品学兼优的,要他入赘柳府,而我外祖会尽全力为他铺路。
挑来挑去,便选中了我父亲——江远道。
那时,江远道确实优秀,他自幼丧父,少时母亲也过世了,一路头悬梁锥刺股,终于过五关斩六将,考入殿试,我外祖看他是个可塑之才,常把他待在身边,倾力培养、不吝赐教,加之柳府倾力相助,他这一路官运亨通。
与我母亲成婚后,江远道温润柔和,与我母亲郎情妾意、琴瑟和鸣,外祖很是满意,再加之自己慢慢衰老,在母亲生下我之后,外祖便渐渐不管事了。
一直到母亲再次怀孕,快要生产的时候,府上突然传来外祖病重的消息,太医医治了七天,外祖还是没挺过去,外祖母伤心过度,也跟着去了。
母亲听闻噩耗,动了胎气,难产生下妹妹江盈雪,便撒手人寰。
彼时我刚刚三岁,江远道在人前悲痛欲绝,人后却无波无澜。一天傍晚,他抱着我,擦去我的眼泪后,对我说:
「珠珠,妹妹刚刚出生便没了阿娘,未免她日后伤心疑惑,不如就让她跟爹爹姓,好吗?」
那时的我根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想来江远道也不在乎我明不明白,只是为了寻个由头,改掉江盈雪的姓。
3
说来,我幼时也曾和江盈雪有过一段好姐妹情。
只是忘了从哪一天起,所有的错事都成了我,所有的好事都成了江盈雪。江盈雪人前哭着说「不关姐姐的事」,人后却字字句句辱骂我,说我不配做父亲的女儿,不配用柳家的东西,就连我曾暗自倾慕过的杜泽,也被她抢去。
久而久之,大家渐渐冷待我,宴会上没人同我说话,有时还会凑在一起奚笑我。提起江盈雪大家赞不绝口,提起我便是娇纵蛮横,每个人都在暗地里说我没有柳家的风骨,丢了外祖的脸。
父亲知道后,不听我的解释,只是一遍遍用失望的语气对我说:
「柳明珠,多学学你妹妹吧。」
「柳明珠,你真让我失望。」
「柳明珠,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
我也曾痛苦过,悲伤过,甚至怀疑过自己,觉得自己愧对母亲和外祖父母,半夜偷偷窝在被子里哭过数次,甚至想要一了百了。
可直到那晚,当我不小心听到父亲的话,怒气冲冲找江盈雪对峙。
而后,江盈雪一刀刺入我的心口,父亲抱着她轻言细语地安慰,接着他又提起刀,狠刺了我两下,冷冰冰地命人把我扔进乱葬岗。
我才知道,其实不是我的错。

4
我撑着下巴,扫了眼江远道冒冷汗的额头。
「父亲怎么满头是汗?见我回来,您不欢喜吗?」
江远道撑起个笑容,他假装拭泪,不动声色地擦了擦汗,再抬头时语气关怀,眼神却惊疑不定地看着我。
「珠珠怎么这么说?当年爹爹以为你已经……如今见你完好无损地回来,自是高兴的,正好今日是雪儿的大婚之日,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
这话一出,众人都偷偷交换着眼神。
毕竟谁不知道,当年外祖与杜家定下婚约的,是我呢?
我浑不在意众人的目光,朝后一挥手,便有个侍卫退下。
「父亲说得不错,确实是双喜临门。」
「既然如此,“喜”的另一个主角,怎么能晕着呢?」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秋雁一鞭抽开杜泽,提起江盈雪的衣襟,将她扯出来,侍卫去而复返,将手中提着的木桶翻转。
哗啦声响,在杜泽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中,一桶凉水尽数浇在江盈雪的脸上,冲花了她精致的妆容。
江盈雪打了个颤,悠悠转醒,一睁眼便止不住地咳嗽。
「柳明珠!你做什么!」
杜泽第一个冲了过来,他不顾肩上的伤口,脱下衣服披在江盈雪身上,而后紧搂着她,眼神淬了毒般看着我。
「她可是你亲妹妹!」
「杜郎,不是姐姐的错……咳咳……」
江盈雪人还没完全清醒,却已经下意识说出耳熟的话。
「雪儿,你就是太心软了,她当初嫉妒你我情投意合,想要杀你,如今又这般对你,怎么不是她的错!」
「杜郎,我……」
两人旁若无人地在一旁你侬我侬起来。
另一边,江远道也板起脸,朝我沉声道:「明珠,你今日死而复生,本是好事,可你怎么如此冥顽不灵、死性难改!一年前,你出手伤了雪儿,害她缠绵病榻数月有余,如今又在她大喜之日当众给她难堪,你真是——」
「真是对不起我死去的娘?」
我欣赏着自己染了蔻丹的指甲,淡定地接过他说的话。
「怎么一年不见,你们还是这老一套?没个长进吗?」
江远道被我这么一堵,一张脸憋得通红。
我又看向地上的两人,见杜泽还是一脸心疼,想了想,好心提醒道:
「首先,我这桶水只浇在她脸上,她的衣服哪里湿了呢?你不给她擦水,反倒给她披衣,该说你的情谊是真呢,还是假呢?」
杜泽一下子黑了脸,正要反驳,但我没给他机会。
「第二,你有句话可说错了。」
杜泽讥讽道:「哦?什么话?」
我挥了挥手,几个侍卫上前,杜泽连忙护住江盈雪。
「柳明珠,你给我适可——」
他的话还没说完,却见那几个侍卫脚步一转,从后面里揪出个妇人,压着她跪在我面前。
杜泽的话堵在了嗓子里。
众人被我这一手惊到,皆是大气不敢出。
所以没人注意到,江远道和江盈雪陡然苍白的脸色。
5
侍卫抽出刀,杀气腾腾地架在那妇人的脖子上。那妇人吓破了胆,哆哆嗦嗦跪在地上,不敢看我。
一片寂静,最先回过神来的是江远道。
「明珠,你这是干什么?」
我似笑非笑地扫他一眼,见他浑身紧绷,心下更是满意。
「父亲急什么?」
「你现在着急,一会儿还要感谢我呢。」
我蹲下身子,抬起那妇人的下巴。
眉若弯月,唇色饱满,眼尾还缀着一颗红色的小痣。虽然上年纪了,但也能看出弱柳扶风之意。
难怪……
「你叫什么名字?」
那妇人声音婉转,低低回答:「奴婢丁香,见过大小姐……」
我沉默不语,右手缓缓下移,兀地抓住丁香的手。
丁香吓了一跳,慌忙想要挣脱,却被脖子上的刀划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下,她登时不敢再动。
衣袖滑落,她腕上佩戴的,赫然是一只掐丝梅花金镯。
我抬起头,没有错过江远道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
众人看清这镯子的样式,一片惊呼。
我盯着丁香惨白的脸色,一字一句问道:「这镯子,怎么在你手上?」
「是……是老爷赏给奴婢的……」
丁香不敢抬头看我,只嗫嚅着回答。
我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撒谎!」
我看了秋雁一眼,对方会意,代我抓住丁香的手腕,狠狠一握。
「还不说实话!」
秋雁常年习武,力气大得惊人,丁香痛呼出声,却还是咬牙答道:「奴婢……奴婢不敢……说谎……啊!」
秋雁狠狠一掰,只听咔嚓一声,丁香的手软趴趴垂下。
我站起身,挑眉看着江远道。
「真的吗?父亲?」
江远道没有回答,或者说,他不敢回答。
因为这镯子,是他亲手给我娘打造的定情信物。
因用料稀奇、样式独特,我娘一直随身携带,死前都不曾摘下,因而京中不少人都认得。
如今,这镯子竟出现在一个婢仆身上,代表什么不言而喻。
江远道久久没有回答,我抬手摘下镯子,慢慢戴在手上,复又坐下,端详着镯子,话却是冲着江远道说:
「父亲,你知道吗?这一年,我经历了不少奇遇。」
「比如说,我被江盈雪当胸刺了一刀,却还能活着回来。」
众人哗然,杜泽也难以置信地盯着江盈雪,她开口柔柔说了句「不是」,我却没给她机会。
「又比如说,我竟然遇到了外祖以前的仆下,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
在江远道不甘到发颤的眼神里,秋雁掏出一样东西,当着众人的面展开。
「当年,你入赘我柳家,曾与我外祖定下契约,若你日后有负我母亲,便净身出户,柳家收回对你的一切助力,你看这字迹手印,是不是出自你与我外祖之手?」
虽这么说着,秋雁却拿着契书,给院内众人一一过目。
这些人中多是为官之人,受我外祖恩惠的不少,敬仰我外祖为人的更多,听我这么说,一个个仔细辨认起来。
「这……真是柳大人的字迹!」
「还有江大人的……确实如此!」
秋雁转了一圈,又回到我身边站定。
我扫了眼江远道,果不其然,他死死盯着契书,脸色黑沉。
「不知这妇人,是家贼呢,还是……」
「——父亲您的心上人?」
满堂寂静,都等着江远道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