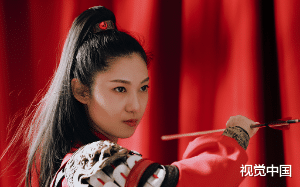夫君让我出府为有孕的妾室祈福,我闻言眼泪便止不住流了下来。
可惜,难过是不可能难过的,只能是喜极而泣罢了。
(1)
谢流第一次带芙蓉回府正是他从边塞归来之时,那天谢府体面人拢共二三十口都站在门口翘首以盼。传令官来了三遍还不见谢流身影,全家人都伸长了脖子往巷口看。
谢流去边塞两载得胜归来,莫说这谢府里的人,就是厨子老黄喂得那条狗都在眼巴巴望着。
在这气氛的烘托下,我也不由得开始激动,至于激动个什么劲却不知道。我同他成亲第二日他便匆匆领命去了边塞,而成亲那晚烛火太暗看不清楚,说句真心话他究竟长得是好是赖我都不知道。
当谢流骑着一匹黑色骏马到门前的时候,我仰头看去,阳光正好从他背后洒下,一身锦袍照的流光溢彩,薄唇凤眸,端的是一副好相貌。
可惜,可惜他看我的目光里分明带着戒备与敲打。
那仅有的疑惑在我看到那黑色骏马后面的马车时便全部消散了。
不管是鹅黄色的车帘还是旁边立着的绿衣丫头,都表明了这马车里坐的是个女眷。
原来啊,原来是带回来了别人,怪不得要那样看我。
我缓缓勾起了嘴角,面上是夫君归来的喜悦和欣慰,内心却满是嘲讽。
满京城里谁不知道我与谢流是陛下赐婚,如今新婚不过两年,他便大张旗鼓带着这样外室回来,还跟在他的仪仗后面,一路受了这京城百姓的欢迎供奉,也不知打的是谁的脸。
谢流下了马便同他母亲祖母抱成一团,我站在旁边静静看着,许是等了太久,那马车里的人按耐不住轻咳了一声。
我的好夫君便突然回神走到马车旁,甚至有些懊悔的神情, “蓉儿,我见了母亲祖母一时高兴便忘了你,你莫要怪我。”
而那女子自是拍了拍他的手臂表示安抚,然后盈盈跪下,“芙蓉拜见老太太、太太。”
我站在台阶上冷冷看着,一身白衣倒是显得她清丽脱俗,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略显臃肿的腰身,原来竟有了身孕。
许是顾及到我的颜面,谢府的下人们都此刻都鸦雀无声,只有目光不时的在我身上瞟来瞟去,太太跟老太太也震惊到了,一时间竟也不知说什么好,大家难得的默契,一瞬间街上静悄悄的。
许是受不了这样的安静,谢流终于开口:“芙蓉是我在边塞纳的妾室,如今已有六个月的身孕,这次便同我一起回府了。”
一瞬间所有人看着那女子的目光又全都落在了我身上,我身边的丫头绿珠则是一脸不忿。
我仍旧默不作声,想看看他们这台戏到底打算怎么唱。
谢母终于出了声:“流儿这一路舟车劳顿,芙蓉姑娘想必也是,我们还是先进府吧。”
“母亲说的对,先进府吧。”
我缓缓出声,谢母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奇怪,家丑不可外扬,当然先是要关起门来再商量这些丑事。
(2)
为了迎接谢流,我半月前便着手让人归置春晖堂,所有桌椅全换成了谢流喜欢的黄花梨,茶盏皆用上好的琉璃盏,帐子都用了江南新产的轻纱帐,甚至桌上摆的糕点都是我一一问过的,可惜此刻的谢流只挽着那女子眉眼俱开的笑着。
我说不上难过,以往我也不曾对谢流有什么期待,陛下赐婚,世家联姻,能相敬如宾已是极好,只是如今看来,我与他似乎连相敬如宾都有些难了。
“母亲,清儿如今已经有了身孕,这个孩子出生便是我的长子,儿子想着妾室的身份倒是有些不妥,不如就扶为侧夫人吧。”
听闻这话,谢母就先皱了眉,说道:“不可,清姑娘这妾室本就于理不合,念在她有孕在身,我谢府最多给一个良妾的名分。若答应就留下来,不答应便出府吧。”
谢母难得的硬气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不过这也不是为了我,谢母出身琅琊王氏,谢家也是百年贵族,若要真扶侧夫人,那也必然是一些高门的旁支小姐,这莫名其妙来的女人,谢母还真看不上。
“母亲,你不知道蓉儿是个医女,在边塞儿子有次受伤是蓉儿衣不解带的照顾,何况蓉儿日常在军营也为不少将士看诊,便是陛下也晓得清儿的功绩的。”
原是如此,谢流就算再混账也不至于带着随便一个女子明晃晃的归家,原是有所依仗。谢母闻言面上有了迟疑。
“既是于边疆将士有功,想必陛下会有赏赐,若是用这府中后院的位子当做赏赐,倒显得我谢府有些不懂礼数了。不过既然将军有意,不知贵妾如何?”
我抿了抿茶水,缓缓开口。
谢流缓了缓神色挣扎几瞬终是点了头。
他不是傻子,如今谢府中只剩两位太太跟谢流这一根独苗。
虽是高门贵族,主脉却也早已式微,我爹虽出身寒门,但如今已是左相。当时陛下有意缓和旧望与新贵的矛盾,便想着将我赐婚谢氏,何况谢家主脉衰弱,这段并不多见的文武联姻倒也无妨。
因着这桩婚事,谢流提拔成了正四品的官职,又被送去了边塞,不少人都觉得谢流有一份大好的前程,可是明眼人心里都清楚,只要我为谢家主母,谢家便只能是望族,不可为权贵。
说到底贱妾怎样、良妾又怎样,即便是做了侧夫人又如何?只要我爹还是左相,我赵玉琬便是谢府的女主人,那女子是什么名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她是什么名分都在我之下,如此,有什么好争的,倒不如卖了谢流这个人情。
(3)
我率先出了春晖堂后,没走几步谢流便赶了上来。
“赵玉琬,你入府两年无所出,按道理我是可以休妻的。”
谢流吐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差点以为我在幻听。
我要是这两年有所出,谢府才要炸上天了吧,莫不是边塞寒冷你迫切的想搞几顶帽子戴?
见我不动声色,谢流可能以为拿捏住了我:“如今芙蓉虽是良妾,但等她生产后,位份肯定还是要抬一抬的。你不要妄想与她争,只要你安分守己,日后你与她便是平妻,可要是生了什么龌龊的心思,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谢流走了之后我还在愣神,不禁疑惑道:“绿珠,你听到他方才说的吗?”
绿珠白了我一眼:“夫人,你没幻听。”
“那是谢流神志不清了?”
绿珠:“……”
“绿珠,我现在觉得谢流开始变丑了,他的脸已经拯救不了他残缺不全的心智了。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脑子有问题呢?”
“夫人,虽说这谢府没人能把您怎么样,但眼下芙蓉进了府,小姐还是得早做打算。”绿珠看着我一脸真诚,真让人感动,还是有人替我着想的。
不过白着想了,我是什么人?我是左相的千金独女!芙蓉时什么人?是无名无分入府为妾的孤女!她需要我准备什么?让她二十年她都未必赶得上我,现在是有谢流撑腰不假,可我也有我爹撑腰啊,这年头,野男人哪有自己亲爹可靠。
为了不触这个眉头给自己多生事端,那日回去后我便称了病。
芙蓉在府中穿着贡品蜀锦绣鞋招摇过市,我视若无睹;
要从公中出钱买翡翠阁的新款天价首饰,我一言不发;
觉得天冷要用老太太房中的金丝炭,我沉默不语。
并不是我多能忍,而是芙蓉如此作为实在不值得我把她放在眼里,她若是晨昏定省伏低做小我倒可能高看她一眼,不过她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各院的管事婆子们在我的房中吵吵嚷嚷。
“夫人,我们秋霜院的月份可是有好几个月没发了,管家说这个月府上还是没有现银?”
“夫人,眼下虽然还早,但往年庄子上该准备明年春播了,府上的资金如今还没下来,小老儿心里着急。”
“夫人,我儿子当年可是为了给老爷挡刀才走了的,如今府里还要扣我的抚恤金吗?”
原以为一个乡野女子捅破了天也无非是些首饰衣裳,没想到她也着实能花了些。
芙蓉这几个月来大手大脚,府上原本就捉襟见肘,如今更是不行了。谢流为了体面身份往往便是都挑好的来,府里多少双眼睛可都看着呢,下人们见我病着还得操心这些事情,不免都露出了同情的眼神。
到底有人长着良心,见我这样有些不忍,一个婆子站在塌边痛心疾首道:“也不知少爷是发什么疯,带回来这么个祸患来,夫人您受委屈了。”
“说什么委屈不委屈的,蓉姨娘毕竟怀着谢府的骨肉,谢府养着也是应该的。”说着我拿起帕子很合事宜的咳了几声。见状几位管事也不好再打扰,纷纷告退回去。
我病了,我装的。
我就是想看芙蓉能把这谢府搅和成什么样子,没有什么比置身事外静静看戏更有意思了。
(4)
第二日我收拾行李时谢流来了梧桐苑。
“赵玉琬你个毒妇!蓉儿进府时我以为你是个通情达理的,没想到竟能做出这种事来!”
大清早便听到谢流在院子里吵,昨晚熬夜看话本子本就睡得晚,这会又被谢流吵醒感觉整个人都是飘的。
步履踉跄的走到门口刚打算掀帘子,谢流在外面也正掀帘子进屋,于是直挺挺的撞到了我身上。
我能怎么办?我只能顺势躺下了。
谢流进屋就看到我面色苍白,形销骨立的躺在地上,乌黑的头发半梳着从胸前垂下,发红的眼眶里满是疑惑跟不可置信。
看到这样一番场景谢流稍微愣神了一下,大概没想到向来大红大紫穿金戴银的我如今会是这番光景。
“赵玉琬!你为何要害蓉儿?”
听听,这一说话还是如此的不中听。
“将军此话何讲?我何曾害过蓉姨娘。”
红玉终于来扶我了,早上绿珠准备早膳,眼下屋里只有红玉一个人伺候。
“蓉儿自从吃了你院子里送去的燕窝,便腹痛不止,你个毒妇就如此容不下旁人吗?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未出生你怎么下得了手?”
谢流指着我唾沫横飞,我借口咳喘便用帕子轻轻捂住了口鼻,这人可真是恶心,但眼里还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疑惑。
红玉见谢流这样子,早已按捺不住:“我家夫人何曾给过她燕窝,老太太知道夫人特意拿出库房中的上品血燕窝给夫人补身体。
谁曾想这燕窝还没进梧桐苑的门便被翠喜拦住说如今蓉姨娘身子也亏,又怀着长子,府中一切都得紧着她来。
硬生生把我家夫人的燕窝拿去了清荷院,若说有问题那也是老太太院子里的东西,将军不如去问老太太,朝我们夫人撒什么疯?”
“虽是出自祖母库房,可难保你们梧桐苑没有做手脚!”
谢流这个蠢货还在咄咄逼人,哪家贵妇会下毒下的这么明显,若我想针对她有一百种办法,下毒是最低级的一种。
“你大清早来玉琬院中吵什么吵,她如今还病着。”红玉忍不住回呛的话正到嘴边,谢母便带着芙蓉走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你身子可好些了?”看到芙蓉跟着谢母进来,谢流立马上前把人拥在怀里。
谢母的眼神越来越冷:“怎么我来得,她便来不得?”
“母亲,儿子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芙蓉今早喝了梧桐苑的东西便腹痛不止,儿子担心她。”
“倒是会攀咬,你自己说怎么回事。”谢母坐在主位端起了茶盏,眼神示意芙蓉道。
“阿流,我自己纵是如何也无关紧要的,只是我太想平安生下这个孩子了,便用了玉琬姐姐的东西。
姐姐出身丞相府,这些东西想来她是不缺的,便当姐姐可怜我让我保住这个孩子,可没曾想我到底不通药理,又没有姐姐身边的绿珠那样懂医术的人,这燕窝竟与一味安胎药相冲才腹痛不止。
阿流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太想生下这个孩子了。”
芙蓉说着便趴着谢流的怀里哭了起来。
“听到了没,那燕窝还没进梧桐苑便被拿走了,是她自己不中用。”谢母撇撇嘴,似乎不愿看见还抱在一起的两人。
“此事既与她无关,但芙蓉毕竟受了惊吓,按道理她身为嫡母,府中子女若出事都难逃其咎。芙蓉怀孕你也无法分担,不如就去金台寺为她们母子祈福吧,也算是全了你做母亲的心。”
谢流看着我诚恳的提出了建议,他竟然觉得让一个当家主母去给妾室祈福合情合理?
我闻言眼泪便止不住流了下来,可惜,难过是不可能难过的,只能是喜极而泣罢了。
金台寺的云烛大师声名远播,京城中的贵妇没有人不愿意听他讲佛法的。
倒不是贵妇们对佛法有多么精通,而是云烛大师实在是俊美无双。
“胡闹!”谢母出门的步子硬生生停住。
我生怕出变故,急忙说道“母亲,这样也好,在金台寺听听佛法想来也能的些佛祖眷顾。我替去您跟老太太祈福也是好的。我留下府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反而不利于我养病。”
缓了缓谢母开口道:“那也好,府里的事不用操心,你养好身子要紧。寺院清苦,山上想来也冷,我昔年得圣上御赐一件广陵长尾鸾袍,一并带着去吧。”
谢流父亲官升一品之时,宫中曾赐下不少东西,这广陵长尾鸾袍乃是九十九只鸾鸟尾羽所制,鸾鸟本就少见,要凑齐九十九只尾羽鲜亮毫无破损的鸾鸟更是难上加难,更别说那复杂的织造工艺,若是没有十几年的心血是制不成的。
谢母怕是觉得谢流多少有些离谱,便拿这广陵长尾鸾袍安抚我一番。
既然舍得将这件袍子给我那断然没有推辞的道理,道一声谢便得一件价值连城的袍子,划算得很。
(5)
因为怕谢流反悔,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带着绿珠往金台寺赶去。
红玉被留在谢府守家,毕竟我的嫁妆也有些,要是趁我不在嫁妆出了问题我可得心疼死。为着这事红玉从晚上便噘嘴不开心,好哄歹哄再答应把我的那支七宝琉璃钗给她,才勉强答应留下。
在金山寺的第一天,散步(猎艳);
在金山寺的第二天,散步(猎艳);
在金山寺的第三天,散步(猎艳);
三天下来,这寺里的小和尚我都见了个七七八八,只是云烛大师闭关去了,还不曾见过。
在第四天的时候发现这寺里俊美的和尚我都见过了,赵玉琬啊赵玉琬,这么点困难就难倒你了吗?要积极拓展范围!要迈出坚定的步伐!只要走得更远,一定会找到更加俊美的男子!
于是我去了后山。
很遗憾,在后山溜达了半天除了两只野兔连半个大型哺乳动物都没遇到,正在沉思猎艳之路为什么如此坎坷的时候眼角余光一闪突然看到对面山顶好像有个小屋,重要的是小屋前好像有个男子。
想到小沙弥曾说:“云烛大师正在后山闭关参悟佛法。”
这人不是云烛还能是谁,为了不打扰我跟云烛大师交流佛法,清了清嗓子对跟着我来的绿珠说道:“此处幽静,我突然心有灵至,在此地参悟一番,绿珠你先回去吧。”
“可是夫人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绿珠露出清澈而愚蠢的目光看着我。
“无妨,我既是来祈福,便得忘了这俗世的身份,你在这寺里也并非我的婢女而是一个信女,不必时时守在我身边,多和大师们参学佛法对你也是好的。
何况此处乃金台寺后山,佛光普照之地,我佛保佑不会有事的。”
绿珠的眼神里充满了感动:“绿珠听夫人的。”
看着小丫头远去的背影,我抬脚朝小屋走了过去。
行至小屋附近时云烛似正在练武,上身衣物早已脱掉露出紧致的肌肉线条,汗水顺着他的脸庞滑落。
真的是……好强壮的男人!
原以为云烛年纪轻轻便参悟佛法应当是清秀的长相,他抬起头来时我才发现这和尚长了一双桃花含情目,粉色的嘴唇更是如花瓣一般。
美中不足的是他见我到来一个闪身便穿上了衣服:“阿弥陀佛,贫僧冒犯了,女施主恕罪。”
云烛声音清冷低沉,低头向下看去,长长的眼睫毛看不清眼里的情绪,只是他发红的耳垂让我看出此刻心绪并不平静。
我莞尔一笑,转而往山下望去:“我不知大师在此处清修,若有打扰还望莫怪。佛语曾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何况你我这些皮相,大师不必介怀。”
听到我的话,云烛似乎放松了一些。
我回头微笑着看着云烛“可有人说过大师的甚美?”
听到这话,云烛睁大眼睛望着我,眼里满是惊讶,刚刚略微退下去的绯红又浮上了耳垂,缓缓后退一步说道:“还望施主自重。”
“这山间繁花、天边云霞、山中鸟雀都是世间美物,人生双眼便可区分美丑,我以为这应当是一句夸赞之语,不知大师此言何意?”
我眨着眼睛看向云烛,将绿珠懵懂的目光学了个十成十。
听到我的话云烛似乎有些羞愧:“是贫僧执着了,还望女施主海涵。”
“好了,不打扰大师清修了,玩笑之语,天色不早我该走了。”
云烛笑了,笑意直达眼底。
这笑容可真好看啊,他的眼睛明亮如山间小鹿,看着你的时候像山间露珠拂过掌中,清冽而闪耀。
我朝他摆摆手也笑了:“大师可要好好修习。”
他仍是双手合十朝我微笑目送我离去,我想云烛此刻的笑我会一辈子都记得。
(6)
夜间我在佛堂为长明灯添油的时候,窗边传来了声响,一个黑衣人从窗口跃了进来。
转眼一把冰凉的刀刃就抵在我身后。
“打发走他们!”
我错了,我应该多带点护卫的,绿珠不够用啊。
我浑身颤抖着点头,就差直呼好汉饶命。
很快有人便来敲门,我打发绿珠去开门,来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着京城巡防营的服饰。
“谢夫人,末将冒昧打扰。”来人向我抱拳施礼后说他是巡防营的校尉,又开口道:“今夜城中有贼人出没,我们追到金台寺那贼人便没了踪迹,不知夫人可见过什么可疑的人?”
我抬起头,朝他笑了一下说道“不曾。”
大约只觉得我是个深宅妇人,半夜打扰已是失礼,何况还是谢府的当家主母,我没有包庇贼人的理由,这将军面露纠结之色后终究带人离去了。
那一批人马刚走,黑衣人便怀里抱着剑从我身后走出,声音里是藏不住的好奇与戏谑:“传闻谢流的夫人出府为妾室祈福成为京城笑柄,如今看来谢夫人胆子也不小。”
我面上卑微,内心忍不住想骂人,嘚瑟什么,等你走了我就去举报!
那人却好像看透我的想法一般,“谢夫人一会也可以去将那将军找回来,只是那是我早已走了,夫人包庇的罪名可就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