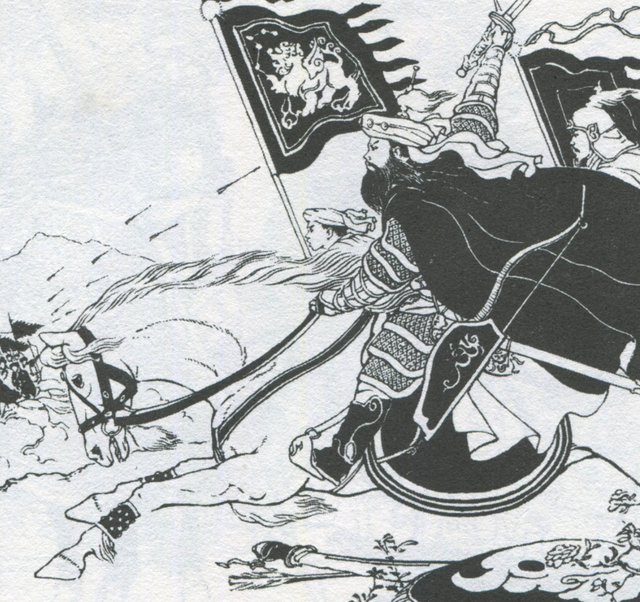1874年3月, 日本横滨市吉田桥大街上有个西方老人正在悠然漫步。他名叫爵柯卜·马克得诺,是从旧金山来的美国渔船“浪浦勒”号的船主。
街上人群熙攘,摩肩擦背。从前面的一个人圈子里,不断传来呐喊声。
爵柯卜挤进人圈,原来是两个壮汉在轮番殴打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周围的人们大声喊着:“阿衣喏壳!阿衣喏壳!”
爵柯卜问了近旁的一个西方人,才弄懂“阿衣喏壳”是日语“混血儿”的意思。混血儿难道不是人! ”爵柯卜按捺不住心中怒火,猛一拳就把一个凶汉击出老远。另一个凶汉拔出匕首就猛扑上来。
爵柯卜躲过那凶汉的匕首,顺势一脚,又把他蹬翻在地。围观的人一阵哄笑,两个凶汉狼狈鼠窜而去。爵柯卜拉过少年,抚爱地问: “他们是怎么打你的,不要紧吧?”
少年擦擦嘴角的血,用英语说: “我不让他们污辱我。”爵柯卜同情地问: “你叫啥名字,现在是让我送你回家,还是送你去医院?”
少年说他名叫富吉。他主人就是个医生,住在侨居地39号公馆,于是爵柯卜雇来东洋车,陪送少年到他主人家。
少年的主人是美国人,名叫黑浜。他对爵柯卜的仗义行为表示敬意,爵柯卜谦逊地说: “这算不了一回事…………”
黑浜医生感慨地说: “由于门户开放,西方人拥进日本,这就出现了混血儿,而这些无辜的孩子却遭到凌辱。富吉是我五年前领养的,我希望他能有新的生活。”
爵柯卜告辞了。医生热情地送至门外: “有空请常来玩,看看富吉。” “如果不离开横滨,我一定来。再见了,黑浜医生,富吉。”
时近黄昏,海风料峭,海浪有节奏地击拍着堤岸,爵柯卜边走边 想,他从富吉的遭遇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
爵柯卜的父亲是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河口一家皮毛公司的英国职员,而他的母亲却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的父亲出于生意经,娶了他的母亲。
他母亲生下他就染病去世。他从小在母亲的印第安部落里生活,学习印第安人原始的狩猎技艺,一直到9岁…………
父亲再婚,娶了一个爱尔兰女人。他失去母亲的温暖,一再逃回那幼年生活过的印第安部落。
父亲为了他的前途,把他送到加拿大,进了一所专为英国人办的学校。但就因为他是个混血儿,而被老师、同学所歧视,常常受到他们的戏弄。
爵柯卜忍受不了屈辱,就逃出学校,辗转流浪于加拿大、阿拉斯加州和墨西哥之间。做过牧童,也当过武器走私商的小伙计。
19岁那年,他上了捕鲸船,在白令海上充当水手。不幸,捕鲸船触了冰山沉没了。他被爱斯基摩人救起。爱斯基摩人的热忱,融化了他心头的冰块。
整整五年,他和爱斯基摩人一起生活,一同忍饥挨饿。他不但能又适应艰苦的环境,还提高了狩猎技艺,兼备了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特长。
他以一个技术高超的射手资格,被俄国人开设在锡特卡的皮毛公司所雇用。
他射击百发百中,任何海兽在他的枪口下都无法逃遁。这使他赢得了好名声, “混血儿”不再成为一面精神枷锁。
在锡特卡,爵柯卜结识了旧金山的美国皮毛商齐布罗克。他离开了俄国公司,在美国的海兽捕猎船上大显身手。
光阴荏苒,海水的盐霜染白了他的头发,海风吹皱了他的皮肤。这次他指挥海兽捕猎船从旧金山来到这里,准备在日本北方和俄国千岛群岛一带偷猎海獭。
由于珍贵的海獭已濒临绝迹,俄国的千岛群岛和日本的择捉岛虽然还有大量存在,可这两个国家严禁偷捕,该怎么办? …………他一抬头,已经来到了码头。
爵柯卜在积极做出航准备和搜集情报的空隙中,三天两头去拜访黑浜医生,看望富吉。他们的友谊越来越亲密。
有一天,爵柯卜带着富吉在码头上散步,讲述着大海和海员的艰苦生活。正在休息的码头搬运工,指着富吉齐声高喊: “阿衣喏壳!阿衣喏壳!”
富吉涨红着脸: “我跟他们拼了!”爵柯卜紧紧抓住他的手,深沉地说: “要沉住气,我…………我也是混血儿,我理解你的痛苦…………”
“您……您也是 ”富吉扑进他的怀里。爵柯卜说: “是的,我父亲是英国人,母亲却是印第安人。我与你一样,是混血儿。面对凌辱,要学会忍耐。懂吗?”
过了几天,爵柯卜又去拜访黑浜医生,发现富吉满脸伤痕。医生说:“富吉应该离开这个充满歧视的地方,让他到船上做个实习水手吧,他不会给您丢脸的!”
爵柯卜终于收留下富吉,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带他上了“浪浦勒”号,顶风逆浪,沿着日本岛向北航行。
船剧烈地颠簸着。富吉躺在吊床上,爵柯卜手提油灯问道: “呕吐得受不了吧?”富吉抬起头决然地说: “先生,我能顶住。”
过了几天,水手长呼列查怒气冲冲跑来对爵柯卜说: “那小子目无上司,竟敢回手。”爵柯卜心里明白,他严肃地告诉水手长说: “以后别再辱骂他!”
为了维护船上的纪律,船长茄克杜以反抗上司的罪,处罚富吉在桅杆顶的瞭望台上过一夜。寒冷折磨着少年,他一声不吭,坚强地忍受着严厉的处罚。
船上的人全都改变了对这少年的看法,啧啧称赞。第二天,当富吉从桅顶上下来时,水手长呼列查亲切地对他说“别生我的气,你这了不起的小家伙。”
几天后, “浪浦勒”号通过了襟裳岬海面,向第一个目的地择捉岛中部的单寇湾前进。瞭望哨大喊“陆地!”人们看到盖满白雪的单寇山出现在左舷前方。
当船通过单寇湾南面湾口时,瞭望哨又大喊: “左舷前方停泊着一艘二桅帆船!”爵柯卜大声命令:“查看一下船名!”“玛丽雅…………阿来托卡,好像是艘俄国船!”
“浪浦勒”号渐渐靠近那船。那边有人问: “喂,你们是美国船吧?”待听到这边的回答后又说: “我们是彼特罗·巴甫洛斯克的玛丽雅·阿来托克号!”

“浪浦勒”号抛了锚。爵柯卜乘上小艇前去了解一下情况,看见 一个黑头发、黑胡子,穿着熊皮大衣的俄国大汉,觉得很面熟,似乎曾在哪儿见过…………
猛然,他记起来了: “真是他! ”此人曾在锡特卡俄国皮毛公司与他共事过。“喂,是依瓦诺夫吗?”对方用嘶哑的大嗓音回答: “啊,对!爵柯卜,你的样子可没变啊!”
依瓦诺夫紧紧抓住爵柯卜,大声喧嚷: “真想念你!我们二十多紧年没见面了,想不到在这里巧遇,依旧是同行!”爵柯卜说: “听说你杀了人,进了监狱。”
依瓦诺夫弯下庞大的身躯,把鲜红的大嘴凑近爵柯卜的耳朵,悄声说:“我在萨哈林监狱里忍受了15年,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我一跑出来,就想方设法重操旧业,可是我那船, ”依瓦诺夫用手朝背面他的船员一指: “那些个破烂伙计,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取到5张海獭皮…………”
爵柯卜知道在这个狡诈的家伙口里,掏不出更多的消息。依瓦诺夫假惺惺地要留他喝酒,他谢辞了,下了小船,径自回“浪浦勒”号。
在“浪浦勒”号上,爵柯卜望见单寇湾内隐隐约约有两三条密猎船。看来这里没多大油水,他下定决心到俄国千岛群岛附近的得抚岛去。
狭长的得抚岛海拔1200米,山峦纵横,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前端的岩礁一直插进海里约20公里,犬牙交错,是个危险的海域。
瞭望哨忽然发现了海獭群。“浪浦勒”号立即抛锚,放下三只涂了保护色的小艇,每艇有一名射手,两名划手,一名舵手。爵柯卜亲自充当射手,指挥小艇前进。
无数的海獭,有的倚伏岩礁上,有的浮游在海面上。其中有只特别大的雄海獭,全然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正悠闲自得地躺在那密集如床的海藻上…………
爵柯卜向左右两艇打了招呼,决定先打那只特别大的。划手们拼命加快速度,飞溅的海水不断拍击着站在艇首的爵柯卜。
大海獭发现了渐近的小艇,警觉地盯着。爵柯卜举起枪,站在摇晃的艇上,首先开了枪,另外两艘艇紧接着也开了火。
大海獭反复的逃逸并没有摆脱猎手的枪口,当它再一次浮出海面吸气时,爵柯卜的枪响了,大海獭被命中。而栖息在险礁上的其余海獭也是同样的命运。
这一天,他们猎获了7头海獭。猎获物被吊上甲板,留在船上的人一下子爆发出欢呼声。
富吉好奇地抓起海獭,爵柯卜说:“在俄国,5张皮可换一艘小帆船。可是它很难打,即使高明的射手,而且配上优秀的划手、舵手也得花费不少子弹才能击中它。”
“浪浦勒”号在得抚岛猎获了42头海獭之后,便起锚北上。富吉已习惯了海上生活。爵柯卜看着少年,心想:该教他射击了,也许他会成为好射手…………
8月中旬, “浪浦勒”号航行到千岛群岛的斯莱特尼哈岛的5个岩礁附近,被浓雾困住了。爵柯卜忽然问船长: “你嗅到腥气了吗?”船长说: “是的,我也嗅到了!”
爵柯卜向船头的人大喊: “喂,前面望见了什么吗?”话音未落,只听“嗵”的一声撞击,船身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倾斜着,并大幅度地摇晃着…………
船长与爵柯卜不约而同想着是撞上了流冰块…………船头水手长呼烈查大声叫着:“是鲸鱼!我在船头附近看见了它黑色的鱼身。”
船长茄克杜腰结缆绳,下去检查,不久就上来报告:“船主,船头3米处被鲸鱼撞开一个口子,即使开足水泵排水,也只能维持五天。”
五天?”爵柯卜说: “那就是说必须在五天内赶到设备齐全的港口去修理。”船长说: “是的,但不能去俄国的堪察加和日本的函馆,只能去室兰!”
爵柯卜查看海图,事情只能这样安排。他犹豫了一下,告诉船长: “不能浪费渔猎期。船你开去修理,我带射手和划手上岸,你在9月中、下旬回来接我们…………”
“浪浦勒”号在南返修理途中,把爵柯卜他们载回得抚岛。爵柯卜挑选了包括富吉在内的九个人,分乘两艘小艇,在西北岸一个无名小湾登陆。
无名小湾的背面是舒缓的斜坡。他们就在斜坡上用漂来的木头和帆布支起一个小屋,安居下来。
清早,爵柯卜率伙伴们出猎去了。富吉留在营地拾柴、烧饭,一有空就去小溪里捉鱼。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再没有以前在横滨遭受的那种屈辱,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岛。
傍晚,人们回来了,围坐在小屋里,剥着猎获物的皮毛,喝着富吉做的鱼汤,嬉笑着…………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打发过去。
转眼到了9月底,气温骤降,冰雪就要来了。“浪浦勒”号仍未出现。人们失望地作了各种猜测。爵柯卜则深信患难与共的茄克杜船长一定会来接他们…………
一直到10月下旬,才看见那朝思夕盼的“浪浦勒”号白色的船体,出现在湾口湛蓝的大海上。大家欢呼着,迫不及待地乘上猎艇迎了上去。
艇船相遇了,奇怪的是上面乘坐的不是“浪浦勒”号上的船员,而是那像熊一样的依瓦诺夫,他说: “你好啊,爵柯卜,又见面了!”
依瓦诺夫打了个手势。茄克杜船长被推了出来,他脊背后被人用枪抵住。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爵柯卜真后悔没随身带着武器。
“喂,看见了吗?”依瓦诺夫傲慢地说: “你们敢乱动,首先要了你们船长的命。” “你要干什么?”爵柯卜愤愤地问。“把皮毛交上来,船就更不在话下了。”
爵柯卜恼怒极了: “畜生,你们这帮海盗!”依瓦诺夫厚颜无耻 地笑着说: “这是没办法的呀,老朋友!我的船、皮毛都丧失殆尽,连堪察加都回不去,请多多原谅。”
在枪口的威逼下,爵柯卜、茄克杜的人除了富吉去岛中捉鱼之逼外,全被反绑着,抛在沙滩上,匪徒们径直地踏过沙滩,走向斜坡上的小屋。
茄克杜对大家说: “我悔不该在返回得抚岛途中的风暴里,救了这伙畜生。”爵柯卜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 “船上的伙伴怎样了?”船长说: “都被关在船舱里。”
爵柯卜听到小屋传来的怪叫喧闹声,想着辛辛苦苦猎获的127张贵重的皮毛,想到自己和伙伴们将被杀害,真是后悔莫及,但是该怎么办呢?
忽然,就在前面10米远的礁石后面,一个瘦小的身影一闪,富吉从隐蔽处跳了出来。他手里拿着刀和那支猎枪。“啊,富吉!真是全船人的救命上帝…………”
富吉跑到最近的爱斯基摩人瓦比底身旁,放下枪,用刀把捆绑的绳索迅速割断。突然,看守人发现了,举枪就放。“啊——”富吉惨叫一声,倒下了。
小屋里的匪徒闻声纷纷跑了出来。“瓦比底,快! ”爵柯卜大声催促。爱斯基摩人用刀迅速割断绑着他的绳索。
被绑着的伙伴都被瓦比底切断绳索获救了,这时匪徒们的子弹呼啸着从头顶、身旁飞掠而过。爵柯卜飞快地捡起富吉丢下的枪,进行还击。

爵柯卜这个神枪手,一枪就把看守的匪徒击倒。其他的匪徒也都逃不出爵柯卜的枪口。
剩下的三个匪徒分散躲藏在岩礁后面,不停地朝爵柯卜他们开枪射击。爵柯卜焦急极了:他们只有一支枪,一比三,持续下去就麻烦了…………
忽见一个匪徒露出了头, “砰!”爵柯卜一枪就把他放倒。另一个匪徒吓得叫了起来: “不要开枪了,我是美国人,我投降!”他举着手,从岩礁后面走了出来。
“只剩下一个依瓦诺夫,哪里去了?”爵柯卜正想着,一个身影一闪,背海朝斜坡上迅速跑去…………“看你往哪里跑,慢慢收拾你!”
爵柯卜跑至富吉身旁。他仰面躺着。茄克杜船长盯着少年的脸:“不行了,爵柯卜。子弹穿过后心…………”
爵柯卜悲愤地凝视躺在茄克杜怀里的富吉说: “茄克杜,你们押 着人质去夺回大船,我找依瓦诺夫去,结果他!”
爵柯卜提着枪,顺斜坡上去,跟踪依瓦诺夫的足印追去。在一条两米宽溪流对面的树枝上,挂着一条布片,下面潮湿的地上,留有依瓦诺夫清晰的皮靴印…………
爵柯卜警觉地察视四周,发现前方没有了足印。看来是狡诈的依瓦诺夫想把追捕者引入歧路,应当赶快返回。
爵柯卜凭着猎人追踪野兽的丰富经验,果断地下溪流,溯水而上。走了90米左右,果然发现右岸上留有新踩的靴印。
“匪徒是绕个圈朝海岬方向奔去的。”爵柯卜奋力追赶。已能看到海湾的远处“浪浦勒”号的船体,桅顶上飘着一面红旗。茄克杜他们已经夺回大船了!
依瓦诺夫想把爵柯卜引向岛的深处,自己溜回“浪浦勒”号。却不知道“浪浦勒”号已经回到茄克杜的手里,他正拼命向海湾奔去。
爵柯卜猜透了依瓦诺夫的鬼主意,像猎捕野兽那样,悄悄地潜伏 在岩礁后面,耐心地等着他的露面。
夕阳被海水吞没了,夜幕开始徐徐降下…………突然,岩礁后面有个黑影在晃动。“黑熊出现了!”爵柯卜紧紧地盯住它。
依瓦诺夫完全想不到,爵柯卜会这么长时间地埋伏在岩礁后面。他急匆匆地走下斜坡,忽然, “砰!”一声清脆的枪响,他摇晃了几下,慢慢地栽倒了。
浪浦勒”号要返航了,天空中无数海鸟在哀鸣。爵柯卜抱着富吉 的遗体,泪流满面地对大家说:“我与他不是父子,却胜过父子之情。他死了,我们却获救了,我们要用对待功勋水手那样,为他举行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