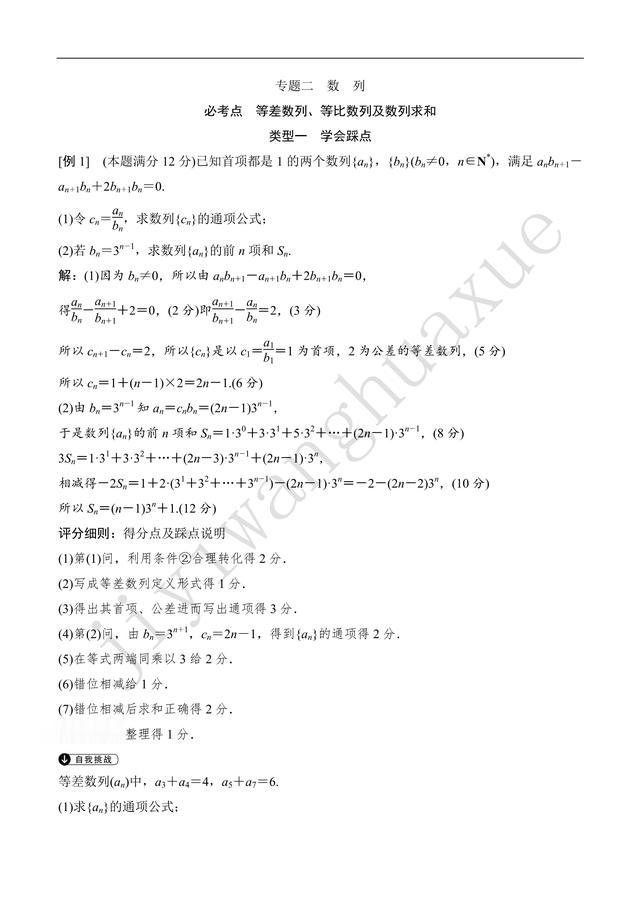娘亲为供爹爹考取功名,
不顾清誉频繁出入世家,献唱献舞,挣得的银子统统交于爹爹。
三年后,
爹爹金榜题名的那日,娘亲赤裸着身子死于城郊野狗林。
于此同时,一乞儿敲响我家大门,未开口人先跪,
「请贵人收留我,我知晓怜娘是被哪些歹人所害。」
他抬头,眸光明亮。
「我也知,贵府日后必将鱼跃龙门。」
1.
爹爹领着我去认领娘亲的尸身,
他穿着大红色的里衣,外头套了一件嵌着银丝线的黑色官袍。
是了,今日本是爹爹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苦日子好不容易要熬出头,
可,命运半点由不得人。
安陵城外的野狗林,多是富家子弟,达官显贵的抛尸圣地,
扔在这里的人,若是有幸被人发现,还能领回去烧半具骸骨,
若是不幸,自然被附近的野狗吃个干净,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
「怜娘…」
「怜…怜娘,你怎么忍心,你如何…忍心!!!」
马儿还未停稳,爹爹几乎是坠下马,踉跄着跑向那半具尸身,
眼前的景象让他颤抖不止,
「啊!!!!!——」
顾不得文人的风仪和傲骨,他将多年读书的教养摔的稀巴烂,对着官兵喊,
「滚开!不许看!你们都不许看!!!」
他毫无章法的扯下官袍将娘亲的尸身裹住,
悲鸣声撕心裂肺,似是有天大的委屈和不甘。
惊的围在附近想饱餐一顿的野狗不敢上前。
官兵想让仵作验尸,查明死因。
爹爹布满血丝的眼将他瞪了回去,
不许任何人碰娘亲的尸身。
他着了大红色里衣,亦步亦趋,将娘亲的尸身轻柔地置于我坐的轿子里。
轿子是硬质的木头板子,年久未修,还有斑驳的铁钉露出来,
「纤儿,你怕不怕?」
「她是娘亲,孩儿如何会怕。」
我垂着泪,下唇咬得出血,指甲嵌入轿子的木板里,忍得辛苦。
「那你抱着娘亲可好?这轿子太硬了,她躺着定会不喜欢。」
那一年,我十三岁,即将步入及笄之年。
娘亲的话似是犹在耳畔,
「再有两年,我们纤儿也要及笄了,娘亲定要替你办一场大宴,你啊,最是馋嘴。」
「若是有了中意的人家,定要说与娘亲与爹爹听,纤儿如今的模样,说是安陵城最好看的姑娘都不为过,可千万不能让混人骗了去。」
「纤儿若是不想嫁人,留在家中,多陪爹娘几年也是极好。」
「这嫁人呐,就要找像你爹爹这般的才好。」
娘亲与爹爹自小青梅竹马,两人相敬如宾,恩爱有加,从未红过脸。
每回提起爹爹,娘亲的脸上总是能浮起少女般的青涩羞赧。
可如今,我抱着几乎没有重量的娘亲,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碎裂成瓣,
一块块,一片片,一粒粒,
风一起,便没了踪迹。
2.
爹爹整日将自己与娘亲关在新建的祠堂里,
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也顾不得我。
消息传得很快,
新晋状元郞的发妻横死野狗林,成了安陵城中茶余饭后的谈资。
人人都说我爹怕是要疯了。
直到四日后,瘦骨嶙峋得他,终是从祠堂走了出来,他有条不紊的为娘亲举办丧事,
一应巨细。
爹爹消瘦了许多,如今的病态添在他这个男子身上,竟比之前多了些许病弱感,
更显秀雅俊美,比大多女子都要好看。
娘亲举办丧事的当天,安陵城中许多达官显贵,世家贵族都闻讯而来,
几人真心,几人假意,我瞧得分明。
他们大多是冲着爹爹状元郎的身份,给个薄面,匆匆而来,疾疾而去,生怕沾染了晦气。
真心的怕是只有与爹爹娘亲一同长大的秦叔叔,
他携家带口一身素白,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安慰爹的话,
七尺的健壮男儿,眼泪鼻涕混做一团,低低的呜咽,
倒是爹爹,见他这样,还去安慰了他两句。
门前终于是冷清了,闭上门没多久,
敲门声响起,一乞儿未开口人先跪,
「请贵人收留我,我知晓怜娘是被哪些歹人所害。」
衣衫褴褛,遮不住身上的青紫,眼角还有未愈合的伤口,
「我也知,贵府日后必将鱼跃龙门。」
3.
爹爹收留了他,不知他们在房里密谈了些什么,
自此后,便将他带在身边。
却留我一人待在府里。
家里的每一处,似是都有娘亲的身影,
我夜里习字,爹爹都会陪在一旁替人抄书补贴家用。
抄到有趣味的地方,还会单独拎出来,与我细细拆解,分享各自心得。
娘亲总会替我们点上一盏油灯,
而她则安安静静的坐在我们身后,捏着针线,仔仔细细地为我和爹爹缝制新衣,
我每次拿到新衣,总是吵着闹着说娘亲偏心,我的针脚总是粗一些,没有爹爹的细致。
爹爹听了便会孩子似的当着娘亲的面穿上,又在我身边走上一圈,显摆他在娘亲心里的地位。
如今,
我几日没见着爹爹了呢,我竟浑浑噩噩,连日子都记得不清不楚。
倒是秦叔叔,每日都会前来,教我习武。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小纤儿,叔叔没什么可教你的,只有一把子用不完的力气,你要好好学,以后莫要被人欺负了去。」
他的心里始终认为,娘亲的惨死,是因着她面对歹人毫无还手之力,才遭此厄运。
秦叔叔与我爹一同从宁远镇来到安陵城,不同的是,他们一人从文,一人从武。
前几日,他也在军中晋升成了百夫长。
或是遗传了爹爹,
我学那些书本上的东西,基本不费什么气力。
说是过目不忘,都不为过,见过的论点,总是能举一反三,学习之法也是无师自通的懂得了融会贯通的道理。
可是,习武,我着实费了不小的心思。
许是年岁大了,骨头长硬了,那些大开大合的动作,总是让我疼痛难忍。
每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秦叔叔见了,不忍。
反过来劝我歇息段时日。
可我不愿,我好不容易找到发泄内里愤懑的途径,
疼痛让我清醒,
感知到自己还活着。
4.
这日夜里,
爹爹终是领着那个莫名的乞儿进了家门。
他难得露出笑容,
「纤儿,你喜不喜欢拨浪鼓?」
这话很是突兀,想着爹爹是不是受了刺激,忘了我的年岁。
我哪里还玩什么拨浪鼓,
「爹爹?」
他笑容不减,出口的话,如夜色冰凉,如寒风刺骨。
「爹爹把那些歹人的的皮剥下来做成鼓面,可好?」
他语气越来越温柔,
「爹记得你儿时最喜欢缠着你娘亲,央着她摇鼓给你听,每次听到声音,你都会笑得很开心。」
「你,喜是不喜?」
我颤动的厉害,眼睫挂出一滴晶莹,
不是害怕,是激动,是兴奋,是心脏又鲜活的跳动。
「爹爹送的,纤儿自是欢喜的。」
他眼里有光芒绽放,月亮都逊色下来,
「爹这些日子与安儿将害你娘的人都查清楚了。」
「谁?是谁害了娘亲?」
爹爹的笑僵在嘴角,一瞬,
「待日后,纤儿自会知晓。」
「孩儿也想替娘亲报仇。」
我拉住爹爹的手,神色晦暗,
「孩儿前些日子和娘亲学做了包子,爹爹得空将他们请回来,定要好好招待才好。」
爹爹很快会意,大笑着抚摸我的头,
「还是纤儿思虑的周到。」
我将目光移向爹爹身边的人,
他和我一般大,个头却只比爹爹稍低些。
是那个乞儿,
初见未能细看,如今见了,才发现此人与爹爹站在一起,竟没有被爹爹比下去,
与爹爹的凤眸不同,他眼睛深邃明亮,纯粹得像是孩童般干净。
他好似并不奇怪,也没有害怕。
「纤儿,他叫陈之安,比你还要小些。」
他这才从爹爹身后走上前来,
「姐姐。」
这个来历莫名的人,叫我姐姐。
5.
爹爹精神好了许多,便回了朝廷任职。
还是一如既往的见不着人影。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将陈之安留在了家里。
起初,我与他并无什么话好说,只顾着做自己的事,
娘亲不在了,她的话才真切的让我觉着珍贵,
普普通通的一句责骂,一句宽慰,一句叮嘱,
我都再也听不着了。
「纤儿,又在发什么呆,可是在想今日做什么吃食?」
熟悉的话,却不是由娘亲说出来,我猛地回头,
陈之安。
我上前揪住他的衣领,凤眸微眯,没有一丝温度,
「你如何知晓娘亲平日对我说的话?」
这人当真奇怪,出现的莫名,还总说些让我不懂的话,我着实不喜。
他这人,我看不透。
「姐姐,自然是沈叔叔告诉我的。」
他不慌也不乱,沉着冷静的让我觉着讨厌,好似笃定我不会拿他如何。
「你胡说!」
我下了狠劲,掐住他的脖颈,一寸寸的收紧,
「我爹无事和你说这些做什么?」
他的脸色一点点变红,呼吸渐渐有些紊乱,这使我兴奋不已。
「说!你是不是那些歹人派来的细作?」
他没回答,我知道他说不了话。
这种完全掌控对方的感觉,让我着迷。
可他都这般境地了,看我的眼神也没有求饶的意思,甚至惊恐和害怕都见不着。
我不解,他不怕死?
只要我愿意,不需片刻,再稍微用些力气,定能让他再也见不着明日的太阳。
怎的他看我的眼神里还有些悲悯和…
我读不懂,顿觉得无趣。
松开了手,
他弯下腰剧烈的咳嗽,大口大口的喘气。
6.
那件事之后,
我本以为陈之安会离我远远地,
至少不会整日跟在我身后,姐姐长姐姐短的,
事实是,他对我依旧如往常般,就像差点被我掐死的不是他一样。
早间同我一齐习武,吃了饭食,便与我同坐在院子里看看书,写写字。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的厨艺当真了得,是我从未吃过的味道。
他待我其实极好,闲暇时,也会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物什,都是我没见过的玩意儿,可我不愿表现出来,他每每兴高采烈的拿予我,我都是看看便作罢,只是余光总会不自觉的追随他。
我对他的态度,似乎对他没什么打击,他乐此不疲。
昨日,我习字的间隙,他拿着一张宣纸,在一旁折折叠叠。
奇妙的是,一张薄薄的宣纸在他手下变得有趣极了,我全神贯注的盯着他翻飞的手指。
他见我看得认真,便慢下速度,
没一会儿,桌案上多了几个鲜明生动,且形状各异的小物什,
他一一指着它们,告诉我,在他生活的地方,称他们为,纸鸢和船只。
这些我都是晓得的,只是我从没见过有人能将天上飞的和海里飘着的,
会以这种方式呈现在我眼前。
今日,日头正盛,他穿着薄薄的单衣,拿着斧子在院里砍些木头,又弄过来气味难闻的液体,涂抹在上面,刺鼻的紧,他见我皱眉,便离我远了些,可依旧待在我目之所及的地方。
晚上他便拿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物什说是送我,
他轻轻一按,便有一枚细针从里头射出去,直直的插入墙面,整根没入。
是机巧之术,我惊喜不已,甚是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