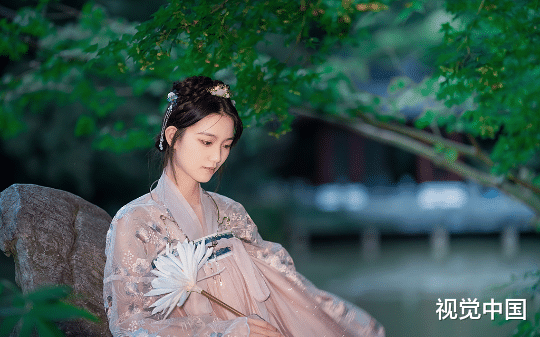我是国公府上寄人篱下的表小姐。
谢昭厌我至极,从未对我有过好脸色。
只因病弱白月光不喜我,他便命人将我赶去永明寺,要我日日为她念经祈福。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心术不正,便好好去磨磨性子吧。”
这一待就是三年。
后来,他和白月光要成婚了。
他将我接回国公府,要我亲眼看着他们成亲。
可惜,我已经快死了。
谢昭,我等不到你们成亲了。
1
国公府的马车已经停在了门口。
“表小姐,世子吩咐我们来接您回去。”
我一眼便看到了众星捧月的谢昭。
他此刻神色冷淡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转身便去收拾东西。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
当初被赶出国公府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收拾东西,他们随意扔给我个包袱,便催着我上马车。
“……你就住在这里?”谢昭拧眉打量着我的住处。
空荡荡的屋子,几张陈旧的桌椅,一张狭窄的小床,甚至连个梳妆台都没有。
“对啊。”我很快便收拾好了东西,平淡地答道。
谢昭冷冷地睨了他身后的两个丫鬟们一眼。
她们慌张地对视一眼,连忙跪下:“世子恕罪,表小姐她…昨日才搬进这间屋子的。”
是了,就她这娇纵的性子怎么可能忍受得了住在这种地方。
不过是博取同情的手段罢了。
谢昭冷笑了声:“少装可怜,没人吃你这套。”
我确实是昨日才搬进这间屋子的。
因为我之前住的屋子可比这差得多了。
这两个丫鬟不过是昨日听说了谢昭要来,想到我毕竟是国公府上的表小姐,害怕被怪罪,着急忙慌地给我换了间新屋子。
我懒得跟他计较,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拨开他挡在我前面的身影:“是啊,没人吃我这套,麻烦让让。”
谢昭没动,他漆黑的眸子落在我生了茧子,冻得通红的手上。
他一把拽住我的手,发觉我瘦得厉害,他怔了一下,但很快便冷了脸色,嗤笑道:“这也是你博同情的把戏?”
“商时序,胡闹也得有个度,适可而止吧。”
他抓得很紧,我挣了挣,没能挣脱,只好放弃,冷笑道:“是,我就是在装,你满意了吗?”
他盯着我看了半晌,面色难看地甩开我,拂袖离去。
2
我踉跄着稳住身形。
垂眸目光落在我的手上。
指节肿胀难看。
这是我每个冬日晨起洗衣时,冰冷刺骨的溪水日日泡发的。
茧子粗粝密布。
这是我试着学会劈柴烧火时,一次次鲜血横流中一点点磨出来的。
永明寺这三年,确实磨平了我的性子。
刚来那段日子,我后悔过。
夜里,我会抱膝蜷缩在阴冷的角落里,默默地流泪。
我哀求过。
我颤抖着写下一封封书信递送给国公府,无人在意。
我反抗过。
“世子有令。”侍卫冷漠地按住我,“小姐必须每日为宁姑娘念经祈福。”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
在这里,我不再是什么国公府上的表小姐,更没有家人偏帮我。
没有人会帮我,迁就我,甚至更多的是等着落井下石。
我自幼体弱多病,兄长为我去学了医,只为了帮我调理好身子。
为此还被父亲狠狠揍了顿,满院子追着怒骂堂堂将军之子怎么能弃武从医。
兄长便偷偷地学,父亲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
但自从父兄走后,没有人再为我日日把脉煎药。
寄人篱下于国公府,他们待我已算得上是仁至义尽,我也不愿替他们平添麻烦。
便忍着从没提起过。
这些年里,我的身子越来越差。
到了永明寺,更是不断地被磋磨。
动不动便在佛堂跪上两三个时辰,洗衣做饭,缝补打扫已成了家常便饭。
我病得越发厉害了,大病小病接连不断。
谢昭下令不许我离开永明寺半步,侍卫丫鬟们更不会替我请医。
有时深夜,发了高热。
小九便会从窗外悄悄地探出光溜溜的脑袋,偷偷地替我递药。
小九是寺里新来的小和尚,他会早课后偷溜过来陪我聊天,时不时帮我打扫院子,干些杂活。
世上好像除了小九,没有人再陪在我身边了。
3
国公府。
我抬眼看着挡在我眼前的人。
她裹着厚厚的狐裘,笑盈盈道:“商姐姐,好久不见。”
初雪寒冬。
洗得陈旧发硬的衣衫根本挡不住寒风,冷得我指尖发僵。
宁芝芝柔柔地咳了几声:“多亏了商姐姐这几年为我祈福念经,我的身子好多了。”
一路车马颠簸,惹得我头昏脑涨。
我实在没力气跟她在这玩什么姐妹情深的戏码。
“好狗不挡道,让让。”
真是可笑,一个个都跑来挡我的路。
我没理会她,径直从她身旁走过。
宁芝芝被下了面子,脸色难看地拽了我一把。
“商家早就已经没了,你以为你还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吗?”
我这些日子病得越发厉害了,身子亏空,根本经不住任何推搡,一下子重重摔在雪地里。
脑海一阵嗡鸣。
冰冷刺骨的温度从手心和膝盖传来,冷得发抖。
谢昭闻声赶了过来。
他蹙眉看着我狼狈的模样,伸手想扶我起来,却被宁芝芝可怜兮兮地拉住了袖子。
“昭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想和商姐姐说说话,我没碰到她。”
“我也不知道商姐姐她怎么突然就摔倒了。”
我深吸一口气,趁他们说话的功夫,自个儿费劲地爬了起来。
谢昭看见我的动作,顿了顿:“你怎么……”
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和落雪,抬眼看向他:“嗯,就是她推的我。”
谢昭眉心紧蹙,下意识道:“芝芝身子弱得很,怎么可能推得了你?”
心脏重重一沉。
一时寂静。
谢昭面色一白,抿了抿唇,不再开口。
我率先打破了沉默。
“哦对,她弱不禁风。”
“是我自己摔的,她没碰我。”
“请问我可以走了吗?”
4
我绕过他们回了自己的院子。
倏地,我停住了步子。
院门大开,院子里光秃秃的,满院枯死的花草。
我指尖蜷缩了一下,快步推开房门。
屋子里倒是满得很,堆满了杂物。
乱成一团,不堪入目。
谢昭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他看着我屋子的模样脸色微微一变,终于还是缓了语气。
“芝芝体弱,你不该同她置气。”
“今日之事,你同她道个歉。”
“……我命人为你重新收拾个屋子。”
心脏瑟缩,疼得厉害。
“谢昭。”我抬眸看向他,“为何错的总是我?”
我一字一句道:“道歉,绝无可能。”
谢昭面色一沉,他紧盯着我,半晌气急地笑笑:“这么多年,你还是没能学会低头。”
“商时序,你别后悔。”他咬牙切齿道。
他重重地摔门而去,我听见他冷冷地吩咐道:“任何人都不许帮她。”
我知道,他在等我求他。
等我低头。
可是谢昭,是你忘了你曾说过的话。
你说,无论如何,国公府永远留有你的位置。
我垂眸看着脏乱的屋子。
你说,在国公府,没人能欺负到你头上来。
我卷起袖子,在众人的目光下,开始擦拭布满厚厚的灰尘的床榻。
是你忘了。
还是你从没记住过。
而且你怎知,我未曾低过头?
5
我在国公府待了五年。
母亲早逝,我的父亲战死沙场,兄长逝于疫病。
我无处可去,只能拿着信物去国公府寻求庇护。
我的母亲同国公夫人是手帕交。
我刚出生时她们曾玩笑话地订下了娃娃亲亲,甚至留下了一枚玉佩作为信物。
将军府倒台,我看得出他们很为难,只是出于旧时情谊收留了我。
我以表小姐的名义留在了国公府。
我很感激他们,也尽我可能的去报答他们。
谢昭不喜欢我,我一直都知道。
他不喜欢被束缚,不喜欢被约束,更不喜欢以同他娃娃亲的名义留在国公府的我。
但我不在乎。
我小心翼翼地打探他的喜好。
每日依旧雷打不动的为他做吃食。
四处奔波替他寻喜欢的物件儿。
日复一日,谢昭终于对我松了态度。
他不再总是对我冷着脸。
他会别扭地尝着我新做的糕点,绷着脸点评尚可。
他会松松地倚着我的房门,喊我去前厅用膳。
我以为日子就可以这么好好的过下去。
直到有一天,宁芝芝出现了。
谢昭对我的态度再次变回了生人勿近的冷漠。
她们说宁芝芝是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分彼此。
我站在门外,看着其乐融融用着晚膳的一桌人。
无人在意我。
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我一直是那个外人。
我从未真正走进这块地方。
6
宁芝芝的病是装的。
但没人怀疑。
“昭哥哥。”宁芝芝半倚在床榻上,脸色惨白,眼眶通红,“我不怪商姐姐。”
我盯着打翻在地的药罐,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熬了两个时辰的药。
宁芝芝摔倒,便定是我推的。
宁芝芝落水,便必是我害的。
无论发生了什么,只要宁芝芝一句她不怪我,所有的罪名便由我担着,从未听过我的辩解。
我抬眼看向面色难看,怒气难掩的谢昭。
“商时序!”他狠狠地捏住我的手腕,“做事总该知点分寸,别以为我不敢对你怎样!”
不久前,宁芝芝喝了我替她熬的药,便当场吐了血。
医官一查,竟是药里被下了毒。
谢昭震怒,不分青红皂白地便将我抓了过来。
真可笑,让我日日熬药给宁芝芝赔罪的是他,喝了药怪我的还是他。
“不是我。”我直直地看向他。
谢昭冷笑一声:“除了你还有谁?”
呼吸一窒,我几乎喘不上气来。
“谢昭。”我闭了闭眼,“我最后解释一次,不是我。”
“你就无法真正相信我一次吗?”
谢昭一怔,微微松了力道,他正想说些什么。
有人从外面冲了进来,跪倒在地,高喊道:“奴婢亲眼看见表小姐将此物倒进了药里!”
我听着这声音,不可置信地朝她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