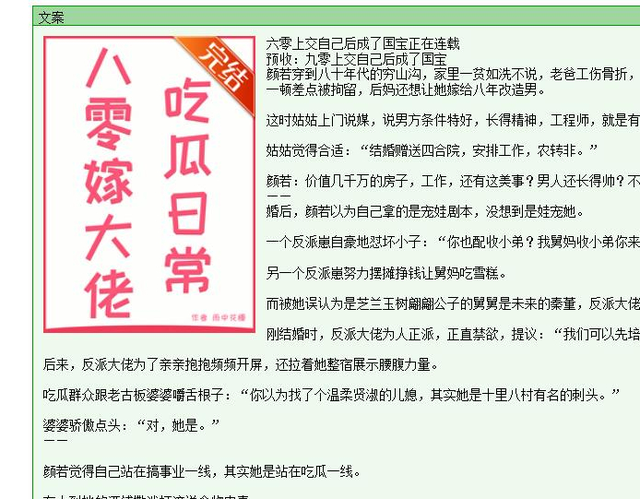攻略时逾成功后,我选择留在了攻略世界。
结婚三年,他对我恩爱有加,直到又一个年轻的攻略者出现。
我们双双出车祸醒来后,他问,「我老婆在哪?」
在我脑海里蛰伏已久的系统激动不已:
【宿主!时逾是装的。】
1
高速飞驰的法拉利和一辆失控的大货车对上。
最后一刻,时逾放弃操控方向盘,着急忙慌掏手机。
当着我的面,发信息给他置顶对象:
「对不起,没能赶上你的演奏会。」
没来及看信息是否发送成功,我就陷入了昏迷。
。。。
醒来时,消毒水味刺鼻。
时逾似笑非笑的一张脸闯入我视线。
「嫂子,我老婆呢?」
我身体一僵,怔怔的看着他。
从三个月前开始,时逾性情大变,对我渐不耐烦。
我以为,自己爱他,所以对他的阈值足够高,也有足够的时间等他回心转意。
可现在,时逾,我留在这个世界的意义——把我忘了?
一道激动的机械声响起:【宿主,时逾是装的!】
是系统,从我选择留在这个世界后就没再出现的系统。
我怔愣着打量这张熟悉的脸庞,一段段画面在我脑海中放映。
为我做早餐的时逾,在台下看我演奏会的时逾,送了一整个后台花给我的时逾。
五年陪伴,生死共度的勇气。
在他的一句「嫂子」里,成了一地鸡毛。
开口我才发现,我的声音撕扯到哑然:
「不好意思,您是哪位?」
我拿我最后的尊严反抗,期冀听到他说:
「姜姜,我开玩笑的。」
可没有,他只是定定的笑,薄唇扯开好看的弧度。
残忍的晃人。
两人一起失忆,也不错。
陪了我8年的系统说过:身为攻略者绝不能喜欢上攻略对象。
可那时我满腔爱意,以为抵得过岁月变迁。
为了留在这个小世界,我和系统做了交易。
只有时逾对我的爱意一直在80%以上,我才能在这个世界安然无恙的活下去。
否则,我会有被抹杀的风险。
三年前的我是这么说的:
「系统,我相信时逾,也相信自己的判断。」
结婚三年,系统沉寂了三年,直到刚刚:
【宿主,打脸吗?】
余光里,隔壁病床的时逾指尖在键盘上翻飞。
系统轻易调取了时逾和他置顶的聊天记录:
时:宝宝,左肩膀疼。
亲一口阿时:我好想去照顾哥哥,那个女人会生气吗?
时:不用管她,在和我装失忆。
【被攻略者时逾,当前爱意值50%。】
【宿主,你对他而言,和一个有好感的普通人无区别。】
【做为惩罚,我将于一个月后正式开始抹杀你的记忆、情绪,和生命。】
【宿主,一起期待你的深情,换来了什么吧。】
忍住留置针酸麻的痛感,我看向时逾。
他一刻不停的盯着手机,笑意分明。
我已经很久没看他这么笑过了。
察觉到我的视线,他也挑眉望过来。
恣意的少年气,开口却让人心寒:
「嫂子,记不得我没关系,你还记得我哥吗?」
我下意识看向床头本该碎裂的手机屏,它完整如新。
锁屏亮起,背景是我和一个男人的合照。不是时逾,是他的好友丁俞澄。
是用我央求拍的周年纪念照片处理的,后期痕迹拙劣。
我自嘲的笑笑:「不记得了。」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人影都没看到一个。」
「应该也不怎么爱我吧。」
我盯着他那双清亮的眼。
试图从我真正的爱人脸上找到一丝愧疚。
可任何情绪都没有出现。
他无比自然的拨了通电话:
「阿澄,你再不来嫂子要生气了。」
下一秒,有人推门进来。
茉莉香气扑鼻。
2
「阿时,你快把我吓死了~」
一张纯欲的脸,和聊天记录里的小猫头格外匹配。
病床上的时逾好整以暇坐起,亲昵地将她拉到怀里:
「给你介绍一下。」
「我老婆,傅筱筱。」
他二人熟稔的姿态,像是相顾了无数个朝暮的爱侣。
我尴尬的抬手,连输液管里开始回血都不自知,讷讷道:
「你好。」
傅筱筱秀气的眉头拧着,小声嘀咕:
「阿时哥哥,她这么丑的吗?」
「本来就长的不好看,还撞坏了脑子,真不知道哪个男人会要。」
我看着电视机倒映里的自己,满脸的青黄淤痕,头顶还缠着绷带。
确实挺丑的。
时逾冷淡的补刀:
「呵,宝宝要是觉得碍眼就别看,污染心情。」
傅筱筱瞥我一眼,像打了胜仗的鸡一样,喂时逾喝甜汤。
两人你侬我侬,汤罐不过喝了一半就急不可耐的走进厕所里。
对话的声音被压的很轻。
「阿时,看她那幅蠢样子,不会真失忆了吧?」
时逾环着手,不屑道:
「宝宝,提她多晦气?」
「和她待在一个房间里我都觉得恶心。」
「还是你觉得这样不够刺激,嗯?」
「没有啦,阿时哥哥,我只是觉得,如果我是她的话。。。」
「呜呜呜。。。能不能轻点。。」
衣物摩擦的声音良久,时逾轻吻傅筱筱的耳廓,冷淡道:
「宝宝,她和你不一样的。」
「她这种人,就算我让她跪下给你道歉,她也会照做。。。」
「以为装失忆我就会放过她吗?」
「呵,异想天开。」
隔着一堵墙,我喉头泛起几股腥甜。
我从来不知道,时逾这么讨厌我到连和我在同一个空间都难受的不行。
我默默质问系统:
「你说时逾对我还有50%的爱意值,是在安慰我?」
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恨不得让我万劫不复。
【宿主,系统不会出错。】
我慢慢攥紧拳头,无奈的笑了。
没关系的,出不出错都不重要了。
不论时逾是恨我也好,认定我是个陌生人也罢。
都无法改变我要被抹杀的定局。
我只是很好奇,如果有天时逾知道。
他不爱我的结果,就是我要彻底消失在世界上,他会为我掉眼泪吗?
头又开始疼,我蜷缩在被窝里。
麻醉的药效还没完全过去,我靠这点模糊记忆中零碎的蛛丝马迹。
衬衫衣领上若隐若现的茉莉花香,袖扣从灰色换成银色,频频出差,摆在沙发上却不准我碰的小玩具。
时逾,你是在什么时候,就准备把我丢掉了呢?
迷迷糊糊的,我出了一身冷汗,记忆却不自觉回泛到从前。
十八岁的时逾,住半地下室,咬着手电修手机。
他修了106台手机,贴了三百多张手机膜,终于在我的生日那天,把一双高跟鞋放在我家花园里。
会客厅内金碧辉煌,灯影交错。我的目光却越过满池富丽,落在只穿了一件老式夹克的他身上。
「时逾,你不需要送我什么,我也会坚定的走向你。」
「你不相信吗?」
十八岁的时逾摇头,丹凤眼中蓄了晶莹的泪。
「不是不相信,只是觉得只有这双鞋子,才配得上你。」
我穿上这双磨脚的高跟鞋,过了人生中唯有一次的成人礼。
但十八岁离现在的我和时逾太过遥远。我脱下了高跟鞋,他穿上了布洛克。遥远的誓言,再珍重听起来都像哭声。
迷迷糊糊中,我只记得我又去拉那双骨节分明的手。
可那双手中指上没有戒指,手上没有拧螺丝拧出的老茧,也不会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刻捂住我的耳朵,和我说:「姜思思,我在。」
没有人会一直都在,是我天真过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