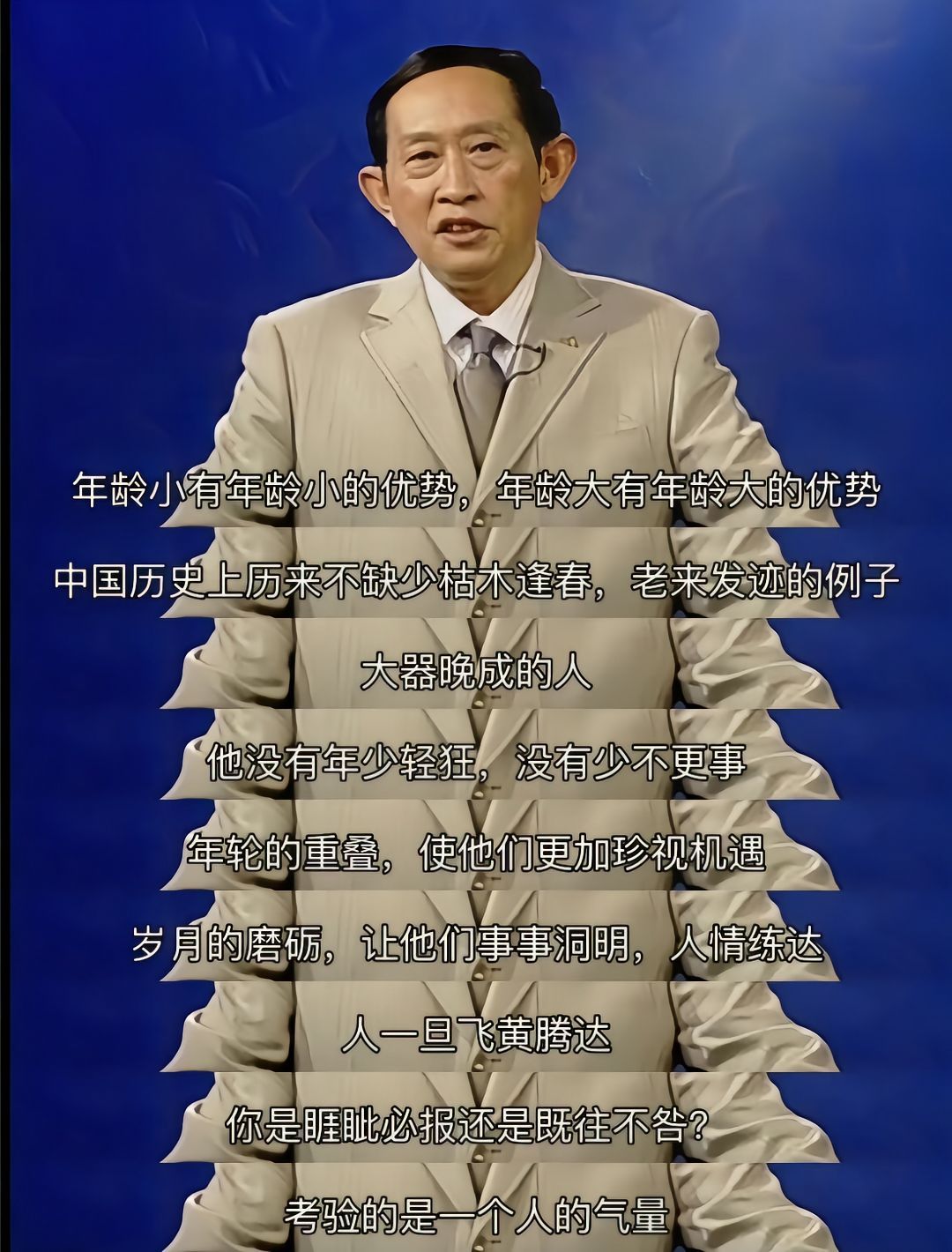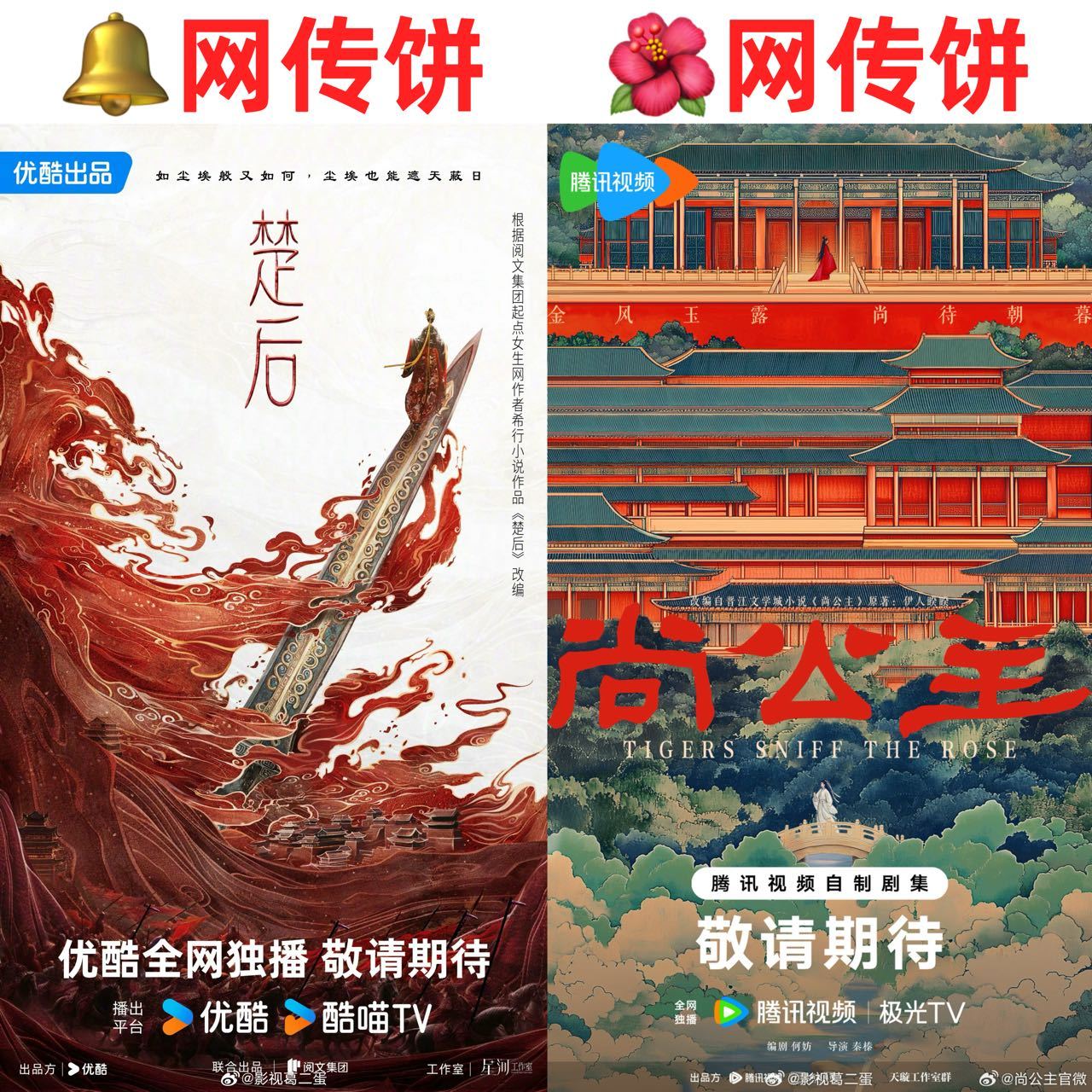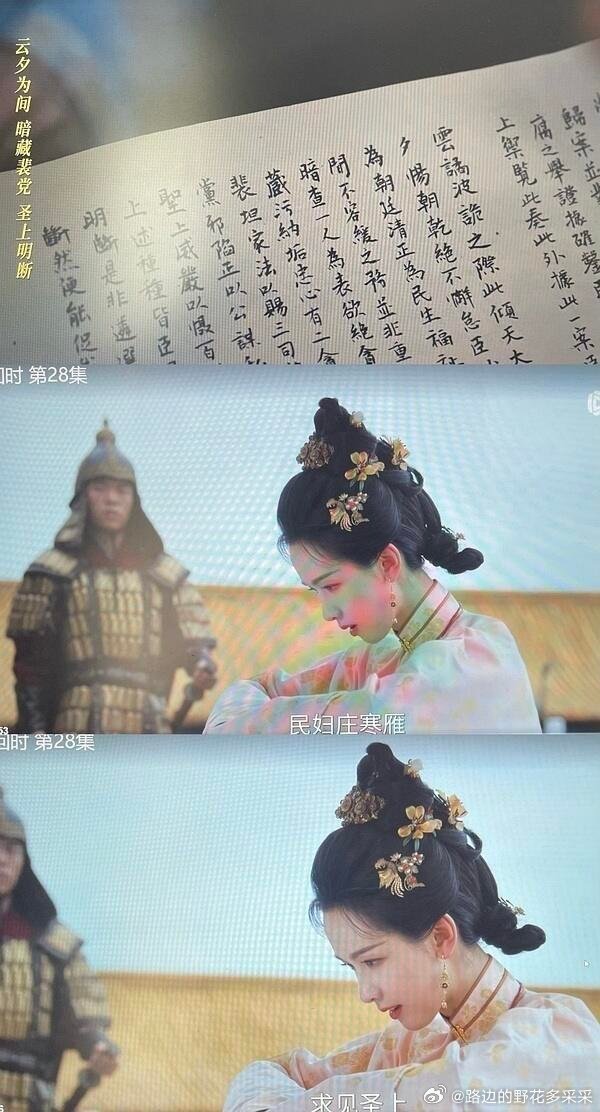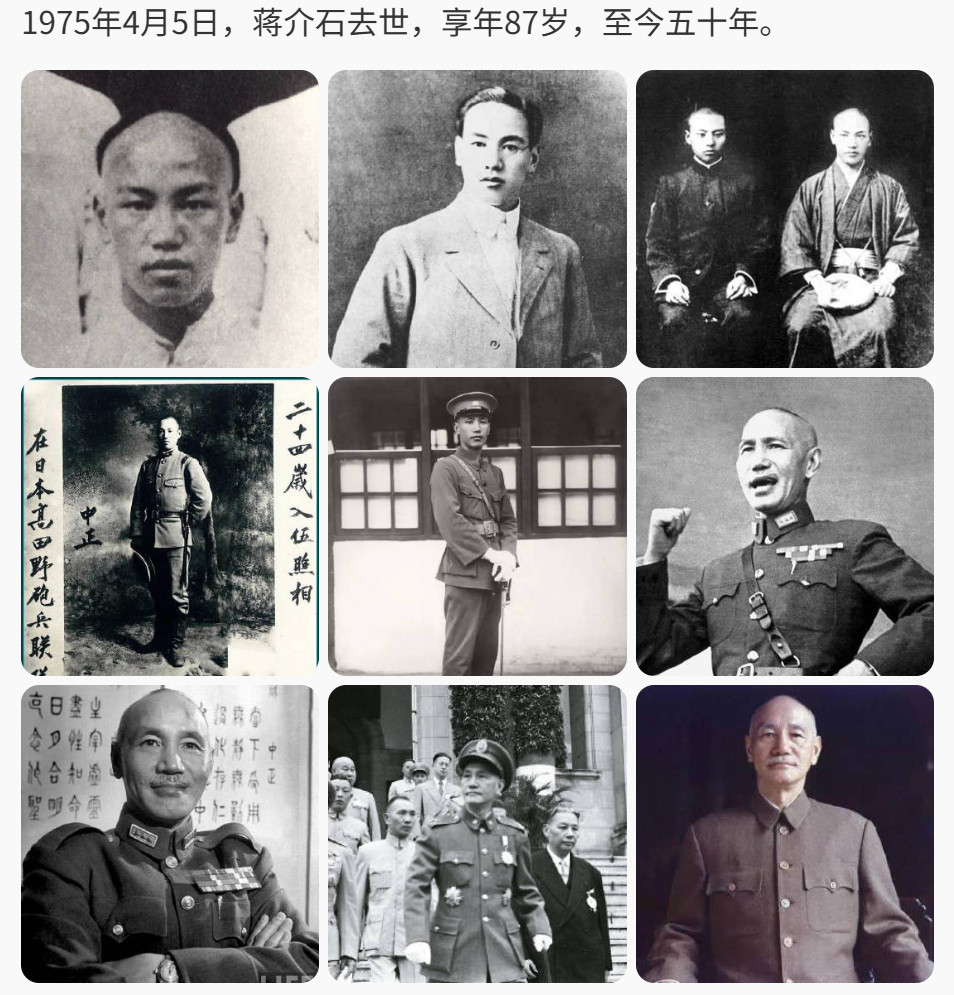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对清朝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以对抗太平军。然而,朝廷并未给湘军拨款,可湘军将士待遇颇高,曾国藩究竟从何处筹措这巨额资金呢? 湘军的组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起义军攻打湖南。清政府无奈之下,要求曾国藩以团练为基础创建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的十二年间,湘军从无到有,发展至十二万人。 湘军实行 “厚饷” 原则,士兵收入约为清廷正规军绿营军的三倍。以中级军官为例,五百人一营的营官,每月纯收入达一百五十两白银,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高级将领如统帅万人以上的,收入更为可观,像湘军名将李续宾,每年净收入达五千四百两,是同级别国家正规军的六倍左右。如此高额的军饷支出,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首先,劝捐成为曾国藩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湘军创建初期,劝捐工作就已展开。过旭明先生在《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一书中提到,咸丰三年、四年的劝捐筹饷,让曾国藩焦头烂额。 他对一些富户不肯掏钱极为不满,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就提及 “长沙常家,安化陶家,务得阁下札两县,再一饬催……”。陶家指的是病逝于两江总督署的陶澍家族,曾国藩认为陶家富有,理应在组建湘军办团练时出资。 这一要求还引发了曾左二人的 “裂隙”,只因陶澍与左宗棠是儿女亲家。此前,道光十五年,曾国藩留京时,见陶澍给京城官员送 “别敬” 达五万两之多。后来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时,也拿出二万两白银送 “别敬”,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那次给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籍京官送了一万四千多两。 在曾国藩眼中,陶家经济实力雄厚。道光二十三年,陶澍过世后,曾国藩途经陕西,得知陶家托付时任陕西巡抚李星沅提取陶澍生前两江总督任上未支取的津贴,金额达 “数万金”。故而,曾国藩组建湘军时,首先想到向陶家这类富户劝捐。 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披露,他与塔齐布麾下一万五千多名湘勇,每月需饷银六七万,战后奖赏、抚恤以及船只、器械的修理添造费用不菲,湖南财政无力支付。于是,曾国藩阐明 “本省派员筹捐”,但众人并不踊跃,他便向朝廷申请 “部、监执照共二千张…… 以便广劝而济要需”,即通过捐款可换取各部候补官员的证明,此申请获皇帝朱批 “户部速行查办”。可见,劝捐方式多样,既有地方官员的 “饬催”,也有以虚缺或实职为 “诱惑”,吸引有钱人出资。 其次,曾国藩积极从其他地方筹集资金。咸丰四年八月的奏折中,他明确要求江西、广东、四川三省 “解饷协济”。江西前后解到白银五万五千两,广东提供了六万两,连同在籍侍郎黄赞汤募捐的二万两,都交至湖南省国库,再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拨付给曾国藩等军营。但四川的资金筹集并不顺利,第一批四万两被荆州将军官文截留,第二批三万两 “绕道前来”,去向不明。 后来,曾国藩上书朝廷,从陕西要到二十四万两。曾国藩善于向朝廷说明情况,他详细汇报人员数量、作战场次、战果等,让朝廷知晓钱的去向,同时表明要打胜仗需资金支持,皇帝也常批示户部等部门办理。 再者,盐引成为湘军筹钱的重要途径。咸丰五年,湘军水陆官兵一万多人,上游运道断绝,饷银匮乏。曾国藩此前奏请福建、浙江两省援助,但浙江因徽州戒严,福建因自身疲敝,均难以提供资金。曾国藩研究发现,盐是重要财政来源。当时,太平军致使淮南盐务 “片引不行”,盐场存盐堆积,而江西、湖南却无盐可售,甚至淮南盐被偷送给太平军,广东土匪低价售盐获利。 于是,曾国藩请求户部拨给浙盐 “三万引” 以抵饷银,由他招募乡绅富户出资购盐,并自行配备运力运往江西、湖南等地。如此,用浙江盐行淮南引地,豁免浙江省钱粮。这一举措效果良好,在刑部侍郎黄汤赞督劝下,募集到四五十万两白银。 最后,关税厘金为湘军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咸丰六年,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闹矛盾,不愿将江西税提供给湘军。此时,上海商贾云集,关税丰富,曾国藩便通过抽取厘金充作军费,即在各地设立关卡,向商贾征收 “厘钱”。湘军所处的华中、东南地区商业繁荣,厘金关卡设在交通要冲,收取资金颇为可观。咸丰八年,湘军克复九江、吉安等重镇,加上胡林翼的支持以及厘金的稳定供应,湘军军费得以保障。 朝廷虽未给湘军拨款,却让曾国藩凭借劝捐、向其他地方筹集、利用盐引以及收取关税厘金等多种手段,成功解决了湘军将士待遇高所带来的资金难题。这些举措不仅支撑了湘军的发展壮大,也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政治、经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