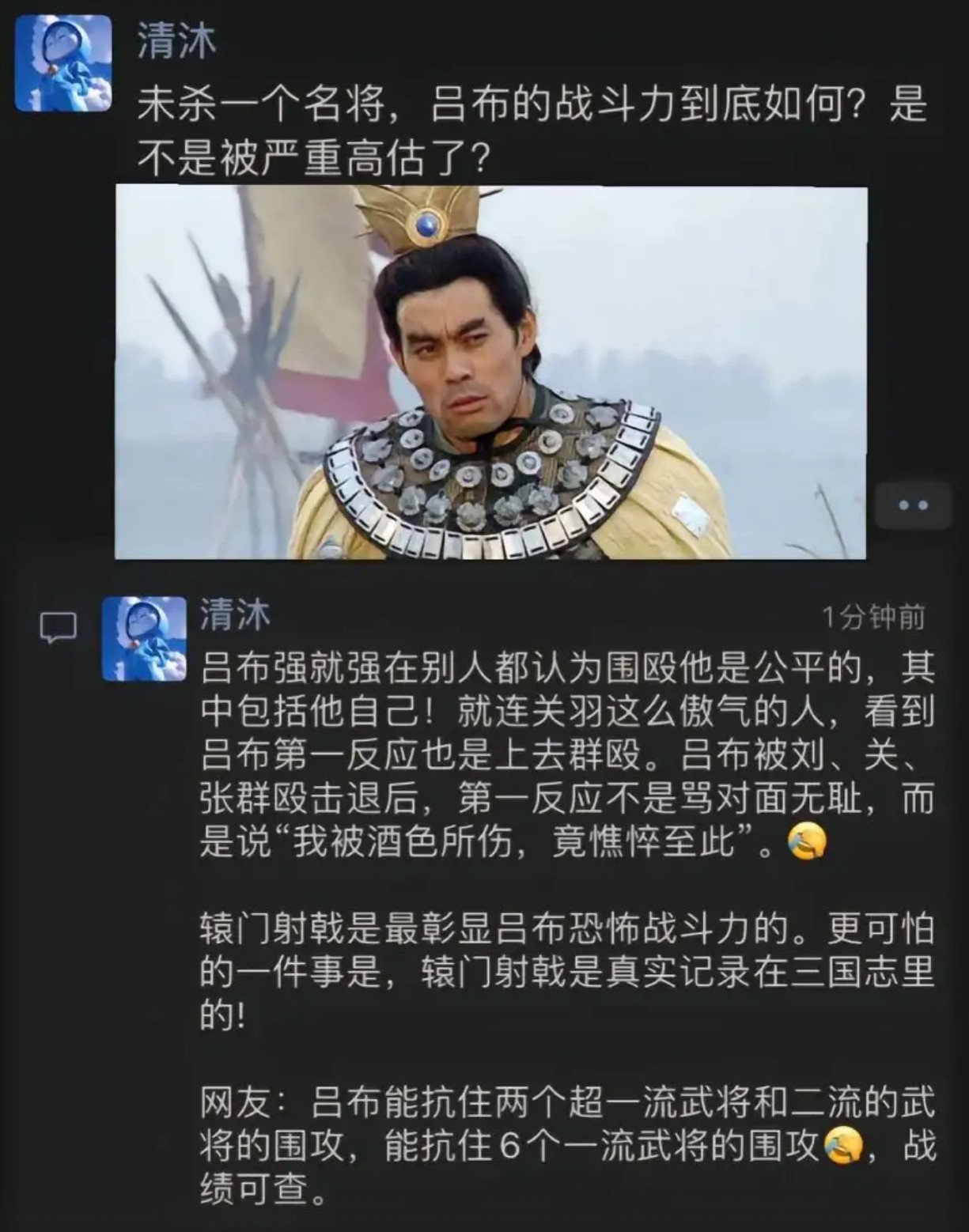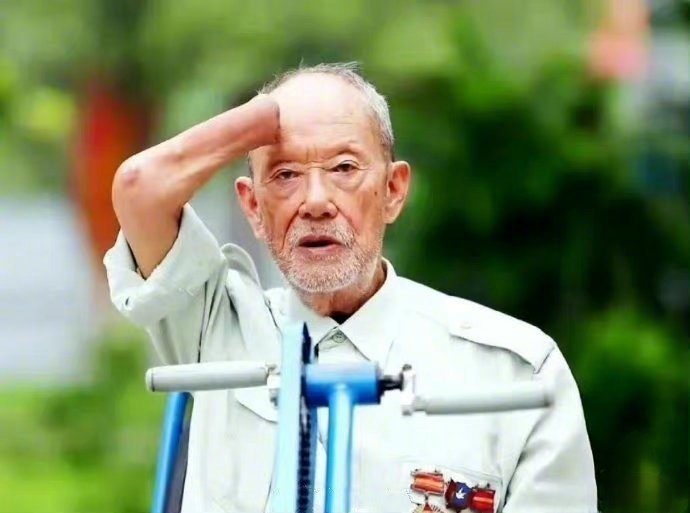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慢慢变黑,一些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1956年的那个春天,一件令整个考古界为之震惊的大事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现代化教育家吴晗七老八十的高龄,却鼓足了发掘明代帝王陵墓的决心。
他们组成了一支发掘队伍,终于说服了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张闻天,获准发掘一处规模不太大的帝陵先行尝试。
就这样,一支由郭沫若、吴晗率领的考古队伍开始了发掘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定陵的艰巨工作,尽管事前郑振铎等著名考古专家曾多次力陈不该轻举妄动,但郭氏等人热情高涩,认为这无疑是彰显中华文明的绝佳机会,最终仍然逐一打开了陵中棺椁。
当破土重现三口丹陵时,考古队员们终于看到了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遗体,尽管只剩骸骨,头颅处却依旧柔亮,皇帝发顶上一顶金丝编织的皇冠熠熠生辉,万历遗容犹存,周围堆满了成箱成匹的织金锦缎,耀眼夺目,彷佛重现了那个盛世的辉煌一般。
然而就在队员们为之赞叹时,棺中文物竟在一瞬间迅速碳化、散架、失色,刹那间就化为黑灰枯骨。
那一刻,所有人的欣喜若狂都被生生掐灭,取而代之的是万分的惊骇,有人立即大叫制止,但为时已晚,郭沫若等人在震惊中反应过来,文物损毁的缘由是因为陵寝内过于稳定的环境被打破,遭受外界剧烈变化时无法承受。
当即,郭氏痛心疾首,命令队员停手,并亲自封存了现场,如此一来,无数令人向往的文物遗珍,都随之被永久地封存在地下,无人能再窥其全貌。
这一重大教训令当局为之深受震撼,即刻下令不得再发掘帝陵,尽管后来一些地区仍热衷于挖掘其他帝陵,但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明令禁止在十年之内决不开掘。
国务院还相继出台文件,任何单位在保护技术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都不得进行大型帝陵发掘,以免引发文化赌注和"陵墓经济化"的恶性循环。
对此陈淳先生引出了当前国内一些考古评奖活动存在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倾向,将考古发掘等同于"挖宝"大赛,追求发现珍贵文物的价值感官刺激,而非致力于真正的考古研究工作。
他批评这种做法已经背离了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学的成就应该在于考古人员对于出土文物的研究深度和水平,而非仅仅是发掘出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品。
紧接着,陈淳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发掘本身就是一种对文物的破坏行为,它与保护文物形成了一对矛盾,因此我们要审慎思考,所谓"抢救性发掘"是否真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最佳方式?在急于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是真正在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还是在"保护"的名义下进行合法的破坏行为?
在进行抢救性发掘之前,考古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的目的,到底要"抢救"什么?为后代子孙保护和传承了什么?我们需要像历史侦探一样,在现场仔细搜集各种有价值的信息线索,努力复原当时的现场和历史过程,并把研究成果呈现在"法庭"上,让大家审视。
总的来说,陈淳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当下考古界一些存在的急功近利、追求热点的不良风气,呼吁考古工作者们回归初心,用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抢救"和"保护"的统一,并为后人留下高质量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只有如此,才是对祖先文明最好的致敬。
考古固然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但文物保护更是这把钥匙的使用准则,只有两者并重,我们才能真正打开通向过去的大门,见证璀璨文明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