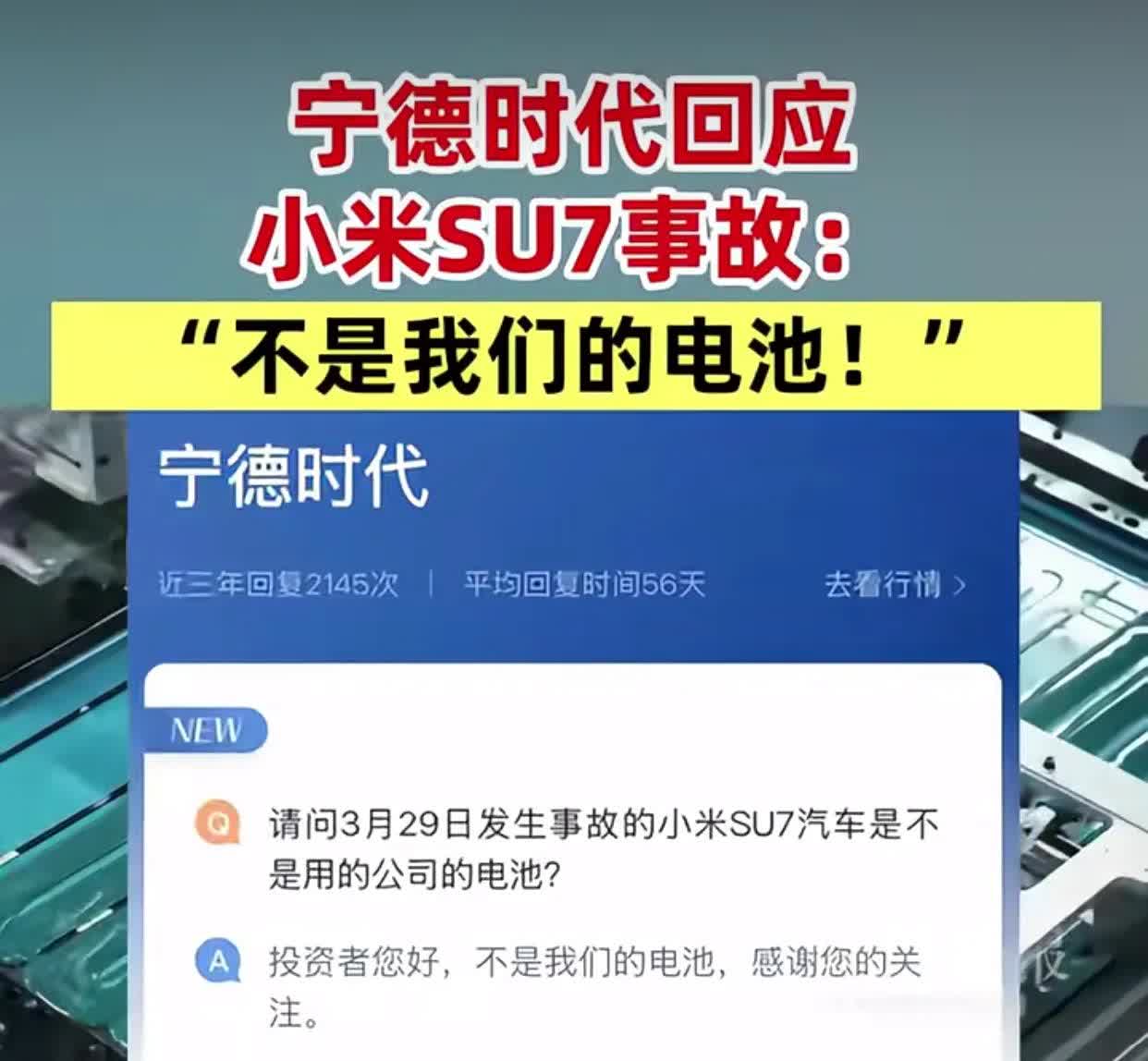1998年《新闻联播》直播还有15分钟,李瑞英突然接到儿子坠楼的消息,但她努力平复心情,镇定地播完新闻后才赶去医院。事情曝光后,原以为大家都会说她敬业,谁知众人却指责她冷血、“六亲不认”。 夜幕下的演播室,灯光刺眼,李瑞英端坐在镜头前,耳边却传来电话那头撕心裂肺的哭声:“孩子坠楼了,快回来!”她愣住,手中的稿件微微颤抖。 1998年的这个夏夜,距离《新闻联播》直播还有15分钟,时间紧得像一根绷紧的弦。她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眼角泛红,却强行挤出一丝笑意——儿子生死未卜,她该怎么办?这场直播还能不能继续? 那是个闷热的傍晚,北京城的天空压着厚厚的云,像要下雨却始终憋着。李瑞英坐在化妆间,桌上摊着厚厚一摞新闻稿,字迹密密麻麻。她习惯性地用手指轻敲桌面,那是她缓解紧张的小动作。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出“家”字。 她皱了皱眉,心想这时候谁会打来?接起电话,婆婆的声音带着哭腔传来:“瑞英啊,小宝从楼上摔下去了,血流了一地,你快回来吧!” 那一刻,她脑子一片空白,手一松,手机差点滑落。儿子才十岁,活泼好动,前几天还缠着她要新自行车,怎么会……坠楼?她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孩子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周围围满了人。她想立刻冲出去,可脚下像灌了铅,动弹不得。 抬头一看,墙上的钟指向6:45——还有15分钟,《新闻联播》就要开播了。 后台忙得像个战场,导演在喊:“李姐,准备好了吗?”化妆师拿着粉扑过来补妆,同事们来回穿梭,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紧张的味道。李瑞英咬紧牙关,低声对电话那头说:“先送医院,我忙完就到。” 挂断电话,她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稿件。她知道,这个时候找人替播根本来不及。《新闻联播》不是普通节目,它是全国亿万观众的窗口,是国家的脸面,分秒必争,容不得半点闪失。 她闭上眼,脑海里两个声音在撕扯。一个是母亲的本能,喊着“去医院,孩子需要你!”另一个是职业的责任,低语着“你不能走,全国人民在看着。”最终,她选择了后者。她让化妆师再扑点粉,盖住眼角的泪痕,然后挺直腰板走进演播室。 灯光打在她脸上,刺得她眼睛发酸,可她还是笑了——那种标准的、职业的微笑。30分钟的直播,她的声音平稳得像机器,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晰有力。没人看出她内心的惊涛骇浪,连搭档都事后说:“那天你状态真好。” 直播结束的瞬间,她几乎是瘫在椅子上,眼泪再也止不住,像开了闸的水。她没换衣服,没卸妆,抓起包就往外冲。医院急诊室的灯光冷冰冰的,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味。她到时,儿子刚被推进手术室,婆婆扑过来抱着她哭:“你怎么才来啊!”那一刻,她的腿软了,却只能硬撑着安慰:“会没事的,医生会救他。” 几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孩子命大,摔得不轻,但保住了。”李瑞英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可看着病床上插满管子的儿子,她鼻子一酸,眼泪又掉下来。她握着他的小手,低声说:“对不起,妈妈来晚了。” 好在,经过几周的治疗,儿子康复了,只是因为伤势错过了那年的高考。她陪在床边,轻声安慰:“没事,考不上也没啥,只要你好好的,比啥都强。”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多久,媒体爆了出来。标题耸人听闻:“《新闻联播》主持人儿子坠楼,她却坚持直播!” 舆论像潮水一样涌来,有人夸她敬业,说她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典范;可更多的人骂她冷血,“连亲儿子都不管,算什么母亲?”、“六亲不认,心都硬成石头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她心上。她没回应,只是默默把报纸收起来,晚上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 其实,李瑞英何尝不疼儿子?她和丈夫张宇燕青梅竹马,1987年结婚后,儿子是他们的心头肉。张宇燕是社科院的大咖,忙得脚不沾地,李瑞英也常年在台里加班,家里的事多半靠保姆和老人。可她从没想过,职业和家庭有一天会逼她二选一。 那一刻,她不是没犹豫过,可她太清楚自己的岗位意味着什么——28年零失误的纪录,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次次咬牙坚持换来的。 后来,她在一次采访中淡淡地说:“《新闻联播》是全国的直播,我走不开,不是不爱孩子,是没办法。”这话听起来简单,却藏着多少心酸。 2014年,她退居幕后,告别了那个让她又爱又痛的岗位。如今,她59岁,常参加公益活动,偶尔陪儿子散步聊天。回头看那段日子,她从不后悔,只是偶尔会想,如果那天她选择冲去医院,故事会不会不一样? 夜深了,李瑞英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闪烁的灯光。她没变,依旧是那个端庄坚强的女人。只是现在,她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平静。 《新闻联播》自1978年开播以来,每晚7点的直播从未间断,主持人需提前数小时准备稿件,确保零失误。李瑞英退役后,曾参与《新华字典》APP的录制,她的嗓音依然是许多人记忆中的“国家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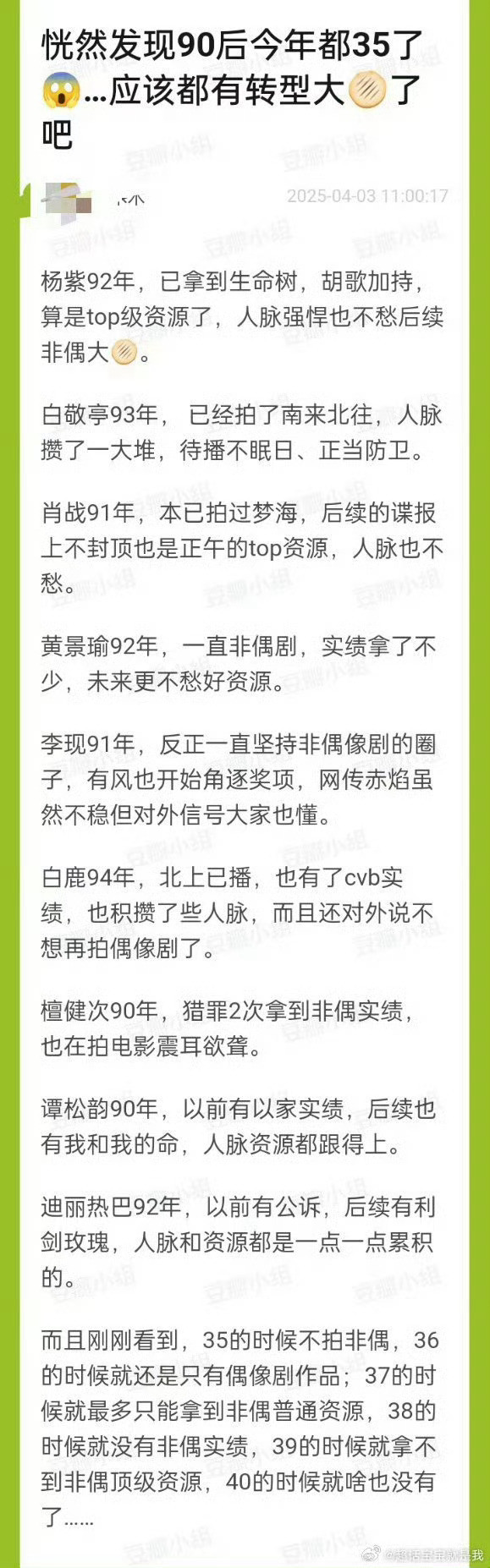

![妈呀笑死了🤣姜甲儒爸爸今天酒醒了还能看昨天的录屏不?[捂脸哭]网友没看够,让他们](http://image.uczzd.cn/72175378262366493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