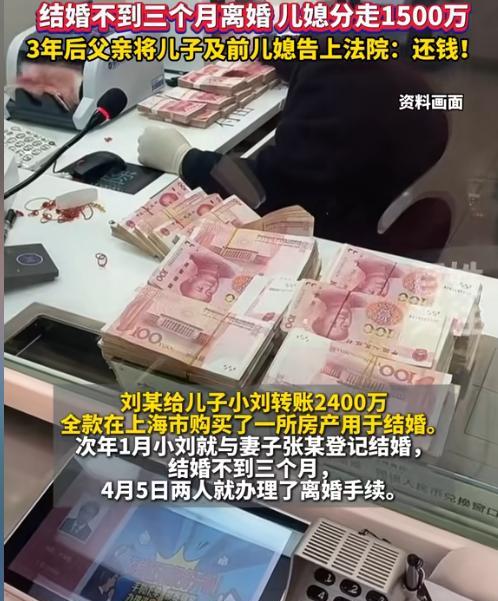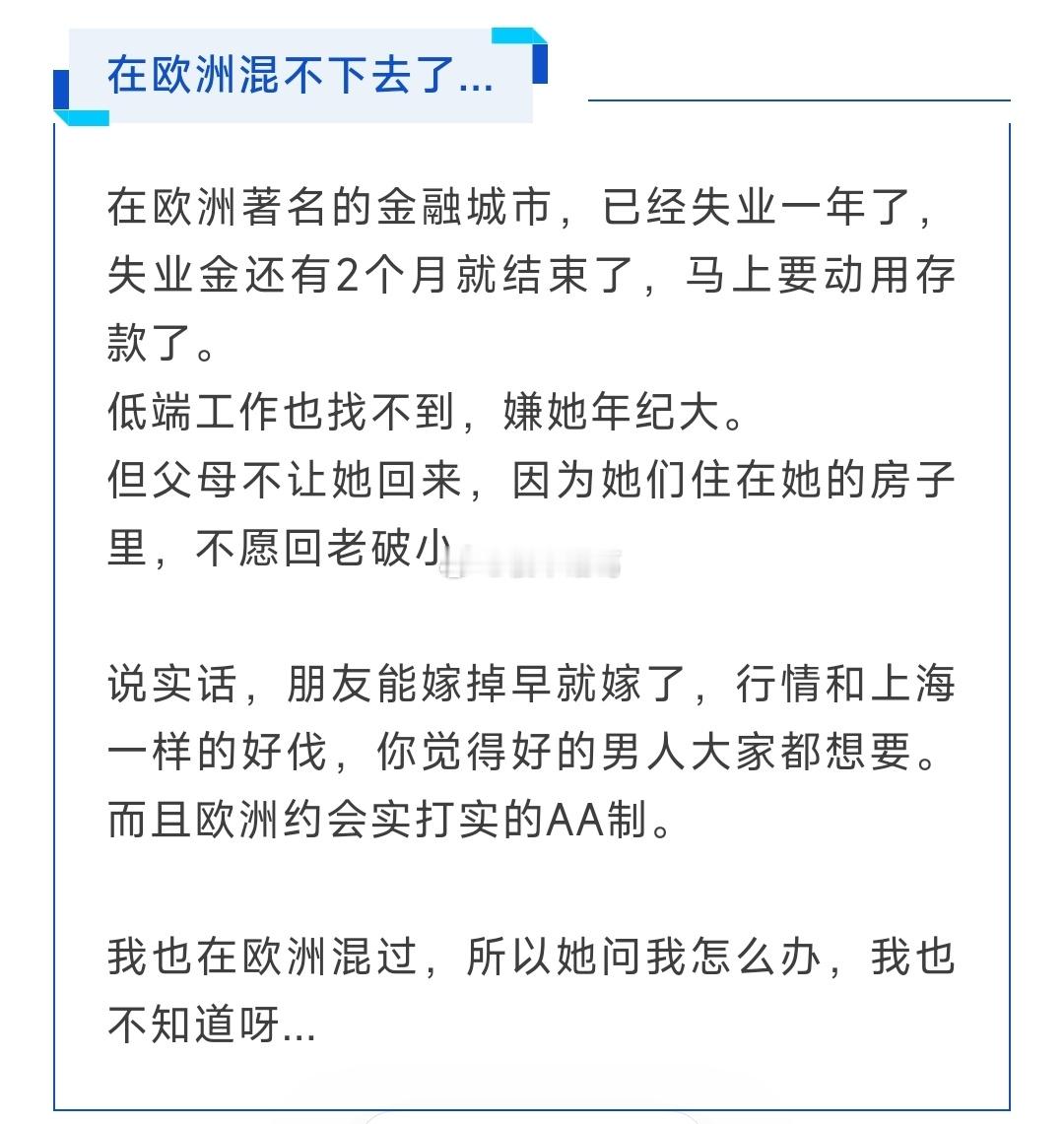上海,女子张某和老师情同母女,为让老师安度晚年,张某买下 125 平房子给老师住,还加上老师名字以便落户,多年后老师去世,张某料理后事欲收回房产,却被老师外甥阻拦,外甥继承百万遗产还想继承房子,张某告上法院,法院会怎么判? 据看看新闻4月7日报道,1983年,女子张某(文中所有人名均系化名)才二十出头,正是青春年少、怀揣梦想的时候。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对音乐的热爱,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 在那里,她遇到了声乐教授陈某。陈某那可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时候,陈某住在学校分配的单身宿舍里,才15个平方。那宿舍条件,别提多差了,隔壁邻居一家四口,跟陈某共用厕所厨房。 陈某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有个弟弟,1984年调到本地另一所高校,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姐弟俩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学院当时优先解决结婚人士的住房问题,陈某一直单身,就一直被安排在后面,所以一直住在那个小宿舍里。 陈某退休了。可退休后的她,还是住在那个小宿舍里。张某毕业后,一直记挂着陈某的生活。 她经常去看望陈某,给她带好吃的,陪她聊天。陈某对张某也是照顾有加,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在张某心里,陈某就是她最慈祥的母亲。 张某看着陈某姐弟俩还住在那个小宿舍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于是,张某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把自己一套房子给卖了,东拼西凑地买了套125平的大房子。 房子收拾好了之后,她就让陈某姐弟住了进去,为了能落户,还在房产证上加了他们的名字。 陈某姐弟俩住进新房子后,那叫一个高兴。他们拉着张某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张某笑着说:老师,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亲生女儿,以后就在这儿安心住着,有啥事都跟我说。 然而,岁月不饶人。2009年,陈某的弟弟身体不行了。张某得知后,急忙赶过去,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心里一阵难过。她陪着老人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为他操办了后事。 之后,张某更是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着陈某。她知道,陈某失去了弟弟,心里一定很孤单。她经常带陈某出去旅游、散心。 2023年,陈某也走了。张某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就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一样。她为陈某举办了隆重的葬礼,送她最后一程。 后事办完了,张某想收回房子。毕竟,这房子是她买的,她也想有个自己的家。可这房产证上有陈某姐弟的名字,要变更还得他们外甥签字。 陈某姐弟留下了百万遗产,被俩外甥继承了。可这俩外甥继承完遗产,还打起了这套房子的主意。 张某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年加名字是为了落户,这俩外甥平常压根不联系,也没赡养过陈某。 陈某生前多次表示,房子是张某买的,去世后要还给张某,主治医生都作证了,外甥也亲口说过房子归张某。 可当记者联系外甥的时候,这外甥倒好,一个劲地推脱,还挂断电话,再打就不通了。张某没办法,只能告上法庭,要求确认房子归自己。 张某四处奔走,收集证据。她找到了当年买房的合同、付款凭证,还有陈某生前留下的遗言。她希望法院能还她一个公道,让好人有好报。 那么,以法律的角度该如何看呢? 一、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在本案中,虽然房产证上登记了陈某及其弟弟的名字,但张某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为自己。 这涉及到不动产登记与实际权利归属不一致的问题。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房屋的出资情况、居住情况、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以确定真正的权利人。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如果张某能证明,当初在房产证上加上陈某及其弟弟的名字,并非真正的赠与行为,而是为了满足落户等实际需要,那么这种“加名”行为可能不构成有效的赠与合同。 法院在认定赠与合同效力时,会审查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财产的交付情况等因素。 二、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在本案中,如果陈某生前留有有效遗嘱,明确表示房屋归张某所有,那么外甥的法定继承权将受到限制。即使外甥继承了陈某的其他遗产,也不能当然地继承该房屋。 外甥在陈某生前并未尽到赡养义务,而张某则长期照顾陈某的生活起居。因此,在分配遗产时,法院可能会考虑这一因素,对外甥的继承份额进行相应调整。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为自己,且陈某生前已明确表示房屋归张某所有。同时,外甥在陈某生前并未尽到赡养义务,因此无权继承该房屋。 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张某所有,外甥需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