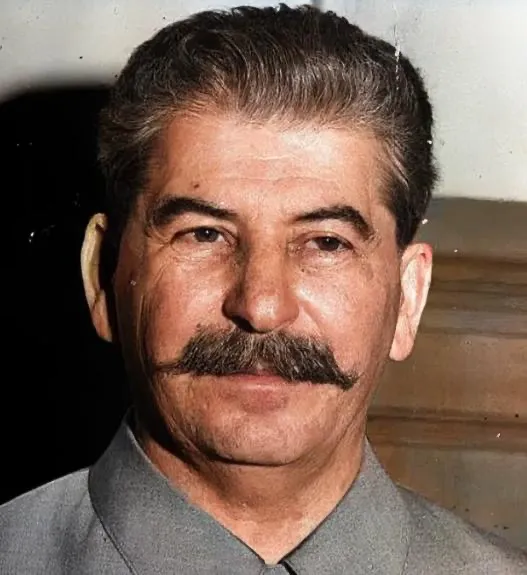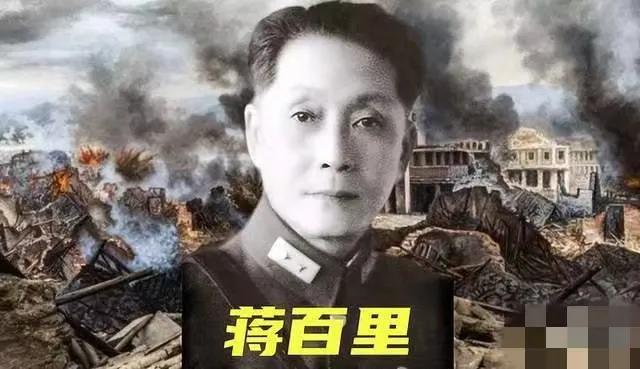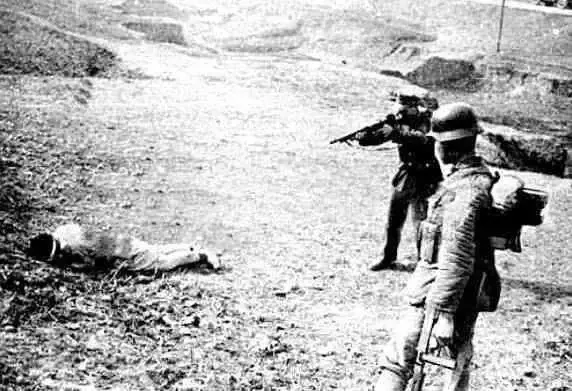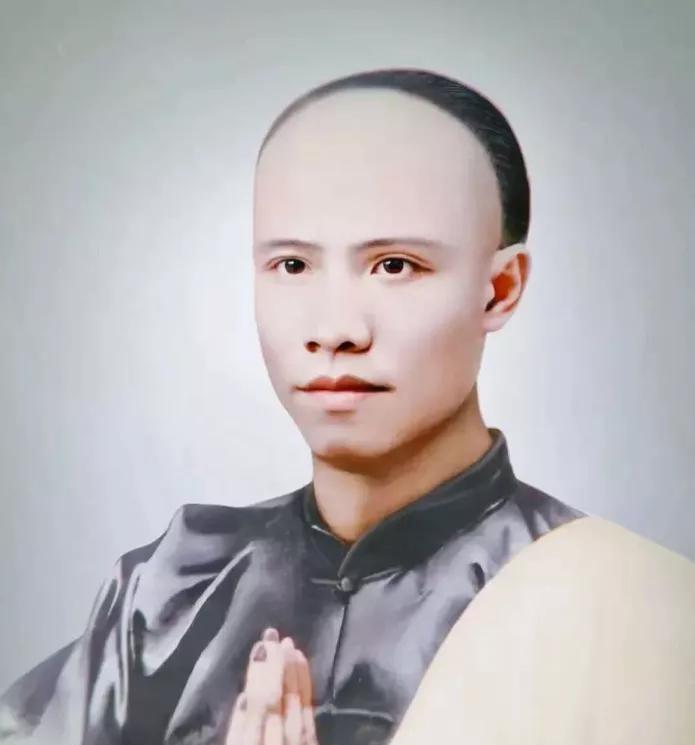1938年6月,日本人准备在丹东大鹿岛,把甲午海战中的沉船,捞上来拆解钢铁。不曾想,先下海的两位潜水员,就出事了,日本潜水员溺毙,中国潜水员生病…… 不是观光,是打捞。他们盯上了海底那批,沉睡了44年的北洋舰队残骸。 “致远”“超勇”这些名字,在甲午战败那年一块沉入水底。 日本人想拆——不是研究历史,是拆钢铁,拿去造坦克造枪炮。 那一年,中日全面开战一年多,钢铁供不上,谁都能拆,连死人底下的船都不放过。 先下水的两个潜水员,一个日本人没上来。 没人知道怎么死的,现场没人说话,只是突然断了气。 紧接着第二个下水的是个中国人,大连人,叫王绪年,船不是他下令开的,任务不是他安排的,海底也不是他熟的,但他硬着头皮下了。 上来之后,人也开始不对劲,连着高烧,咳得厉害,身上没外伤,像是病,但来得又太巧。 有人说撞了邪,有人说被气的。 王绪年住在李桂斌、李桂仁兄弟家,房东叫于永灵。 几个渔民照顾了他一阵,他也开始说起海底的事,大概没人想听这些,但他说得认真,说得沉。 他说,他下水那次,看到了“致远”号。 不是猜,是看到了那块铜牌,直径一尺,海水泡过几十年,上面的字还在——“致远”。 这不是普通船,这是邓世昌的船。 再往下说,就不是沉船的问题了,是人。 他说,进了指挥舱,舱门没坏,开得小心,里头有具完整骸骨,坐得笔直,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 不是水冲进来躺着的姿势,是坐着的,像还在指挥一样。 没人随便坐指挥舱的位置,特别是邓世昌这种人治军严、规矩死的,没人敢擅入。 更何况,甲午开战前,他说过:“阖舰俱没,义不独生。”这样的话,坐在那里,也就只可能是一个人。 王绪年说得慢,但眼神准,他知道这骸骨是谁。 第三天,他又下海了,病还没好,身上还虚,可他又一次下去。 带上布袋,把那具遗骸一点点搬出来,没有仪式,没有命令,也没有录像,只有一个人,和一群村民。 骸骨装进袋子,带上岸,几个人连夜去东口哑巴营,挖土掩埋。 没立碑,没声张,只是埋了,草草一堆,那一夜风大,岛上冷,只有一点点灯光。 日本人不知道,可能知道,也没管,他们只想拆铁,对死人无感。 几十年过去,村里人一直记得那座小墓。 没人敢动,也没人敢忘,不是因为胆小,是因为知道那是谁,孩子出生,老人过世,渔船出海,转回头都得看一眼那块地方。 到了1985年,丹东市搞文物普查,终于有了点动作。 官方说,墓地确为甲午北洋阵亡将士遗骨,但没有科学证据,没做DNA检测,也没有随身物品,认定不了是邓世昌。 结论是:叫“甲午英烈遗骸”。 名字没错,却不够狠,村民不服,几十年供着的,不是无名,是有名有姓有誓言有船号的人。 讲得最多的,就是那句:“阖舰俱没,义不独生。” 学者也起争议,有人说,也可能是林永升,也可能是别人,海底船多,将领也不是只有一个,不能凭“坐姿”断定身份,不能只靠一个人证说法。 王绪年已经不在了,他活着时没人听他说话,死后却因为说过的话,引来一群人争论。 那具遗骸后来被迁了,陵园建在东山北坡,叫“甲午英烈陵园”。 和无名将士墓并排,旁边竖起邓世昌雕像,风一吹过来,刀削似的面庞,眼望海面。 2019年,成了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人来拍照,有人来献花,有人来讲解历史,但没人能说清楚,那一具到底是谁的骨头。 陵园修得好看了,铜像金字刻得亮,可王绪年当年埋下去的那一袋东西,如今再没人敢开。 “坐在指挥舱”那件事,比任何科学数据都沉。 邓世昌是死了,可“致远”号没沉干净,那口铜牌,那座旧墓,那群守墓的村民,还有王绪年那次决绝的下潜,都还在。 1938年,本来是日本来拆船的。 却被一个中国潜水员和几位渔民,用自己的办法,给历史封了一道口。 不靠权力,不靠学位,不靠任何机构背书,只靠一口气,一点信。 打捞这事儿,到最后不是捞船,是捞记忆,不是为了修历史,是为了救尊严。 参考资料: 胡中明.《大鹿岛的忠魂:王绪年与致远舰铜牌的故事》.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文献,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