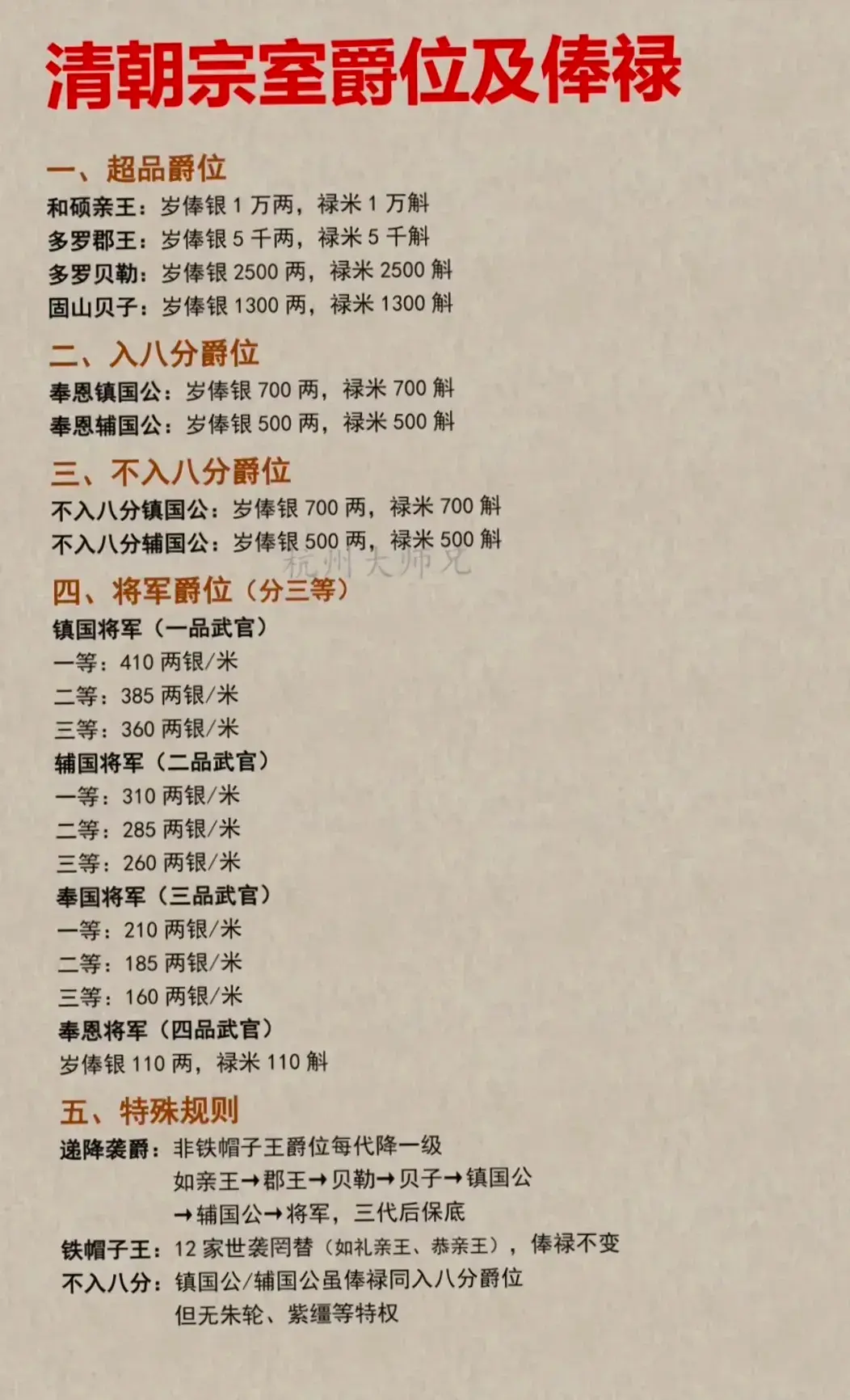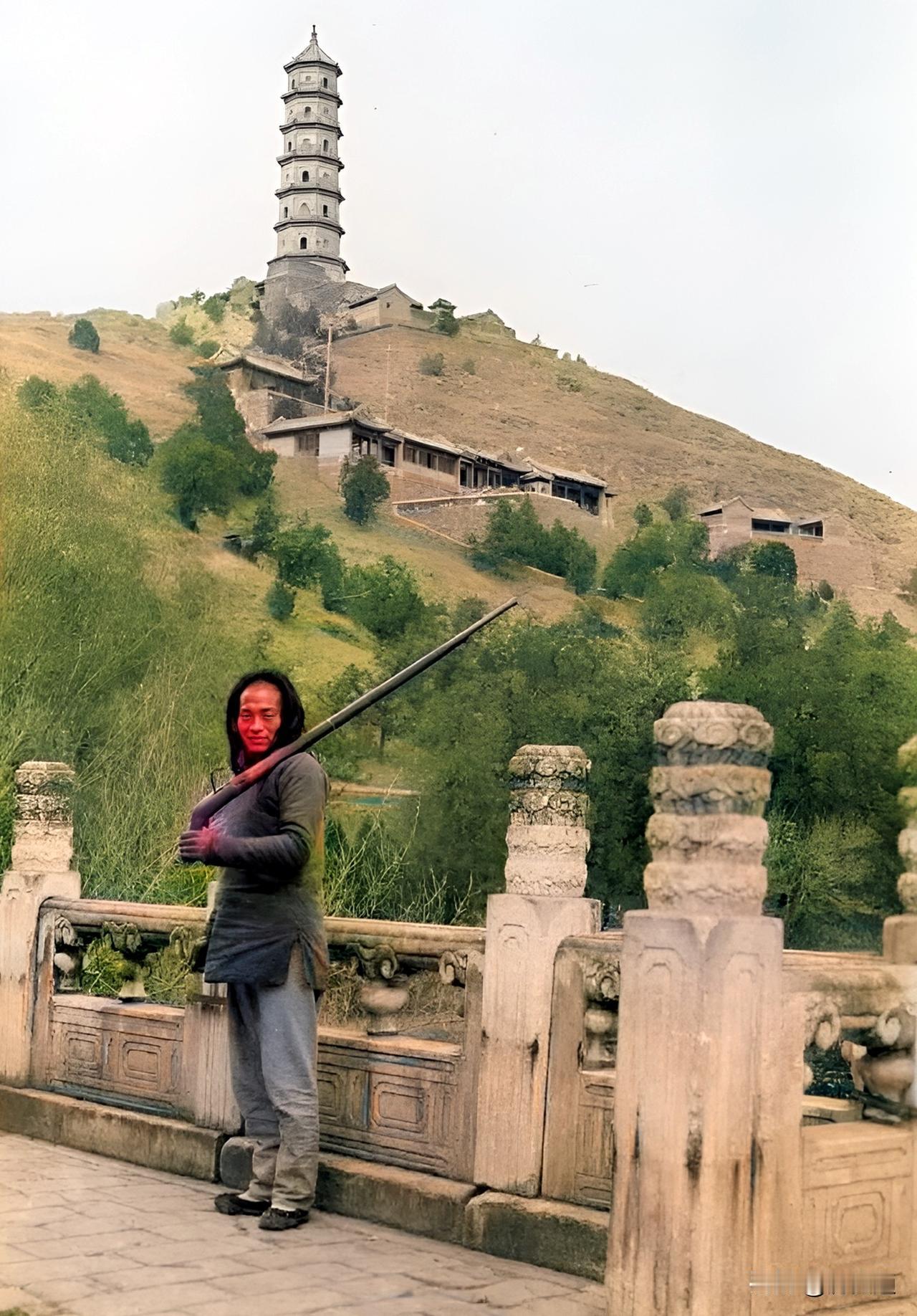1946年秋天,曾泽生带着他的60军进驻吉林,住的地方不是营房,而是一间10平米的破庙方丈室。
士兵们挤在旧粮仓,军部设在关帝庙,连张像样的桌椅都凑不齐。
更丢人的是,当地的官员公开在报纸上宣称另一个军长才是真正的指挥官,曾泽生这位军长,被架空了。
更绝的是,这支部队连补给都要不到,被骂作“60熊”,从军长到笑柄,不过短短几个月。
事情要从60军调防东北说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着急往东北布防,曾泽生带着滇军部队被派去守吉林。
当时东北局势混乱,部队疲惫,装备破旧,刚安顿下来就遭遇冷脸。
国民党在吉林的地头蛇梁华盛是嫡系出身,根本看不起这支“杂牌军”。
曾泽生到吉林后,向省政府申请军部驻地和军官宿舍,结果被告知:“吉林辖区太小,房子不够。”
最后军部只分到一个破庙办公,曾泽生自己也只能住在庙里的方丈室,四面漏风,连灯都没有。
部队住得苦还不是最惨的,更难受的是没有兵权。
梁华盛直接任命了新38师的李鸿为吉林城防总指挥,这李鸿是他自己的人,电台和报纸里天天喊的是李鸿的名字,连曾泽生的部下看了都心里发毛,谁才是老大?这还怎么打仗?
驻地没房子、军长被架空、将士吃不饱,60军原本就已经打得七零八落,这时候补给也断了。
部队开口要粮,换来一句话:“天天打败仗,还有脸住房子、吃饭?”
梁华盛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当众冷笑,说:“你们这些60熊,想要粮食,就去敌人那儿抢!”
兵士气得哭,有的甚至扒门框上吊,曾泽生看着眼前这支军队,满脸是灰。
可这事还没完,部队苦、装备差,战场上自然吃亏,可每次打了败仗,曾泽生都要挨骂。
他向上级请示撤退,杜聿明卡了两天,等敌人包了饺子才来电批“准”。
184师顶不住,投了共军;21师全军覆没,报纸上把这些全算在60军头上。
吉林街头巷尾都流传着打油诗:“出兵不离鸭子架,山沟里头来回钻;白天前进夜晚退,几乎全落大酱缸。”曾泽生听到时,脸上发青。
外人骂也就罢了,最让他寒心的是自己的同僚,有一次开会,一个参谋不点名讽刺:“有些部队啊,连阵地都不会守。”
其他人都笑了,曾泽生没吭声,晚上回到庙里,把军帽放在桌上坐了半宿,庙外是呼啦啦的秋风,庙里灯都没有,黑得发冷。
60军在东北被称“60熊”,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连带士兵都被地方百姓看不起,买东西不给账,借口说“你们反正不打仗。”
有人出去剃个头,还被理发店赶出来,军纪也开始散了,有士兵在街上偷东西,被警察当场打断两根手指,曾泽生调来宪兵整顿,根本压不住。
其实早在1947年,曾泽生就对国民党的派系斗争灰了心。
他向南京打报告说:“军纪日益涣散,士气低落,请求调防。”没人理。
那一年冬天,吉林下大雪,粮食断供三天,有部队官兵被饿死。
师部报告打上去,压了十天才批下来两袋米,部队自己去城郊挖野菜,挖到冻土层里,把锄头都磕断。
局势一天天恶化,辽西会战失败后,国民党节节败退,60军也被迫向南撤,战场上武器不敌,后方又无补给,部队几乎散架。
1948年9月,部队撤到长春外围,一口气打了七天七夜,伤亡惨重,城里弹药堆着,60军却一个子弹都没分到。
曾泽生急得直拍桌子,结果上面还是一句话:“60军无战斗力,慎用。”那晚,他在自己的作战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圈住了部队的防线,然后在纸角写下两个字:“生死。”
再往后打已经打不动了,部队不想再死,士兵开始传话:“听说对面给吃给穿。”有营长来报告,说底下有人想投共。
曾泽生让他滚出去,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待了一整夜,第二天他没有抓人,反而召集全军军官开会。
会上一句话说得很重:“不是我们不想打,是没人想我们活。”
1948年10月17日凌晨,长春外围突然传来爆炸声,不是敌人打来的,是60军主动放弃阵地,全线投诚。
曾泽生站在城外土坡上,穿着旧棉大衣,对迎上来的解放军说:“我是曾泽生,第60军军长,愿带全军起义。”
起义后,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新番号,新编制,曾泽生留任军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干部。
部队换了制服,住进整修过的兵营,饭堂每天有米有菜,最重要的是,没人再骂他们是“60熊”。
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第50军奉命入朝。那时候他们还没完全换装,很多人穿的是缴获来的美军棉衣。
可打起仗来,这支部队一口气顶了三次大仗,第三次战役,他们跟39军一起攻进汉城,拿下市区西南角。
汉江阻击战最惨烈,打了整整五天,50军伤亡六千多人,硬是拖住了美军增援部队,美军在报告里称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单位”。
那年冬天,曾泽生站在汉城郊外雪地里,看着营地里冒烟的伙房,嘴里说了句:“从60熊到50军,老天给我们开了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