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有点牵强。奈何这么说的人真的多,且司马迁、王充竟都是何等级别的人啊——且他们这么说的用心又无疑都是好的。至此,还须问,为什么同样一首诗会有这么多理解?听谁的为最宜?……
《关雎》之诗,无人不知。但它究竟在写些什么,该作何理解,其实一直是一笔“糊涂账”——争议不断。历朝历代方家意见,少则已有如下之三。其一,就是文本的字面意思,此《诗经》首篇之谓:对心上人的单相思也(傅斯年等)。这种说法,姑妄言之,属于它的“过去理解”。纯然由文本而发,自“关关雎鸠”由不知哪一位先民唱出的时刻——其很久很久以前已有。“最原始亦最贴近实情”,“最过去亦最现在”,今天的语文课上,因此大都讲这一种理解。其二,这是一首赞美诗,赞美周天子的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毛传》等)。孔子推而倡之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为后世君子树立了婚姻人伦的典范。
——好像……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姑妄言之,曰:“未来理解”——以“伦常即王道”寄予后世,供后之览者学之行之。

其三,这是一首讽刺诗,与上述赞美诗的理解则完全相反。汉儒多持此理解。如王充在《论衡》里说:“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晏”即迟到、耽误国家正事儿,《史记》《淮南子》《风俗通义》等一大批汉儒之书均言《关雎》为讽刺周康王好色误事而作(《史记》同时又赞成赞美说,见诸《外戚世家》)。这就属于是“当代理解”,据史说诗,据诗说史,意在劝谏他们当时的帝王以周康王那段荒唐的经历为戒。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有点牵强。奈何这么说的人真的多,且司马迁、王充竟都是何等级别的人啊——且他们这么说的用心又无疑都是好的。至此,还须问,为什么同样一首诗会有这么多理解?听谁的为最宜?
——近代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先生在《诗经学》中说得甚好。要言之,三种说法都得听,又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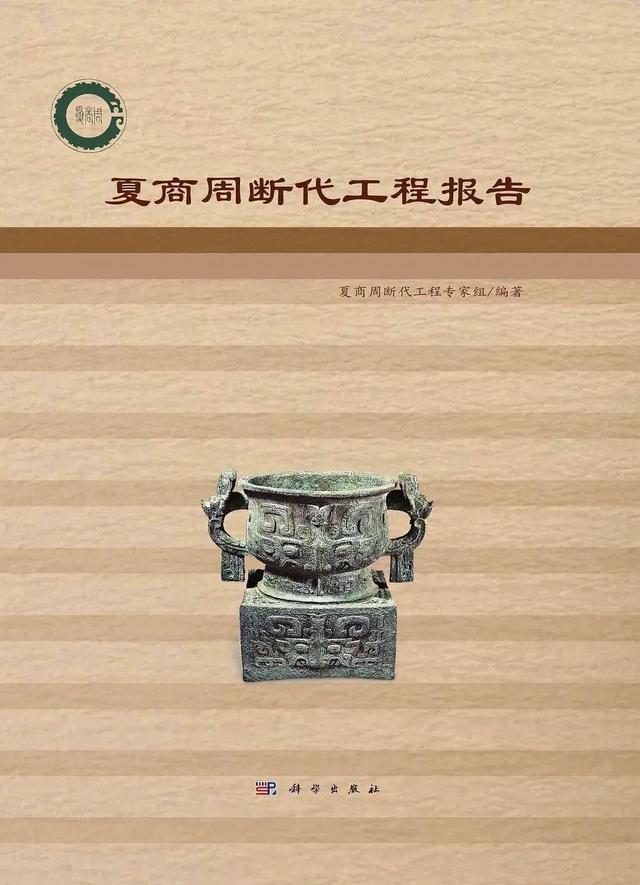

这就涉及到《诗经》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起先,“关关雎鸠”等尚是草昧的民歌,已在某一地区长久地流传,百姓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由来已久——这便形成了“过去理解”,亦胡氏所说的“作诗之义”。继而,周朝派人把这些民歌采集回来,这便形成了“采诗之义”——朝臣因之拿到了这些“净化版本”,推而阐发为各自的“当代理解”,为这些原本的民歌加诸种种新鲜的、政治性的注脚。最终,《诗经》其最终还经历了孔子等人删诗的过程,遂成“删诗之义”、“未来理解”——《关雎》诸诗,因之又加上了一层道德意义上的注脚。综上,后之览者不妨根据自己对《诗经》个性化的需要选择一种或两种诠释即可——为了感受文学的美好,亦或者为了走近历史、修身养正。
——是所谓“三种说法都得听,又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听”,各安对这首诗的所需就挺好。这是由《诗经》的特殊性决定的。

后世之诗则不必如此去读。1、屈原之后,诗人署名越发明白,即“文学”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事业,而再不像《诗经》三百零五篇,竟几无一位确信的作者(仅个别《雅》篇结以“吉甫作诵”、“寺人孟子”)。尤其《国风》,基本上篇篇没有确信的创作背景,而大约只知道它们是从哪里采集来的。2、文学事业既已趋于独立,文本作者既已趋于清楚,则各个诗篇的创作背景自然清楚——此如《楚辞》诸诗既然紧紧跟着屈宋,何忧何愁,没有头绪吗?3、后世也不会再有《诗经》这种特殊地位的诗了——不会再有:一部诗集而已,周文王、周公、孔子及历代宗师竟都为了它煞费苦心。诗而称“经”,别无分号。所谓经典,其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纲领也,其整个中华民族世代共享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迩之可以事父,远之可以事君(《论语•阳货第十七》)……
——若屈宋李杜是文学中的水草嘉鱼,《诗经》便是那鱼缸;无数中华先民的生产生活便是那鱼缸赖以取水的江河湖海。
写于北京家中
2024年8月17日星期六
【主要参考文献】《诗经》,《论语》,司马迁《史记》,《淮南子》,朱熹《诗集传》,胡朴安《诗经学》,闻一多《诗经讲义》,傅斯年《诗经讲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