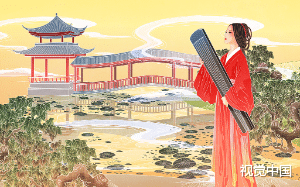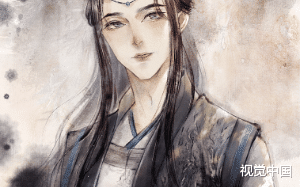相传,这世上有种失传已久的技艺,名唤指画。
我娘生得一双纤纤玉手,以血为墨,以指为笔,便可生死人而肉白骨。
名动天下的女将军遇敌夜袭,除她外无人生还。
她抓了我娘,放干我娘的血,逼迫我娘以指作画,救活她的所有将士。
美其名曰:“舍小家为大家,此乃大义。”
“我将为你立功德碑,世世代代受人尊崇。”
可她不知道,我和我娘不想要什么狗屁的功德。
我只想要我娘活过来。
只要她死,我娘便能活。
1
我是被秦余翀带回边疆的。
他是戍守边疆的镇关王,遭山匪劫持,不慎掉下山崖,是我救了他。
我同他定了终生,伤好后,他便带我回了王府。
谁知刚一回府,就撞上宋铃之在教训人。
粗壮的鞭子毫不留情地落在那女子娇嫩的脸蛋上,刹那间便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镇关王是什么人物,岂是你们这群腌臜贱婢能够肖想的!”
“竟敢脱了外衣爬床,如此不知羞耻,那本将军就成全你们!”
“来人,把这贱婢扒光了扔外面去!”
“将军饶命啊,将军饶命——”
那女子的皮肤白得晃眼,却横亘着一道又一道血淋淋的伤痕。
很快,她被扒个精光,被人拖出去。
路上是一道道鲜红的血痕。
宋铃之很不耐烦:“既她如此爱被人看,便挂在城墙上,被看个痛快!”
偌大的王府上下竟无一人劝阻。
甚至于一群人还要对她瞻前马后,端茶送水。
只我一人坐在石桌上饮茶。
我知道她早看到了我,只是一直在观察。最后也是她先按捺不住,拖着又粗又长的鞭子朝我靠近。
“王姝年。”她露出警惕试探的眼神,“是吗?”
“民女见过将军。”
我这时才起身见礼。
她热络地握住我的手腕,滚烫的掌心十分灼人。
她在笑,但笑意未达眼底:“我幺叔从未婚娶,本以为他就要这般孤独终老了,倒没想到竟能有此缘分,掉下山崖都能寻到佳人,当真可喜可贺啊。”
一字一句,皆是试探。
我只作不懂:“确实很巧。”
她的笑便冷了几分。
我能怎么办?
总不可能老老实实告诉她,这的确不是个巧合。
告诉她镇关王只是我的踏脚石。
我是为她而来。
为,杀她而来。
2
我在山崖下,已住了十余年。
我没有爹爹,只一个娘亲,甚至于娘亲也不是我亲生的娘亲。
在我还是个婴童时,就被亲生父母遗弃。
天寒地冻,我冷得哭都哭不出来时,是娘亲将我抱回了家,打那以后,我们便相依为命。
我本以为余生都会如此平淡结束,却没想到,十四岁那年,一场战乱不仅让天下风雨飘摇,更直接夺走了我娘的性命。
这世上有种技艺,名唤指画,以血为墨,以指为笔,便可生死人而肉白骨,它失传已久,只因我娘带着我隐居世外,再不问世。
我娘生得一双纤纤玉手,既是救人的手,亦是伤己之手。
那一日,天生异象,黑云压城,狂风骤雨之中,是宋铃之和她的几百精锐在逃命。
他们遇敌夜袭,陷入困境,最终除她外无人生还。
宋铃之是名动天下的女将军,护佑边疆,从无败绩,除了自身能力出众,其实更多是依仗她手中的那只精锐。
可以说,没了他们,她的实力将大打折扣。
于是,她找上了我娘。
那个深夜,我被我娘藏在米缸,鼻尖是浓郁的血腥味,我不敢出声,只能捂着自己的嘴瑟瑟发抖。
雷鸣声中,是宋铃之冷漠的话语:“宋青之,你总是如此自私。”
“你一个人便能救我泱泱大国,有何不妥?”
“舍小家为大家,此乃大义!”
宋铃之口中的大义,便是放干我娘的血,用她的命,来换她手中精锐的命。
何其可笑。
那一日,我娘成了一具干尸。
宋铃之连她的双眼都不帮忙合上,却说:“我将为你立功德碑,世世代代受人尊崇。”
可她不知道,我和我娘不想要什么狗屁的功德。
我只想要我娘活过来。
我娘的尸体被我存于冰棺之中。
我娘自小教我指画,我学得很好。可惜我不是她的亲生孩子,我的血不能做墨。
但宋铃之的血可以。
她与我娘是亲姐妹。
只要她死,我娘便能活。
3
秦余翀在婚期前两日回来。
宋铃之比我积极,一大早便来王府等,坐在府湖旁实在无聊,还顺便教训了两个她看不顺眼的奴仆。
其中一个是照顾我的贴身婢女春念。
只因她端上的茶水还是滚烫的,便被宋铃之兜头泼下。
宋铃之一巴掌狠狠落在春念脸上,春念被打得脑子一懵,迅速跪倒,瑟瑟发抖,还主动朝自己的脸上扇巴掌:“将军饶命,将军饶命……”
她的脸被茶水烫得通红,打自己脸的手却丝毫未停。
直到我按住她的手:“将军何必如此。”
宋铃之笑了:“我教训一个下贱的奴婢而已。”
“王姝年,你还没嫁进王府呢,就想摆主母的架子了?”
“也不看自己够不够格!”
她抬手一挥,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我没想到她会直接动手,脑子被打得嗡嗡的,下意识就往前一推。
宋铃之瞬间摔倒在地,身体距湖水仅一寸之遥。
“王姝年,你竟敢推——”
话语未落,已陡然直转:“王姝年,我已同你说了,我与幺叔只是普通叔侄关系,你怎能妄下断论,侮辱我与幺叔的感情——”
紧接着,又朝着我背后喊道:“幺叔,我瞧在你的面子上,才特别尊重你这未嫁娘子,她却十分善妒,对我随意出口侮辱,刚刚还说要将我推入湖中给我个教训!”
“这般女子,你当真要娶?”
我回头,对上秦余翀的视线。
其实,这才是宋铃之的真实目的。
之所以选择秦余翀做我的踏脚石,也正因如此。
宋铃之虽只是秦余翀的侄女,却打小就被送来边疆,与他相依为命,感情极好。
秦余翀也曾有过好几个要走到一起的姑娘。
可惜,全都意外丧命。
除了宋铃之,还能是谁的手笔?
我干脆冷笑一声,坐实宋铃之的胡言乱语,抬手将她推下湖。
4
宋铃之快疯了。
她水性不好,在湖中挣扎,呛了好几口水,险些丧命,好不容易被秦余翀救起。
倒在秦余翀的怀里,宋铃之刚缓过来,就猛地跳起,抓着鞭子往我身上打。
被秦余翀拦下:“铃之!冷静!”
宋铃之何曾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她恶狠狠地看着我:“幺叔,你没看到吗,这贱皮子方才竟直接伸手将我推入湖中!”
“你还要护着她?!”宋铃之望向秦余翀的眼神,七分愤怒,三分委屈,眼眶微红,泫然泪泣。
一个娇娇美人,如此可怜兮兮要求公道,换做是谁,也得心软。
可秦余翀只是叹了口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铃之,此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你先回吧。”
宋铃之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幺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这么喜欢这女人,如此护着她?”
秦余翀咬牙不言,我倚栏而立,眼神平静:“王爷,方才是宋将军先对我这幺婶出言不逊,作为长辈,我只好教导一番。”
“王姝年!你还没过门呢!”
她冲上来就要抓我的脸。
秦余翀一把握住她的手腕:“够了!”
宋铃之却全然失去理智,狠狠甩掉秦余翀的手,一字一顿道:“幺叔,为了个女人,你便要毁掉你我情谊吗?”
她神色阴冷:“别忘了,你是靠谁才活到现下的。”
秦余翀一怔,松了手。
宋铃之捡起地上的长鞭,与我错身而过时,声音却轻轻飘起。
“王姝年,你当真以为自己能顺利嫁入王府?”
“还做什么幺婶,痴心妄想!”
5
大白天的,秦余翀点了盏灯。
人油灯。
那是宋铃之为他特制的,每月初三送到,日以继夜地点,方能为他续命。
秦余翀曾告诉我,与其痛苦地活着,不如畅快的死去,但很可惜,有宋铃之在,他连求死也不能。
“你何必跟她闹。”秦余翀盯着跳跃的火苗,幽幽叹息,“明知道她锱铢必较,这样只会毁了你我的计划。”
“见她不惯。”
我冷哼一声,直接吹熄那盏人油灯,秦余翀瞬间咳出一口鲜血,苍白的脸刹那潮红。
“怎么,你心疼了?”
“要知道,她为了给你续命,可是每月都要放出一碗鲜血。”
“也着实是情深义重了。”
秦余翀攥紧瓷碗,手指被碎掉的边角划伤,却无鲜血涌出。
昏暗的环境之下,我看到他眼神怔然,幽幽道:“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算什么情深义重?”
秦余翀早该死在十年前的一个隆冬。
敌国破军,长驱直入,他被将首斩于马下。
宋铃之携兵数万,将他救回,杀了敌国一个片甲不留。
那是宋铃之的成名之战,却是秦余翀噩梦的开始。
本该死了的他,又活过来。
但宋铃之从未问过他,还想不想活。
6
前线战事再次吃紧。
敌国将破嘉乾关,若是继续长驱直入,我国根基将毁。
皇上的圣旨如鹰破云,直接飞入了宋铃之的手中,她气得摔了兵符,让三百兵锐全都滚出营帐。
还骂他们连狗都不如,狗被抢了吃食还得奋起直搏呢。
彼时我正在挑选要做喜服的布料。
大红的料子,用金线绣了些牡丹的花样,精致华贵。
我都打算付钱了,一个长得小家碧玉的姑娘突然冲过来,非得管我要这匹料子。
我扔下一粒金子:“抱歉,我先给了钱。”
她却抄手就把那金子扔了,放了一坨金锭,直接把那布料从我的手中抢过去。
毫不客气:“你算什么东西?我哥可是宋将军的心腹,这匹布料我若要,你敢不给?”
眉毛飞舞,眼梢上吊,一举一动与宋铃之皆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知道这位凌微微凌小姐脾气骄纵,但着实没料到她竟与宋铃之如出一辙。
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