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六祖慧能在曹溪竖起顿悟成佛的大旗,许多弟子在他的启发下,当下开悟,犹如跃过龙门的鲤鱼,遨游天海,喷云播雾,好不潇洒。
因此,曹溪名声大噪,成了天下禅僧心目中的圣地,大江南北的学僧望风而动,争相来投者不绝于途。
可这样一来,宝林寺原来的殿堂、寮房就显得局促狭窄,不足容众了。
有一天,行思对慧能说:“师父,近来从各地来的学僧超过了千人,再过几日,远在数千里的荆州通应律师,也将率领他的数百名徒弟来皈依您,寺中的房屋已不够居住了。”
慧能说:“那就找几处山水清幽的地方,再建几处寺院吧。通应律师是我受戒的师父之一。他反而来皈依我,不能太委屈了他们。”
“是,不过……”

行思欲言又止,慧能问道:“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吗?”
行思说:“整个曹溪几乎每一座山、每一块地,都是大财主陈亚仙的。他为人极为精明,从来不肯施舍一文钱,恐怕……”
慧能笑着说:“他若不精明、吝啬,如何能攒下如此大的家业?这种人,甭想向他化缘,他连一粒米都不会布施,怎舍得大片土地?你去请曹善人通融一下,我们花钱置买他的山场好啦。”
“可是,寺中聚集了上千名僧人,尽管大家遵照您的指示,开荒种田,力争自给,但每年增收的粮食远远不如新增加的人多,大家的伙食钱都很紧张……”
慧能从铺下拎出一个小包,说:“这是前几天印宗大师捎来的几十两黄金,正好派上用场。”
然而,千金难买人如愿。
行思、刘志略与曹叔良那几天省了饭菜,因为他们在陈亚仙家饱尝闭门羹,一说来买地皮,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于是,一天,慧能带着婴行,沿着山野道路,向陈亚仙家走去。
路上,婴行蹦蹦跳跳,他一会儿嗅野花,一会儿追蝴蝶,极为快乐。连慧能都被他的天真所染,显得年轻了许多。
婴行吹散了一支蒲公英的种子,种子们带着小伞随风飘荡。
慧能见状,不由自主地吟起四祖道信的偈子:
花种有生性,得地就能生。
因缘如不合,全都不能生。
婴行说:“师父,你吟的是你的太师父四祖的偈子吧?”
慧能点点头,称赞道:“小婴行现在不光贪玩,也知道用功啦!”
“师父,你老人家今天的兴致真好,肯带着我游山啦。”
“谁说这是游山玩水?咱们是去化缘。”
“化缘,有师兄弟们,用得着六祖您?”
慧能说:“今天咱们化的缘很大,非得我这个老头子出面不可。”
婴行兴奋地问:“化多大的缘?”
“整个曹溪。我们得让陈亚仙把曹溪的山水林木、土地房舍都布施给宝林寺。”
婴行突然捂住肚子,哎哟哎哟叫唤起来,像肚子很疼似的。
慧能不理他,顾自向前走。

婴行蹲到地上喊:“师父、师父!”
慧能脚不停,头不回,说:“婴行,你是不是想说,‘师父,我肚子疼,先回寺里啦,你自己去化缘吧!’啊?”
婴行见露了馅,便不再装傻,问:“师父,你怎么知道的?”
“你呀你,这些年来,啥时候骗得了我?”
婴行将衣袖捋起来,一边往手上吐唾液,一边说:“师父,咱们是不是找上几十个人一块去?”
“干啥?咱们去化缘,又不是去打架。”
“可是、可是……陈亚仙这个大财主,最最可恨了。他经常放恶狗去咬到他家讨饭的叫花子,僧人去化缘,他甭说施舍,连个好脸都不给。真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您老人家想要抢走他的全部家业,他还不跟咱们拼老命!”
慧能笑道:“什么抢呀、夺呀的,多难听!出家人化缘,是让人家自愿布施。”
“他能自愿?行思师兄和曹善人为买他的地,不知跑了多少趟,说好话快把嘴皮子磨破了,他也没答应。他卖都不肯,舍得白送人?”
“我去给他治病,他总得给我一些出诊费吧?”
婴行来了劲:“噢?陈亚仙病啦?活该!师父,你咋不早说是去治病,白让婴行肚子疼了。”
慧能神秘地一笑。

说话之间,慧能与婴行已经走到了陈亚仙家的大门前。
既然宝林寺的六祖亲自出了面,尽管一百个不情愿,陈亚仙也不得不将他们让到了客厅。
丫环上过茶后,陈亚仙开门见山说:“大师亲登寒舍,一定也是为置地而来。不瞒你说,我们陈家,只有置买别人家土地的习惯,从未有过典当房屋、出卖土地之类的败家事情,所以……”
婴行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你别狗眼看人低,我师父是来给你看病的!”
陈亚仙大笑:“哈哈……我有病?小师父,你没发高烧吧?”
“你才发高烧呢!”
“没有发高烧,你怎么说胡话?我有病!你看我像有病吗?”
婴行望望陈亚仙,他红光满面、中气十足,确实不像有病的样子。他不解地看着慧能。
慧能肯定地说:“陈施主,你确确实实病了,而且,病得极为严重,可说已病入膏肓。放眼天下,也只有贫僧可以救得了你。”

陈亚仙不高兴了:“大师,你是佛门弟子,怎么乱打诳语?有病没病我自己不知道?”
慧能严肃地说:“有一些病症,病人自己能感觉到;还有一些病症,不到命终,病人很难察觉到。而一旦感觉到时,什么都晚了。”
陈亚仙将信将疑:“哪,你说说,我得的是什么病?”
“医者诊病,望、闻、问、切。在未诊脉之前,贫僧可不敢随便下定论。”
陈亚仙早就知道慧能是得道高僧,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现在又见他一本正经,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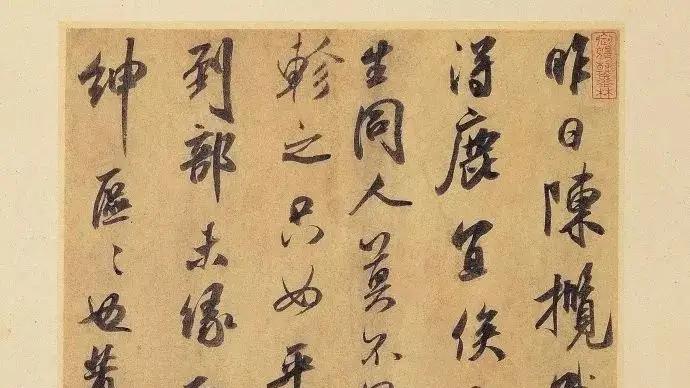


写半截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