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我曾收到一封信,是我那动不动就抱恙在家的未来夫君唯一送来的。
信中简简单单几行字,却处处写着「不愿」「嫌弃」二字。
我撕了,碎屑埋在花盆地下,除了我,无人知道。
直到,婚事一搁再搁,传来少年战死沙场的消息。
-
八岁时,阿爹和我说,在远方,有一个少年,他眉目如画,是我的夫君。
我握紧了手中的糖人,「夫君是什么?」
阿爹摸摸我的头,「夫君啊,就是要和幺儿过一辈子的人」
我舔一口糖人儿。
「那不要他,要阿爹和阿娘」
阿爹笑得和煦,「好好好」
十岁那年,来了一户人家,男子雍容,女子华贵。
都是上好的面容,我趴在墙上,偷偷瞧着。
阿爹说,那位远方的夫君的阿爹阿娘,来看我了。
我是想瞧未见过面的夫君一眼的,可并没有。
只有和阿爹阿娘一样高一样大的人们,里边,并没有少年。
阿爹说,少年正生病了,不宜长途跋涉。
我咬着手指。

阿爹和我说过,这个少年英勇非凡,小小年纪舞刀弄枪,英姿飒爽。
提到我未见过面的夫君,阿爹平和的脸上也会有得意。
少年人中豪杰,天资聪颖。
十二岁那年,我收到一封信。
信的落款,写着严和二字。
我撕碎了那封信,埋在了花盆底下。
阿爹说,少年从军了,让我再等等。
等他回来,就立刻成亲。
我等呀等,等呀等。
十八岁的那年,终于等来了一封信。
是给阿爹的。
阿爹看后,沉思良久。
次日便和阿娘找了媒婆,要给我相看人家。
我默默收拾了包袱,留了一封信,去了那信中少年死去的地方。
无他,做了那么多年我的夫君,连一场面都没见过,说不下去。
一路北上,我去了那荒凉的北山。
几经打听,才知道是有一只军队,在北山战役中不知所踪,应是凶多吉少。
「姑娘啊,那地可凶险得很,别说你了,就是老婆子我在这住了几十年,都不敢去」
我辞了妇人,顺着她给我的路线,一路而去。
路途荒凉,不见野兽。
唯有阴风嘶嘶,如怨如泣。
大风呼啸,平沙漫地。
走了许久的我,停滞不前。
要不,就在此处吧。
拿出包袱里的符纸,掏出火折子。
安歇吧,少年。

我来送你最后一途。
突然间有了声响。
脚步有节奏,不是一人。
一支破破烂烂穿着盔甲的人群向我走来。
符纸照亮了他们的身影。
「有人」
「真是人」
这支人群大叫起来,围在我身边。
「天助我也!」
一个人举起双臂,情绪激昂。
心里诧异过后,我只觉,世事难料。
因我在他们围成一圈中,听到了一个名字。
严和。
真是难得的一次慈悲做戏,反倒,哎。
「姑娘是怎么进来这里的」
这支人群里唯一一个面容还干净,气质卓群,沉稳的男子,问着我。
他的眼里,可都是怀疑与计较。
其他人都是高兴着欢呼。只有他,一直盯着我。
看样子,他是这群人的领头人。
「我去寻远房亲戚,时间急,这路最近」
我不看他,包好包袱,压住里边剩余的符纸。
他心思缜密,拿起烧掉的灰烬,端详着。
「姑娘可是在祭奠人?」
说得肯定,目光让我不敢编瞎话。
「不是,天太黑了,我点个光」

他将信将疑,默不作声了半晌。
最后直接盘坐在地,离我一步之遥,闭眼歇息了起来。
我往过挪。
却听到一声冷静的音。
「姑娘早些歇息,明早还要麻烦姑娘带路呢」
虽然他看不到,我还是恰媚地点头。
瘫坐在地,真是倒霉,这人,就是严和。
1.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严和拍着手腕上的泥,不经意问我一嘴。
我正好瞧见他手上青筋毕露,衣下覆盖嫩白的皮肉。
我不自觉咽了下喉咙。
「我姓刘,将军可叫我刘姑娘」
舌头打结,尴尬地瞟了一眼面前的严和。
严和不置可否,点点头。
救命,一看到他我就抖得厉害。
他看了看天色,心不在焉「这一路烦请姑娘带路了,出去之后严某必将重谢」
我的嘴又没出息地弯起。
「严将军客气,客气」
不必谢我,离我远点就行了。
「呦,严和你又来找刘姑娘了」
在严和又再次来盘问我是何城人时,其他男子一拥而来,打趣着看我俩。
我正寻思着该说哪城人,这些男子一来,严和也不知怎么回事,面色一红,任由男子们拉走了。
天,要是被他知道我就是刘送姬,说不得他立刻要带着那帮兄弟离我而去,不愿跟我沾半点关系。
还好我是记得路的,约莫再三天,就能出去了,我也能解放了。
到时候,还是立刻回家吧。
可是这天晚上,我正抱肩假寐,昏昏欲睡时,有人一把使劲摇醒了我。
我睁着惺忪睡眼,却还是脱口而出。
「严将军又有什么事」
严和不会是发现我的身份了吧,三天两头就来向我打听,我扯东扯西,到最后,漏洞百出。
「赵姑娘,是我,韩木」
焦急的声音让我清醒了过来。
韩木?
严和自己套不出我话,让韩木来?
好你个严和!
「赵故娘,严和发高烧了,我们都不知怎么办,你是个女子,去看看严和吧」
什么?我一骨碌坐起。
忙不分说跑了过去。
明明中午还生龙活虎,我吃着大饼,不识货得在我面前绕来绕去,问我家中可有父母什么的。
我光想着编谎话,一个大饼吃得味都没尝出来,现在回过神还饿呢。
现在一群男子围着,中间眼紧闭,额间细汗,嘴唇发白的,也是严和?
「赵姑娘,严和他受了剑伤,入了心肺,荒郊野外也没个大夫」
一群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
其中一个使劲拍了拍严和惨白的脸,大叫着「严大哥,严和,你别死了吧!」
七嘴八舌,「好不容易快出去了,你怎么就快死了呢」
从看到严和不省人事围在人群里第一眼心底不知名的害怕,到现在这群糙汉子摇胳膊得摇胳膊,抹鼻涕的抹鼻涕。
到最后,拽着严和干净的手。
我额间不禁突突地跳。
虽然但是,他的胸膛起伏,眉间微皱,明显没他们口中那般严重。
咳咳,我清了清嗓子「他只是疼晕过去了」
哪知这些兄弟给我一个白眼。
异口同声「赵姑娘,疼也会疼死人的」
我僵在原地,这齐刷刷的一声,真整齐啊。
严和胸间好像有血迹,我上前一步,看清后。
装作平静地戳了戳他的胸肌。
还挺弹劲,手感极好。
「他渗血了,需要包扎一下」
围在严和旁边的兄弟们一瞬间全散开了。
异口同声「我们知道啊」
知道?那你们不给他包扎抱着鬼哭狼嚎。
「刘姑娘,你是女子,您给严和包扎吧」
去你的!
我的嘴已经先一步「不不,我虽是女子,整日在家割草喂猪,力气太大,弄伤了严将军怎么办」
我倒无所谓,关键我怕严和日后拿着大刀砍我。
这些兄弟一个个眼巴巴瞅着我,哀怨的小眼神。
极其酥得喊了一句「刘姑娘」
一股恐怖的电流席卷我的全身,感觉头皮发麻得厉害。
「刘姑娘」又喊了我一声。
我差点翻白眼当场去世。
不是说从军的男子一个个冷若冰霜,不解风情,说话都是唬人,可这些男子,怎么还会撒娇?
咵,严和咳了一声。
这群男子齐刷刷看向我,小嘴扁起,恍若我是个负心人。
我这个小姑娘拗不过他们这群人,只能认栽。
在严和面前蹲下,其他男子也与我一起蹲着。
面面相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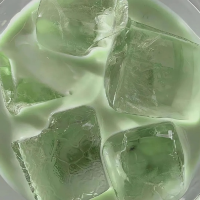
好事多磨呀,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