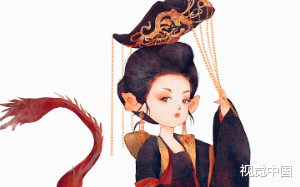我嫁给闻岁晏十年。
第十一年,他不再爱我了。
当初我只是个逃难的孤女,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要娶我为妻,为此被打的下不来床整整半个月。
能动弹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来求娶我,少年将军意气风发,对我许诺。
“阿楹,我会一生一世只对你好。”
可如今他捡回一个女子,任其踩踏我的尊严,还劝我忍让。
“阿楹,卿卿她身世凄苦,你多担待。”
一向乖巧听话的我这次没有退让。
我说:“闻岁晏,我们和离吧。”
我们谁都没松手,可是缘分断了。
1.
我做侯夫人的第十一年,闻岁晏带了一个女子回来。
她叫许卿卿,是闻岁晏在岭南平匪乱时救下的孤女。
起初,闻岁晏只是说她无家可归,让我给她找个院子安置下来。
可是后来,他日日去那院子里送糕点鲜花。
亲自给那院子里的姑娘置办钗环首饰。
府中里里外外都在看我的笑话。
上京城里,流言满天飞。
所有人都在传,说闻岁晏要纳妾了。
作为候府的主母,我不能坐视不管这些流言。
可我刚处理掉几个碎嘴的丫鬟,闻岁晏就带着许卿卿来找我了。
“阿楹,我想娶卿卿。”
他的语气坚定,眼底眸光流转。
我定睛看着面前的人,虽然不再是少年郎,但仍旧意气风发。
这十年好像并没有改变他太多。
“阿晏”,他身后的女子轻轻拽了拽他的手臂。
我才回过神来,往后撇了一眼。
还没看清什么,便被他侧身挡住了。
“好,选个吉日,纳了她吧。”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了,他愣了愣,然后松了一口气。
唇角微扬,笑道:“阿楹,以后我不在府里,也有卿卿可以陪你说话了。”
看着他的笑,我忽的想起他一瘸一拐拿着聘书来向先生求娶我的样子。
先生松口同意时,他也是这般扬起唇角。
2.
我一直以为,我会和闻岁晏永远相爱。
成婚十年,我陪着他从少年小将军到位高权重的侯爷。
无数个日夜里,他牵着我的手情深义重的对我说:“阿楹,幸好有你。”
直到这一刻,他牵着别人的手站在我面前。
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不顾侯府的名声,他说他要为许卿卿办一场喜宴。
“阿楹,卿卿她身世凄惨,双亲都在匪乱中故去了。”
“她说她爹娘生前遗愿就是期待着能看见她穿上嫁衣嫁人的样子。”
闻岁晏神色复杂,又带点祈求的看着我。
那双乌黑的眼眸里藏着让我看不懂的情切。
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少年,好像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压住心头涌起的酸意,扯出一抹笑。
“好。”
我挑了个好日子,顺着闻岁晏的意思请了两桌宾客。
敬茶的时候,闻岁晏就和我坐在一起。
滚烫的茶水打翻的那一刻,他立马站起来护住了许卿卿。
留下我怔愣在椅子上,手烫的红肿也忘了惊呼。
“嫂子!”
“候夫人!”
直到众人的惊呼传进我的耳中,我才回过神来。
“阿楹,你没事吧?”
闻岁晏也回过头来看我的手,眉头皱的紧紧的。
“都是卿卿不好,是我手笨,打翻了茶杯,烫伤了姐姐。”许卿卿赶忙开口。
“没事,别怕别怕。”闻岁晏轻声安抚着怀中的人。
又吩咐道:“春茶,快去给夫人取些冰来敷一下,再去拿药膏来。”
手上的灼热感仍在,但我似乎感受不到疼痛了。
眼前如胶似漆的两个人,刺的我的眼睛好痛,牵动了我的心,也好痛好痛。
我借口受伤离场,留闻岁晏这个新郎官和许卿卿这个新娘子在前面。
踏出前厅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几乎要栽在地上。
胸口猛地一窒,口中涌出一股甜腻的血腥气。
3.
我快要死了。
可是闻岁晏不知道。
他还在牵着别人的手同别人拜堂。
其实许卿卿来的正是时候,这样以后我不在了他也不会孤单了。
“夫人,我去请杨大夫来吧,您都吐血了!”春茶的眼眶红红的,含着泪说道。
我捂着帕子咳了两声,张口拦住她。
“今日府里办喜事要紧,不许去,不要让我的事打扰到他。”
“夫人,要是侯爷知道…”
我打断她:“好了,去替我煎药来。”
春茶转身去煎药后,我垂眸看着帕子上鲜红的血迹。
一朵朵,像绽开的红梅。
还记得,我们刚成婚的时候是冬天。
闻岁晏喜欢牵着我去国安寺看红梅,在梅林里折下一朵簪在我鬓间。
然后亮着眼睛,张嘴就夸我。
“我家阿楹,人比花娇。”
不知道以后,他是不是也会这样簪花在许卿卿的鬓间,是不是也会夸她人比花娇。
或许连闻岁晏自己也没有发现,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带我去看过梅林的梅花了。
也好久好久没有夸过我了。
人说色衰爱弛,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早就不复当年了,我不再是十四岁那个脾气坚硬心底柔软的孤女了。
我的心上人,也不再是那个年轻莽撞但勇敢无畏的少年将军了。
我们安安稳稳的爱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相爱了。
春茶端进来的药碗就放在我身边,直到凉了我才一饮而尽。
外面的喧闹声,直到天色渐暗才停。
我就坐着,怔怔的看着窗外暗下来。
4.
这场婚宴办完。
果不其然,我沦为了全上京的笑柄。
人人都在谈论着,镇北侯从岭南带回来的那个孤女。
说镇北侯对这名孤女格外宠爱,破例为她一个妾室办宴席,还准她穿嫁衣。
说着说着,话题总是会绕回到我身上。
说当年镇北侯也是从南边把我一个孤女带回来,不顾老侯爷的反对,硬要娶我为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些话传的满天飞的时候,众人也不禁开始留意起我和许卿卿身上的相似之处。
我早从第一眼就发现了,许卿卿有几分像我。
只是我被闻岁晏带回来的时候,浑身是刺,不似她那般柔弱温顺。
我那时候和他吵架抬杠了一路,看他说不过我又不舍得骂我我就开心。
那时候我才十四岁,一场暴乱让我失去了双亲家人。
除了恐惧和慌乱以外,就是强装出来的镇定。
闻岁晏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像个话本里的英雄一样,拎着一杆长枪策马而来。
但凡他晚到一刻,我或许就会像爹娘一样,死在那场暴乱里。
我现在都还记得,他的长枪挑开那把劈向我的尖刀,兵刃相接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把我一把拽到马上,护着我从人堆里逃出去。
就算是这样,起初我对他还是防备。
我竖起全身的刺保护自己,只有不畏惧被我刺伤的人,才能拥抱我的柔软。
可嫁给闻岁晏的这十年,磨平了我身上所有的刺。
硬生生把我从一个不服管教的活泼姑娘,变成了高门大院的贤淑主母。
5.
许卿卿来给我请安的时候,我刚喝完药。
这几日我的精神愈发不济,不喝药甚至起不来身。
我明白,或许是真的大限将至了。
“卿卿见过姐姐,给姐姐请安。茶就不奉了,免得又烫到姐姐。”
我不是傻子,自然能听得出来这话里明晃晃的挑衅。
可是我实在没力气多说什么。
我又能说什么呢。
“没事,坐吧。”
我摇摇头,示意她坐下。
“旁人都说姐姐和我相像,如今一看姐姐确实是有几分像我呢。”
清脆悦耳的声音落在我耳朵里,却像针扎。
“你想说什么。”
她的神情有一瞬间的僵硬,又马上恢复正常。
“阿晏说,我和他当初捡到姐姐时很像。”
我陡然一愣。
哪里像了,分明很不一样。
我哪有她这样,说话的时候茶味都快盖过我杯里的龙井了。
闻岁晏果然是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使了。
算了,他喜欢就好了。
左右,我也陪不了他多久了。
嘴里的血腥味愈发浓重,我摆摆手让许卿卿回去。
可是她完全不领会我的意思,还要留下来惹我生气。
“我瞧着姐姐的那件红狐披风可真漂亮,我可以瞧瞧吗。”
话虽这么问着,但她径自走过去就摸上了我的披风。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披风。
是闻岁晏前年猎给我的,做了披风哄我开心用的。
那个时候,我刚失去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
他安慰我,说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孩子。
许卿卿的手用力一拽,红狐披风就落在地上。
我撑起精神走过去,捡起披风死死抱在怀里。
“滚,你给我滚出去!”
刚吼完一句,就被匆匆赶来的闻岁晏听了个正着。
“卿卿,怎么了?”
他着急忙慌的进来,把许卿卿拉进怀里四处查看。
“没事阿晏,就是我不小心弄掉了姐姐的红狐披风,姐姐生气了。”
许卿卿委屈的撇了撇嘴,眼里闪着泪光。
“不就是件披风吗,阿楹你有那么多披风,做什么为了个披风和卿卿计较。”
他眉心微皱,面上闪过一丝失望。
我想告诉他,这不仅仅是一件披风,这是他亲自为我猎的,那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刚没了,这是我的念想。
但这一刻,我连多说几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头晕目眩的感觉袭来,我强撑着装作正常。
“我累了,你们都出去吧。”
“阿楹”,闻岁晏喊住我,似乎还想要对我说教。
我打断他,“我说我累了,你们出去。”
想到了许卿卿,我又加了一句。
“以后没事不用来给我请安了,我身体不好,禁不起气。”
闻岁晏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牵着许卿卿走了。
6.
我倒在榻上睡了沉沉的一觉。
直到天黑透了才醒。
我梦见父亲和母亲了,梦见幼时父亲手把手教我读书写字,梦见儿时母亲替我梳头。
我本来也是有爹娘疼爱,有兄长娇宠的小姑娘。
只是后来,我什么也没了。
闻岁晏曾对我说:“阿楹,你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保护你。”
可现下,他却陪着另外一个女人欺负我。
闻岁晏送了许卿卿一件红狐披风。
许卿卿穿着那件披风来了我的院子,刺眼的红。
刺的我有些睁不开眼。
“姐姐,那日是我的错,惹了姐姐生气。”
“我给姐姐道歉,对不起。”
许卿卿垂着眸,像是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
闻岁晏在一旁帮腔,“阿楹,卿卿不是有意的,你不该因为一件披风就这样欺负她。”
“他只是看那件披风漂亮,她从没见过红狐披风。”
“温楹,卿卿身世凄惨,父母都死在了匪乱中,你该对她好些。”
轻飘飘的话语落在我的耳边却宛如当头棒喝,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还夹杂着委屈和愤怒。
他说我该对许卿卿好些,我该......
“闻岁晏,我父母也死了,早死了,死在暴乱里。”
我冷冷的出口,打断他的话。
他愣了愣,“阿楹,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心疼她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就要我让着她吗,要把所有的好都捧给她吗?”
“可我也十四岁就失去双亲,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女,我在这个世上也早就没有亲人。”
“还有,那红狐披风你要就拿去吧,左右那也是你猎来送我的。”
我拿来红狐披风塞在闻岁晏怀里,将他和许卿卿往屋外赶。
我把门一关,无力的滑坐在地。
脸颊上有什么东西冰凉凉的,许是我的眼泪。
闻岁晏,那不仅是一件披风,那是你对我的爱,是我珍之重之,这世上唯一属于我的东西。
如今,披风我不要了,爱也还给你吧。
7.
再醒来时,已近黄昏。
最近我越来越嗜睡了,醒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每次和许卿卿打完交道,都要沉沉的睡上半天才能缓过神来。
春茶偷偷请了杨大夫来替我看诊,此刻正在屋中,只是面色沉重。
见我醒来,低声开口,“夫人的病,老夫说了若是按时服药,不动怒不多忧思,还可多活些时日,只是如今,夫人忧思过重郁结于心,老夫也无能为力了。”
“夫人”,春茶忍不住垂眸掩泣。
我攥着被角,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我问他:“我还能活多久。”
他摇着头,神色黯然,夹杂着惋惜。
“至多两三个月,少则月余。”
此时就算我再想镇定,也忍不住替自己难过起来。
我颤着声开口,“杨大夫,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算我一个将死之人求您帮我一回。”
我才二十四岁,却死期将至。
不过也没事,左右这世上,已经没什么值得我留下的了。
原来也只有一个闻岁晏,如今他另有所爱,倒也不必我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