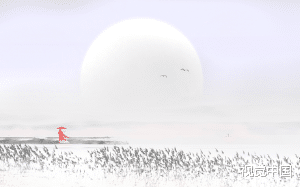我是真千金,也是女仵作。
好不容易被接回家,却被假千金带人羞辱。
亲生爹娘不仅不帮我,还嫌我丢人训斥我。
他们本以为,会看到我委曲求全自卑不已的模样。
可我却没有,反而勾起嘴角,「先别吵这些没用的,你们都没看到吗?」
「这湖中心,飘着个死人啊。」
01
我叫向舒,是被刁奴替换的真千金。
此刻爹娘正把我丢在一旁,带假千金向娩与人攀谈。
「娩儿和向舒都是我们的亲女儿,但向舒身子不好,只能养在乡下。」
爹娘笑容慈爱,故作亲昵地指我,「这不,她病刚好我们就把她接回来了。」
撒谎。
我根本没病,向娩也不是他们亲女儿。
而是那刁奴的。
她娘想将我暴尸荒野,她霸占我十几年人生,如今我被找回来,却要叫她一声姐姐。
即使我心底无怨,也觉荒唐可笑。
「阿舒,阿舒。」温和女声响起,我缓缓抬眸。
发现是向娩在远处唤我。
她亭亭玉立笑容璀璨,对身旁几个女子说了几句。
随即她们便嫌恶惊呼,「什么?向舒在乡下当过仵作?!」
「太晦气了吧!!」

02
没错,被找回来前,我是个仵作。
呼声一落,所有宾客都静默了。
探究和嫌恶的目光,在我和爹娘身上不断徘徊。
我爹黑了脸:「娩儿,怎么回事!」
宴席开始前,他分明再三强调,绝不能透露我当过仵作之事。
向娩满眼愧疚:「爹,妹妹未答应您的要求,我便想先打个招呼,却没想到....」
她嘴唇泛白,忽然向我垂头:「妹妹别怪她们,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一副卑微可怜的模样。
瞬间激起她姐妹们的怒火。
「仵作本就晦气,娩姐姐也是好心,何错之有?」
「就是,让娩姐姐低头,向舒你哪来的脸啊!」
其他宾客观察着这边动静,更议论纷纷。
即使他们第一次见我,即使我从未开口,但大多在骂我果然低贱卑劣。
这一切只因为,他们知道了我是个仵作。
不论行径如何,人品如何,
仵作生来就是低贱卑劣的。
好好的宴席被闹成这样,爹娘脸色愈发阴沉,眼看也要开口吼我。
「先别吵这些没用的,你们都没看见吗?」
我没理他们,只忽地指向湖面:「这湖中心,飘着个死人啊。」
03
这话实在惊悚。
霎时所有人闭了嘴,朝我指的方向看。
湖面平淡无波,可湖心隐隐能见黑发漂浮,黑发下是青白肿胀的皮肤。
还真有具女尸。
「啊!!」
不知谁尖叫出声,划破此刻死寂。
女客们再顾不上骂我了,纷纷拉着旁人往后缩。
向娩倒没失态,但脸色异常惨白。
爹隐晦瞥她一眼,竟高喊道:「事发突然,还请各位先回....」
「不可!」
被我打断,「验明死者死因前,所有人都有嫌疑,怎能遣散?应当立即报官才是。」
说罢,我转向愣神的下人:「可否劳烦你们,用木舟把尸体捞上来?」
当仵作多年,我自然知晓发现死人该是什么章程。
身为大户人家的家主,爹娘也该知晓的。
「报官捞尸,向舒你想干什么!」
可娘却气愤又略带焦急地制止,「你还嫌害得向家不够丢人吗?!」
我没回话,只深深扫她一眼。
再正常不过的事,怎么会丢人?
除非....
脑中灵光一现,我眼眸微凛,干脆自己站上木舟。
「向舒!!」
爹厉声咆哮,眼底怒意几乎要把我洞穿。
但看我始终没放下撑杆的手,他死死咬牙,还是招呼了下人。
女尸总算被捞上岸。
「呀!」
刚把女尸翻面,便有丫鬟惊呼:「这,这不是大小姐院里的翠竹吗?!」
04
不出意料,死者是向娩的丫鬟。
我挑眉,看向那一直『温婉和善』的女子。
众宾客也朝她看去。
只见她面色僵硬,捏着裙角的指尖泛白。
可下一瞬,她又似才缓过神,不可置信跌进娘的怀中:「怎么会,怎么会是翠竹?」
「分明两日前,那丫头才跟我告了假....难道她在回屋路上不慎落了水?!」
说着,向娩悲痛落下泪来:「都怪我,若我差人送她,或许她就不会死了!」
「娩儿,这哪能怪你,不过是命运无常。」
娘立即心疼地搂住她,又狠狠瞪我:「向舒,现在你满意了吧!」
「翠竹落水已是惨剧,你强行捞尸想构陷娩儿也就罢了,竟还让这么多人亵渎翠竹尸首,你居心何在?!」
「我向府行善多年,怎会有你这般恶毒的女儿啊!」
向府的女人都是哭丧的好手。
娘吼完也红了眼眶,与向娩依偎在一起啜泣,场面好不可怜。
瞬间我便成了罪大恶极之人。
宾客们对向娩的狐疑彻底消失,更无人提起报官了,只争先恐后地将「不孝」、「阴毒」等罪名扣到我头上。
亲娘为替养女开脱,竟不惜把女儿污蔑至此境地。
失望吗?倒也没有。
只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果然她不在意我这亲生骨肉,也果然,向娩真有问题。
毕竟,
「可翠竹根本不是落水死的。」
终于查清翠竹尸首,我淡漠开口:「她分明是被人勒死,再抛入水中的啊。」
溺亡与窒息死亡后再落水,尸体外表便有差别。
若是溺亡,手缝和指甲会因挣扎夹有泥沙,翠竹却没有。
不止如此,她脖子和腹部更有极深的勒痕。
显然凶手是用麻绳勒死她,又在她腹部绑了石子,将她沉湖。
这么大动静,这么明显的证据,身为主子的向娩却只说是意外,真有人信?
「正是因为大多人听风便是雨,世间才需要仵作。」
扫了眼面色难看的众人,我又郑重看向娘,「还有,捞尸不是亵渎。」
「像你们这般想任由尸首泡在湖中,三言两语便想掩盖其死因的,才是真正的亵渎!」
「还请向大小姐说清楚,翠竹的死,与你究竟有何关联!」
话音落下,万籁俱寂。
所有人都僵硬杵在原地,连向娩都不再啜泣了。
只面色难看地咬唇,似乎还想反驳。
但就在这时,角落又冲出一丫鬟,指着她撕心裂肺道:「奴愿替二小姐作证,向娩在撒谎!」
「翠竹就是她杀的!!」

05
这倒在意料之外。
我还未反应,那丫鬟又扑通跪下,「二小姐,奴婢名唤紫竹,与翠竹是好友。」
「据奴所知翠竹没有告假,只在干活时不慎洒了几滴水到向娩鞋面,之后便再无踪迹!」
她边喊边磕头:「奴还特意问过向娩,她当时分明说,翠竹因手脚不利索被赶出府了!」
「贱婢!你敢非议小姐?!」
向娩的贴身丫鬟瞬间暴怒,举起巴掌冲来。
我上前一步拦下,冷眼看着向娩。
方才我没轻举妄动,只用言语反驳,便是因为没有此事与她相关的实证。
如今人证已然出现,我也该行动了。
「既然你们都不肯迈步,那便由我和紫竹去报官!」
将紫竹扶起,我领着她便往府门走去。
没走几步,身后传来又爹咬牙切齿的声音:「向舒,你真要搅得向家丢尽颜面?你要知道,向府是皇城的名门贵族,」
「而那翠竹,不过是个丫鬟而已!」
...这是什么话?
我脚步停顿,抬眸扫向所有人。
包括宾客,也包括向府的下人们。
可与我对视的瞬间,他们竟全都避开视线,有的还直接垂下了头。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我就说出了人命,怎无一人支持报官,原来是要维系向府的颜面,
原来因为翠竹不过是个丫鬟。
可丫鬟又怎么了,丫鬟那也是条人命啊!
难道丫鬟的命便不是人命,丫鬟的命便不比那脸皮重要吗?!
心中愤恨无比,我握紧紫竹的手,再度向前,「本朝律法规定,杀人就该偿命,不论身份如何她都不该死得不明不白!」
「这么正义凛然啊,」
许久没说话的娘,却骤然嗤笑出声,「紫竹,你说你爹娘,会不会骄傲有你这么个好女儿?」
坏了!
感受身旁女子瞬间僵硬的身体,我眉头一跳。
侧眸去看,她果然已泪流满面。
「我,我,」紫竹剧烈颤抖着,拳头紧攥。
但片刻后,她还是无力松手,任由血丝滴落:「对不起二小姐,我方才只是胡言乱语...」
「向...大小姐她,清清白白。」
说完,紫竹深深闭眼。
仿佛被剥去所有生机。
06
最后爹娘如我所愿报了官。
官兵来了,却没搜查。
只跟爹娘寒暄几句,便带走了他们交出的『凶手』。
翠竹父母上门替翠竹收尸,我去劝他们继续追查。
「死便死了,有什么好查的,小姐莫不是想收回这百两补偿?!」
可他们只惊叫着把银子往怀里塞,再没回头。
来皇城前,教我仵作本事的王爹爹还有一口气。
他干枯的手握着我的,嘴里不停嘟囔:「皇城是会吃人的,阿舒要小心,要小心。」
当时我还不知这是何意,现在知道了。
杀人不用偿命,皇城当真会吃人。
当真恶心。
事情尘埃落定,爹娘让受惊的向娩好好休息,把我带到祠堂。
「跪下!」
刚进门,娘便一脚踹在我腿窝处,逼我跪倒。
爹则冷脸拿出长鞭:「贱民养大的孩子果真粗鄙!向舒,老子今日就教教你何为规矩!」
说完他便猛地挥鞭。
满是倒刺的鞭子打在我身上,勾烂皮肉,瞬间有血液渗出。
疼得我几乎痉挛。
在回到向府的第五日,我挨了打。
可从前在王爹爹身边,哪怕我险些点着屋子,他也没打过我。
王爹爹....
想着那老头笑呵呵的面庞,我眼中逐渐泛起泪花。
但现在,我的亲爹亲娘还举着鞭子,马上就要再次挥下。
「我没错,错的是杀人凶手向娩,是你们!」
我再不忍耐,爬起身,趁他们未反应全力撞去。
「啊!」爹被撞倒跌坐凳上。
我趁机夺过鞭子,紧紧握在手中。
「老爷!你没事吧?」娘立马扑向爹。
发现他未受伤,又火冒三丈吼我:「贱蹄子,你还敢诬陷娩儿?你爹打你是让你长记性,你怎敢反抗?!」
所以就要我乖乖站着,挨不明不白的打?
我又没做错,凭什么!
「当初我跟你们走,只为遵循王爹爹的遗愿。」
我深吸气,骤然一笑:「如今正好,我便明摆告诉你们,这向府二小姐我根本不想当!」
「现在我便离开,最好老死不相往来!」
07
被向家夫妻找到的前十几年,我一直跟着仵作王全,也就是王爹爹生活。
直到这二人突然出现,说我是他们的孩子,一定要带我走。
与此同时,身子硬朗的王爹爹突然患病日渐消瘦。
谁都看得出他快死了。
「阿舒,跟他们去皇城吧。」
正巧是我生辰,小老头没像以往一样,给我做卧了两个蛋的长寿面。
只躺在床上,呢喃都无比艰难:「做小姐也好,做你想做的也好,这小地方容不下女仵作。」
「走了,就再别回来了。」
话落他便闭上眼,再没睁开。
我再吃不到他做的长寿面了。
用当仵作攒的银钱,我安葬了小老头,按他遗愿跟向家夫妻来到皇城。
最开始,我对这二人有过期待。
「你以后便是向府二小姐,绝不能沾染那仵作的晦气!」
可进向府第一天,他们就扒了我的衣裳,抢走王爹爹给我的布包,全扔进火堆。
做完这些,还将向娩带到我面前:「这是你亲姐姐,好好跟她学规矩,别把穷酸相带到向府来!」
他们趾高气昂,毫不掩盖对我和王爹爹的鄙夷。
可身为我亲爹娘,他们却满不在乎,若不是王爹爹和那仵作手艺,我早被向娩她娘害死了。
其实我也有疑虑,不明白他们为何非要带我回来,又如此对我。
但从那之后,这疑虑便不重要了。
我下定决心要走,只是现在才找到机会。
收拾好包袱,我正准备离开。
便见向娩的丫鬟在门外冷嘲热讽:「向仵作,老爷说了你想走可以,但向府之物一样不准拿!」
「女子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只怕活下去都难,我劝你啊,还是去跟大小姐磕头认错吧!」
狗仗人势的东西。
我只当没听见,越过她继续往前。
「站住!」
她气急追来,「说了不准拿向家的东西,你这仵作耳聋吗?你们几个,给我搜!」
随着号令,有人上前制住我,有人抢走我的包袱。
布包被摊开,所有东西砸落在地。
只有仵作用的工具,和几件麻布衣,都是我拿安葬王爹爹剩下的银钱买的。
与向家无关。
丫鬟们似没想到我什么都没拿,面面相觑。
我顺势挣开桎梏,收拾好包袱再度前行。
「死仵作,真晦气!」
身后传来大声唾骂。
我没反驳,也没回头。
跟王爹爹当仵作十几年,这点羞辱我早已习惯,算不上什么。
与其跟她们纠缠,我还不如想想,身无分文的我该何去何从。
思绪紊乱,不知不觉穿过几条街,走到一扇门前。
抬头看去,只见门上刻着三个大字:
大理寺。
08
我抿了抿唇,敲响大理寺的门。
竟真有人推门而出。
「向姑娘,大人候您多时了。」
差吏领我进了大理寺,又走进屋子,屋内满是书架没有其余装饰,只一张桌案摆在中央。
而桌案前,有一青衫男子正端坐书写着什么。
「民女见过任大人。」我规矩朝男子行礼。
我认识他,他是大理寺右少卿,任政。
可听我拜见,任政并未抬头,连笔都未曾放下。
只不冷不淡说了句:「既知晓我身份,又为我策划了这场好戏,姑娘所求不妨直说。」
瞬间,我背上浸出一层薄汗。
原来他都猜到了。
猜到我想利用他。
强忍心中惊惧,我立即跪答:「我想当大理寺仵作,任何考察我都接受!」
早在被向家夫妻找到前,我便有了此生目标。
我想当大理寺的仵作。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所有人,哪怕同样地位不高的下人,提起仵作的第一反应都是低贱晦气。
与死人接触又如何,谁到最后不是死人?
而且仵作接触死人,是替他们传达意志平复冤屈,说来也算高尚。
凭什么就得看人白眼受人欺凌?!
在仵作中,大理寺仵作地位最高。
若我能担任,或许就能改变现状,让所有仵作挺起胸膛!
那时王爹爹还活着。
得知我有此夙愿,他眼眶通红,特意给我看了任政的画像。
他说任少卿是惜才之人,大抵不介意男女,是我进大理寺的唯一途径。
而昨日那场宴会,好巧不巧任政也在席。
是以我拼命违抗向家夫妻,执意捞尸,除去想还翠竹一个公道,
也因为我得让任政看到,我真有本事!
话音落下,任政放下笔,认认真真打量我。
许久许久,他终于露出第一个笑,如春风拂过冰川,万物得以生长。
「向舒向姑娘,不错。」
他将桌角的纸递给我,上面写着一处地址,「湖中女尸死因简单,我不敢替你担保。」
「你若回不去向家,便到此处暂且住下,之后有案情再来一试。」
那纸上墨渍已经干涩,看样子是早写好了。
他甚至猜到我无处可去,替我安排了住所。
王爹爹说得对,任政是好人。
聪明的好人。
我也扬起笑,正打算谢他。
方才领我进门的差吏却突然闯入,「任大人,出事了!」
「有人在碧泉别院,发现了一具女尸!」
09
机会竟来得这样突然。
我与任政对视一眼,立即赶往碧泉别院。
「我们今日是来游园的,谁料竟发现了....」
别院内,几个公子聚在一起,面色都有些苍白。
任政拍他们的肩以示安抚,才走到我身旁:「看出什么了?」
他问话的同时,我已初步观察了尸首。
发现女尸之地是别院最幽深的园林,女尸还蜷缩状夹在假山缝隙间。
若不是尸臭飘散称得上隐蔽。
且她头脸满是青紫色瘢痕,树状血脉在皮肤下清晰可见。
「死了有些时日了。」
回过任政的话,我又去翻女尸衣物。
不出所料,鞋底并无遍布四周的青苔,衣衫上除了与假山接触之处也无脏污,只胸口有一处刀伤。
我道:「她应该是在别处被人捅穿心脉杀死后,才抱到此处藏匿的。」
「也就是说,凶手是对别院有些了解的男人?」任政挑眉。
男人才有力气做这些事。
但也说不准,还得再验验才行。
将女尸从假山中挪出,我和任政正准备前往义庄。
却忽见一高大的玄衣男子,领着白裙女子疾步走来。
「月儿!真的是月儿!」
看清女尸,女子瞬间哭得梨花带雨,「都怪我!若我能抽空陪她前来,或许她就不会死了!」

10
这熟悉的语气,熟悉的惺惺作态。
不是向大小姐向娩又会是谁。
可她怎么来了,跟死者又是什么关系?
我正疑惑皱眉,便听任政朝玄衣男子询问:「齐少卿,这?」
「此乃向家小姐向娩,死者林月的闺中密友!」
男子不屑冷笑,「她也算事关之人,况且你自己都带了个闲杂人等,还想以此参我一本不成?!」
见到女尸后,任政便查清了她的身份。
是林府庶女林月。
可先前向娩装模作样,给我介绍她姐妹时,根本没提过死者林月。
她跟林月真是闺中密友?
若不是,她来这一趟想做什么?
还有这玄衣男子,原来他便是大理寺另一位少卿,齐安度。
他领向娩前来,看向娩的眼神也无比关切。
难不成他们二人....?
脑中思绪万千,我也没遗落齐安度的话,主动开口:「齐大人,我是仵作。」
并不是他口中的闲杂人等。
「你?仵作?」
「女仵作?」
齐安度却嘲弄扫我,眼神不屑鄙夷:「娩儿,她就是向府养在乡野的粗鄙蠢妇?」
「阿舒...」
向娩恍惚抬眸,一副才注意到我的模样。
随即瞪大眼,跌跌撞撞朝我扑来,「妹妹,原来你在这,我终于找到你了!」
「爹娘按我喜好给你布置卧房是不对,但他们知错了,你就同姐姐回家好不好?」
11
她在说什么,什么卧房?
话口转变太快,我还在不解。
就听向娩朝任政道:「任大人,阿舒说要走时家父也在气头上,这才给您添了麻烦。」
「如今家父已答应给阿舒道歉,您就帮忙劝劝她吧,她离家的几个时辰二老时时垂泪啊。」
快速说完,向娩捂着心口落下泪来。
白裙飘渺身姿如柳,倒真有西子捧心的姿态。
顷刻间所有人都不满瞪我。
齐安度神情也愈发阴沉:「任政,大理寺那么多仵作,你为何偏要带这矫情不孝,只会卖弄的女仵作?」
「这本就不合规矩。若你执意让这女人验尸,别怪我上奏陈大人!」
陈大人便是大理寺卿,大理寺的一把手。
前面的话任政跟没听见似的,可陈大人三字一出,他瞬间眉头锁紧。
他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帮我了。
事已至此,我怎可能还不明白向娩来意?
原来不是为了林月,而是为了我!
她是想引齐安度出手施压,让我失去任政助力,只能老实回向府认错吧!
也是奇了,到底为何?
为何向家人都对我厌恶至极,又好像一定要我待在向府?
心中疑云渐起,但我也知此事可之后再探。
眼下最重要的,是我修习验尸之术多年,好不容易触到大理寺仵作的门槛,
绝不能让向娩几句话便夺走!
「我离开向府不是这般缘由。况且你嘴上说得关切,那齐少卿羞辱我时,你为何一句都不反驳?」
我冷声质问向娩,把她问得面色微僵。
才转身看向齐安度:「齐少卿,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但能否给我一炷香时间?只一炷香我便能验出尸首所有异处,」
「若不能让你满意,不必驱赶我自己走!」
一番豪言壮语,引得旁人纷纷侧目。
那么短时间,资历再深的仵作都不敢担保精确,我这女子竟敢口出狂言。
任政眼底划过欣赏。
齐安度脸色几变,却仍嘲弄耸肩,「有必要吗?」
「我乃大理寺少卿,请离闲杂人等的权力还是有的,用不着那一炷香!」
12
...虽不想承认,但他说的是事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大脑飞快转动,我咬牙思考对策。
「不过,」就在这时,齐安度竟话锋一转,「我也不是不能给你机会。」
「一炷香时间,若我不满意你不止要走,更要为先前宴会之事跟娩儿磕头道歉!」
搞了半天,他打的竟是这般主意。
我甚至安了心,毫不犹豫应下:「没问题。」
这可是我盼了多年的,进大理寺当仵作的机会。
别说我不会输,哪怕他要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不犹豫!
拿起所需的工具,我走到女尸身边,立即有差吏掏出香准备点燃。
「等等。」
我却开口打断,「齐大人放心,我不是想临阵脱逃,只是您提了要求,我也可以加码吧?」
「哦?」齐安度眯眼,「说。」
我深吸口气,「没磕头那么过分,只要向娩承认方才在污蔑我,并为之道歉。」
「还有您,也要为瞧不起女仵作道歉。」
齐安度从头到尾,是没说过侮辱女仵作的话。
但我听得出他那一句又一句「女仵作」下暗含的恶意。
他就是瞧不起我,更瞧不起女仵作。
那我偏要让他被女仵作打得心服口服!
待齐安度也毫不犹豫,仿佛我输定了般应下要求后,我便开始了验尸。
首先是胸口刀伤。
「奇怪,」我对任政道,「刀虽扎得深,但周围的肉都被撕裂了。」
以撕裂形状看,这刀分明是被扭送进女尸胸腔的。
人被刀捅会痛,自然会反抗逃跑。
扭着刀杀人,除非死者被捅时已昏迷,或重伤无力反抗。
但这女尸又无其他伤口。
「是迷药,或者毒!」
13
一炷香时间很快过去。
替女尸穿好衣裳,我不等齐安度问便开口:「她死于刀伤,从五脏六腑看毒性没来得及蔓延。」
所以重点该放在刀伤上。
「从胸腔肋骨划痕看,这刀不止是扭送,更是卡顿着捅进去的,倒不像故意折磨。」
更像凶手也失了力气,只能这样杀害死者。
且刀伤角度也别有洞天,即使伤口撕裂,还是能看出往右偏移。
「很大可能,凶手是个左利手的男子,就住在别院附近。且他杀人时中了迷香,待效果过去才趁夜把死者藏到此处。」
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
在女尸胃部,我发现一些药渣,分明是某种迷香的解药。
这女尸死因还挺复杂,又中毒又被捅又有迷香,背后因由连我都有些好奇了。
但那是之后的事。
「如何?」我边净手边朝齐安度道,「大人可还满意?」
方才他们都看着,就算其他仵作来验,也绝验不出更多东西了。
别说齐安度,向娩的神情都险些没维持住。
「妹妹何必咄咄逼人。」
可她还是落泪呢喃,替齐安度『打抱不平』。
齐安度则把她拉到身后,才梗着脖子回应:「说了半天,仍不知凶手何人,要我如何满意!」
这是想破罐子破摔,直接玩赖了?
若光验尸就能抓出凶手,还要他大理寺少卿何用啊!
我们对峙激烈,差吏们自然议论纷纷。
有人骂齐安度不要脸,也有人帮他说话,一时竟商量不出解法。
「谁说没有结果?」
就在这时,方才不知去向的任政终于出现,还领着一个下人装扮的男子,
「你要的结果,这便来了!」
14
「这是何人?难,难道...」
齐安度看着那男子,脸色愈发难堪。
任政却摇头,「不是凶手,但算个重要人证。」
说罢,他朝男子使了个眼色。
男子立即跪答:「回大人的话,小人是别院的小厮。」
「而这位姑娘说的左利手男子,小人还真知道一个,也是别院的小厮,就住在别院偏房内!」
在小厮的讲述下,左利手男子的形象越发丰满。
他没有名字,别院主人给他赐名良福。
良福是邻城过来做工的,今年十七,长相清俊,受不少丫鬟偏宠。
因此他有些自傲,也常在其他小厮面前炫耀。
直到三个月前,良福突然不收任何丫鬟东西了,问他也不答,只说等他发迹请所有人吃酒。
原本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
谁料又过两月,也就是一个月前,他竟真给了银子让大伙吃酒去。
「有便宜我们自然要占了!那夜别院好多小厮次日才回来,一回来才知道,良福大早便以老母重病为由,向主家请辞回乡了。」
小厮挠挠脑袋,「可我记得清楚,他分明说过自己老母早就离世了啊。」
这么看来,答案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