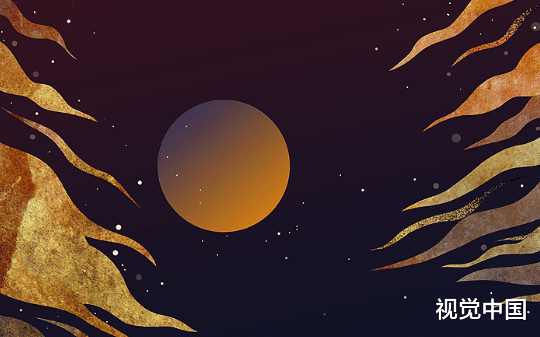“唔,求你,别,别亲,痒……”
盛云珠双手被自己的发带反绑于身后的大树,雪白的足尖在草地上绷紧,呜咽哭泣。
厉飞羽的嘴唇滚烫,在她耳畔辗转轻啄。
盛云珠瞧不见男人的面容,因被腰带蒙住了双眼。
可这个正在肆意调戏她的男人,声音有些耳熟,却不是她夫君。
......
盛云珠的夫君是石府郡富商冯仑嫡出的长子冯天寿。
因出身时就先天不足,冯天寿这才起名天寿。他生母早逝,父亲冯仑后娶的继妻又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便对这长子极为“溺爱”。还未及婚配,就替他养了两个窑姐出身的侍妾,这下愈发掏空了他的身体。
盛云珠嫁过去后,夫君床笫间竟不能人事,大婚夜对她用了工具这才落红过了圆房那关,之后又请大夫偷偷给夫君用了点药,几经磋磨这才能怀上孩子,是万万没有身前欺她的男子这般威猛强悍。
盛云珠自幼便被家中长辈教导,女子无才便是德,出嫁从夫。夫君一年有三百天无法人事,她也只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反正她原也对床底之事不太热衷,嫁人后一直老实本分守在自家院子的一亩三分地,除了夫君几乎没有再见过其他男子。
她儿子才刚半岁,如今还在哺乳期。
今日这般被男人轻薄......自己的身体还不受控制的发抖,嘴里还抑制不住发出奇怪的呻吟,更让她又惊又怕。
盛云珠喘息的厉害,没一会儿蒙眼的腰带就被眼泪浸湿,她一再哭着低声央求着那男人别再轻薄她,放过自己。同时心里又害怕这一幕被带来的丫鬟们撞见,所以不敢太大声。
正因如此,她的求救与求情都无力又软弱,落在男人耳中便成了绵绵情曲。
此时正值盛夏书院休沐期,烈日炎炎,丫鬟们都等在书院外的榕树下,她的呜咽再如何也是传不出书院的围墙,只有池塘的鱼跟天空的鸟儿听见。
身前男人许是不耐烦听她的哭泣,竟将修长的手指探入她唇齿,夹住她柔软的舌尖:“不许哭!”
盛云珠舌头被夹住,这下真的连哭都哭不出,只能用鼻腔哼哼着呜咽。
男人的动作愈发的放肆……
树根下歪着的一个香炉中生出袅袅白烟,一股甜腻的暖香逐渐弥散开将两人身影笼罩。
盛云珠吸入那妖娆香雾,呜咽变了味,雪白肌肤也逐渐泛出桃红。
甜香一缕缕沁入肺腑,她挣扎的力道小了许多,哭声逐渐化作了婉转的娇啼轻吟。
她的腰肢一寸寸软下去,整个人近乎完全瘫软着靠在大树上,萤萤草地也被这暖香熏出的潺潺染污,脏了书院这清净圣所。
盛云珠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只想缅怀下年少时的读书岁月,竟会在进入书院后被人强行掳了,青天白日下就绑在树上。
最想不明白的是,这种情况下自己竟会隐约感到快活。她心中羞愧万分,万一真的被.....事后为了名声,说不得只能去投缳自尽。
此时的盛云珠并不知道,她刚吸入的香雾,是一种夫妻间的意趣香,名唤合心。
最能令人迷醉情动。
盛云珠今日原是跟侍女上街采买布料,果子等物。路过儿时上学的书院,因一时念及过往便进入书院缅怀一下曾经的年少时光,哪曾想书院已经休沐,整个书院半个人都没有。她刚走了几间房便发觉不对,但等她想要离开时,却被人从后打晕,等醒来时已经被绑在书院后花园的大树上,被这不知哪里来的男子轻薄。
绑她的人是厉飞羽的书童,厉飞羽在办案时中了敌人的情毒后躲入书院,若不能解毒,便会爆体而亡。正巧曾与厉飞羽有过婚约且青梅竹马的盛云珠送上门,那书童便不想再浪费时间,直接绑她来替厉飞羽解毒。
书童担忧她不从,便点了香。
果然,合心香熏得盛云珠身子软滩似泥,呜咽中带着隐秘的渴求,声音连盛云珠自己都觉羞耻。
粗粝的树干将盛云珠后背的薄纱披肩撕裂,厉飞羽抬了抬肌肉逑结的胳膊,大掌猛得又掐紧了女人的纤腰。
领口不知何时敞开,衣裳被剥至肩头,当被男人吻至锁骨时,盛云珠一个激灵,惊慌失措的挣扎起来,她不能对不起夫君。
这一番挣的女人香汗淋漓,挣的男人也猝不及防,连蒙眼布也被她蹭掉了。
蒙眼布掉落的瞬间,她终于看清眼前男子的面容。
一道晴天霹雳落在盛云珠头顶,是他,怎么会是他?
眼前的男人生得貌若潘安,剑眉星目,华贵的锦云纱都已脱到腰间,胸膛宽阔,额头勒着一抹镶嵌翠玉的头带,通身气派。
当年自家未曾落魄之时,差点跟侯府联姻,嫁入厉家成为他的妻。
如今,本该在京城当小侯爷的厉飞羽却做着羞辱他人妻子,采花贼的勾当。
盛云珠噙着泪的望向厉飞羽,瞧见他肩头与胸膛多了好几道狰狞旧伤疤,大臂上还多了一个青龙纹身。当年侯府退亲后只听说他自请入军中,从一名行伍小兵做起,近几年竟得了圣眷,扶摇直上。
这少年时比她还要羞怯容易脸红的同窗兼竹马,定是已经混成了传说中的行伍兵痞,就是长得再好,也是匪气难脱,大恶之徒。
盛云珠又惊又怕,慌忙闭上眼睛,假装不认识他:“我什么都没看见。”
她本能的想要继续挣扎,甚至想要将自己的小腿从他胳膊中抽出。
可那香却让她的动作像绣花一样软绵。
大腿颤抖着,膝盖想要捶打他腰际时都使不出气力,反而像是故意磨蹭。
盛云珠又呜咽起来,眉宇间被合心香熏得媚色如春。
“呵!”男人轻笑一声,声音中透着玩味。
在他看来,此刻女人所有的举动,都是.....欲拒还迎。
烈阳高照,女人雪白的肌肤颤颤巍巍,小白兔一样软语哀求,求他放了她,求他不要再进一步了。
可她口中说着不要,长腿却像蔓藤一样攀附,连哭音都像潺潺雨丝般裹着甜腻。
厉飞羽并不知暗卫对盛云珠用了手段,见她一边哭求抗拒,一边却像水蛇一样浪荡。
便觉得曾经差点娶了的女人真能做戏,比起那些欢场女子不遑多让。
男人眉目间满是邪肆痞气,垂头凑近人耳边,嗓音沙哑道:
“珠儿,你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
那些话都被暖风吹进耳朵,灌进盛云珠脑海里。
盛云珠羞愤交加,哭求声也愈发凄楚可怜:“飞羽,我求求你......放了我......求求......你了!”
厉飞羽闻言,眸光暗沉了下去。
他俯首含住了她吵闹的樱唇,狠狠碾磨了下,低笑着道:
“还说什么都没看见?求饶的话都说的这般好听,看来珠儿也是个不老实的。既如此,那本侯就放了你,咱俩好好玩儿。”
言罢,厉飞羽俯身一扯,松了绑缚她双手的发带。
盛云珠双手一得解脱,本能伸手抵着他胸膛要推开他。
厉飞羽眸光骤冷。
他手掌扣住她双腕,按在她头顶,不让她动弹,随即俯身将她身子重新翻转过来,让她抱住大树,双手掐住她的纤腰,竟直接又从后贴了上来吻她的耳垂。
他不顾她的挣扎和反抗,疯狂轻吻着她雪白颈项。
男人灼热滚烫的吻不住炙烤着盛云珠的心,盛云珠的脸颊一下下撞在粗粝的树皮上,她又痛又羞又恼,哭得梨花带雨,泪珠一滴滴滑落。
厉飞羽不为所动,只因他已认定女人在欲拒还迎。
待厉飞羽终于尽兴,他方才停下。
盛云珠瘫软在地,哽咽着说不出话,慢慢爬起身将散乱的衣服好整理好。
她不知该恨这人的不知廉耻,还是恨自己的软弱,亦或者是对他身上的旧伤感到同情。
他们虽从前是两小无猜,可早已退婚,她又已嫁做人妇,竟发生了这种事,实在是荒唐至极。
可她心里却不排斥这种感觉。
这样的感觉,就算是被强迫,也不讨厌。
厉飞羽却还不肯放过她。
他伸出大掌托住她娇软的腰肢,将她的身子扶正坐了起来,低头又亲吻了上去,这一次却不似先前那般粗鲁,而是温柔细致的吻着她唇瓣、额角、脸颊,脖颈......最终落在她白嫩透粉的锁骨上。
他轻咬着她锁骨,含糊不清道:“珠儿,别担心,我会娶你为妻。”
盛云珠心跳骤乱。
她抬起泪汪汪的眼睛,定定的望着他,心头百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