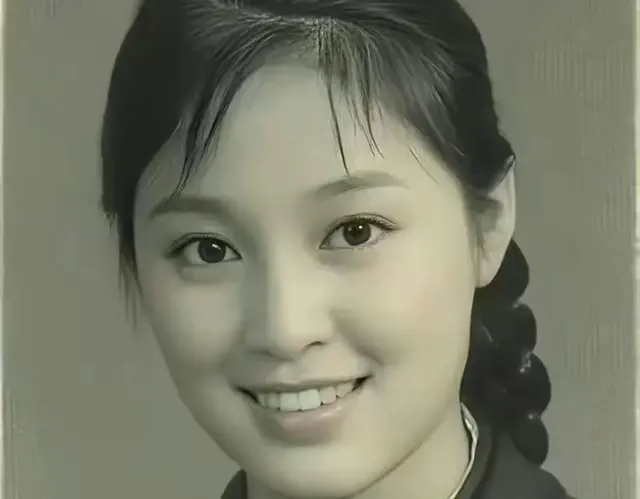1979年11月,因为伤病,我选择了退伍。团里派了政委来县里协调我在地方的工作关系。在民政局军人安置办公室谈完后,政委交接了我的档案,返回了部队。我拎着包裹,往家走去。老乡们见我回来了都跑来嘘寒问暖,有的捏捏我的胳膊,瞅瞅我的腿,看看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是看我有没有负伤。

人群喧闹着,反正我也听不大清,只能附和着回应,有个大娘牵着我的手还哭了起来,这一时搞得我手足无措。人群簇拥着我往家里去,我家门前已是破败不堪,门口的墙都已经变黑了,墙头长着高高的茅草,俺娘拄着拐棍开了门,我看到俺娘花白的头发,佝偻着腰,这才一年没见已经老成了这样,我颤抖着喊了一声:娘!她眯着眼睛看着我,愣了下神。人群中有人喊:婶子,存富回来了!俺娘这才反应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接着双手又在我脸上摸着,喃喃的说:存富回来了,存富回来了。……众人一起往家里涌去,我看到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堂屋里阴冷,光线很暗,屋里一股霉味。墙角还放着接漏水的桶,里面水都快满了。这时有个年轻人说:俺去叫俺叔回来!我问娘,爹去哪里呢?爹和大妹上工挑水利去了,小妹在上学。

众人在我家聊了一会儿,就各自散开了。过了约两个小时,我爹才回来,一进门就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问大妹呢?爹说:在挑水利,提前回来,要扣工分,我提前回来还是公社会计让我先走的呢,家里口粮不够吃,要挣工分粮哩。我们在家聊着,我见俺娘不时的转过身去擦眼泪。到了傍晚时分,大妹和小妹都回来了,大妹赶紧生活做饭,我拿出我在部队驻地给他们买的礼物,我感觉,一家人团聚在昏暗的灯光下吃晚饭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我对爹说:民政局让我等消息,会优先安排,明天我和你一起上工,挑水利挣工分。爹说:不急,明早,你的伤,我先带你去中医那里看看,再上工。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干了三个月,还没等到民政局的通知,我感觉身体有些吃不消了,熬的中药效果并不大,我头痛得越来越厉害。看东西都有重影了,我知道这是颅压高,引发炎症的表现,我拿着部队证明及处方去县医院,找到办公室里闲聊的女医生,说我想注射甘露醇及青霉素,这两种药一个是降颅压,一个是去除炎症的。

可医生告知这是管制药品,要上级批条。我拿着部队证明和处方给她看,她瞟了一眼说:哦,你是伤残军人,但现在这些药品医院都没有,你等几天再来吧,少喝水就好了。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嘲笑和轻蔑,可能笑我是个泥腿子吧?我一步一挨的走出了办公室,发现部队证明忘在她桌上了,又回去取,就见那名医生拿着我的部队证明对其他医生说:哼,哪有那么多伤残军人,这我见得多了,鬼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总有些不法分子打着军人的幌子,从医院骗药去倒卖。她见我又走进来,表情有些不自然,我从她手里拿过部队证明,强忍着泪,走了出去。我在医院门口蹲了一会儿,感觉稍微好点了,想着,我反正已经到县里了,我干脆去民政局那边问问我工作安置的情况。

进了民政局,我说明我的来意,民政局的干部们热情的接待了我,但先前接待我的主任和局长都外出开会了,他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索性我拿出部队证明问他们这个部队证明和处方有没有作用?是不是伪造的?我又把医院的遭遇说给他们听,这时有个姓李的干部,约摸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看了我的部队证明后问:战友,你打过谅山?我惊讶的望着他说:是,我们部队是从谅山到安农走同登进友谊关撤下来的。他眉头紧皱,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说:这还了得!这样下去,将来谁还会保家卫国?!他这一巴掌倒把我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