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感到全身发热,焦躁不安,她心中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匆匆回家后,她听到房内传来响声,赶进屋一看,姚玉兰已泪流满面。 那天午后,天不算热,牌局却越打越心烦,不是输,是莫名地燥。 汗珠蹭着鬓角往下流,心口像被猫挠,爪子一下一下,抓得慌,姚玉兰擦了擦额头,突然停牌,说:“我得回家。” 别人都劝:“手气正好,走啥?” 她站起身:“心跳得慌,眼皮也跳,像出事了。” 没人当回事,她却再没回头,步子急得像逃命。 进家门那一刻,屋里死静,客厅没人,厨房没人,最里面那间门半掩着,缝里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 推门进去时,整个人像被扔进冰窟。 杜维嵩,儿子,躺在床上,嘴唇发紫,身边是空空的药瓶。 人没气了。才29岁,一点招呼都没打。 之前没一点征兆,早上还吃了早饭,说要出门理个发,顺便看看朋友,钱包丢了,心里堵,但也没大吵大闹。 后来才知道,理发店里被人当贼,老板认定他想赖账,几句难听话没完,旁边还有人起哄,“这年头还有这种人?”、“以前的杜家少爷,现在混成这样?” 脸丢尽了,火憋满了,谁也没想到,就为这点破事,他回家吞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不是一天崩溃的,是这些年,一步一步,踩着光环碎下来的。 杜维嵩是杜月笙最小的儿子,老来得子,宝得不行,杜家那么多孩子,这一个最娇,别人偷糖挨打,他偷了给赏;别人摔倒被骂,他摔了还得人抱着哄。 姚玉兰本是京剧名角,嗓子一开台下能哭,可对孩子,从没板起脸。 那个时候,杜家在上海滩是天,杜维嵩穿定制西装,坐私人汽车,出门有随从,讲话带腔,他是少爷,不是普通人,是“杜老板的崽”。 1949年之后,一切崩了。 先是搬去香港,再就是杜月笙投资赔光了,过去的风光变成笑话,剩的那点钱,几个孩子分完就没了。 每人一万美元,听着多,花起来三两下。 杜维嵩最受不了的,就是没人认得他是谁,在上海,别人喊“杜少爷”;在香港,别人看他像个无业游民。 曾试过找工作,可干了几天,跟人吵,辞了;想自己开铺子,没门道、没人脉,赔钱收场。 他不是不能活,是不懂怎么活,身边没有人教过他怎么低头,怎么妥协,只学会了怎么挥霍、怎么有人围着转。 那些年,他试着去适应,但骨子里早就养成了“我是少爷”的习惯。 再后来,杜月笙去世,姚玉兰哭得死去活来,几个兄弟姐妹为遗产吵翻天。 杜维嵩像浮萍,一边是断了线的天,一边是翻船的海。 他不说话,也不抱怨,但情绪一点点积压,酒喝多了,话就多:“我爸当年要还在,我能被人当贼?” 那天晚上他没发火,也没叫人,理完发回到家,跟平常一样,关门、锁门,然后灌下那瓶安眠药。 姚玉兰坐在床边,拍着那早已没了气息的身子,嘴里念着:“我怎么就没早点回来……怎么就没教过他自己活着……” 她不是不爱,是太爱了,爱到没让他长大,爱到把他困死在那句“你是我儿子”里。 那之后,她整个人像被掏空,出门不说话,回家不吃饭,有人劝她去走走,她摇头:“心已经埋了。” 晚年,她靠着宋美龄接济,日子过得并不差,可每回人提起孩子,她眼里就浮出一层雾:“养出一个儿子,不会活,不会死。” 她说:惯子如杀子。这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 死后没留一封信,没一句话,只留一间没拉窗帘的小屋,一地碎掉的生活。 这个结局,不是一天来的,是一场慢性的溺亡,从光里走到黑,一步一个脚印。 不是他脆,是从来没人教他怎么硬气。 姚玉兰后来说,如果能重来一次,她宁愿让儿子受点苦,饿几顿、摔几跤,也不想他像泡在糖罐里,一辈子没活过半天人样的日子。 参考资料: 《杜月笙外传》,张品成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64-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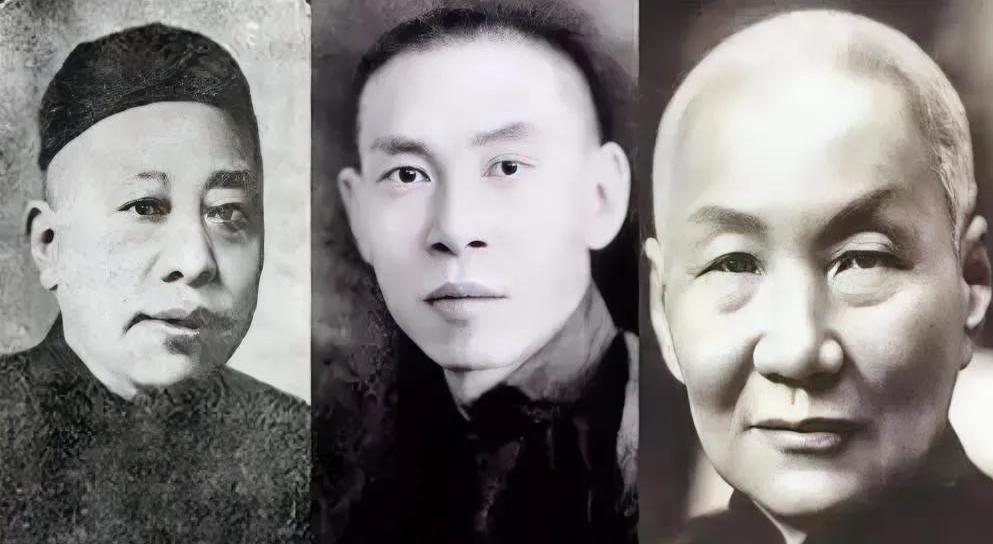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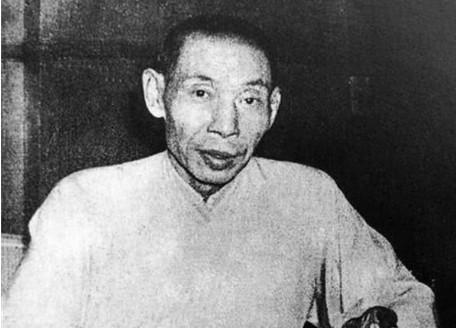







小小
哪怕杀俩日本鬼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