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46岁的林纾刚丧妻不久,青楼头牌谢蝶仙便让人送来四只特大的柿饼,林纾打开一看,只见每个柿饼都被咬过一口,还留着齿痕,带着脂粉香气,林纾看后哈哈大笑,随后让人给谢蝶仙送去几条鱼和一首诗。 林纾这人,提起晚清文坛,谁不得竖个大拇指?1852年,他生在福建闽县,家里穷得叮当响,五岁就没了爹,靠外祖母拉扯大。没钱买书咋办?他小时候蹲在私塾外头偷听,捡别人扔的破书页,借书抄书,硬是靠这股倔劲儿读了两千多卷古籍。 这桩风流公案里的柿饼暗藏玄机。青楼女子的唇印落在柿饼上,分明是带着香艳的邀请——"柿"谐音"事","咬过一口"暗喻肌肤之亲。但林纾的回礼更绝,几条鲜鱼配着诗句"柿叶满庭红颗秋,清霜杀物不言愁。老夫别有伤心泪,洒向鲛绡寄阿侯",愣是把风月场上的试探化成了文人间的高雅唱和。 那年头的文人墨客,哪个没在秦楼楚馆留过几段佳话?可林纾偏要做个异类。谢蝶仙何等人物?福州城里最炙手可热的红姑娘,多少达官显贵捧着真金白银求她抬眼一顾。偏偏这倔书生,对着美人齿痕犹存的柿饼,既不见面红耳赤,也不故作清高,倒像看透风尘似的拍案大笑。 有人嚼舌头说林纾假正经,守着礼教活该当鳏夫。可翻翻他的《春觉斋论文》就知道,这位能把西方小说译得缠绵悱恻的才子,骨子里早把世情看得通透。送鱼之举藏着机锋:鱼水之欢本是露水情缘,倒不如留首酸诗给后人猜谜。这哪是拒绝?分明是给风尘知己留足了体面。 晚清文坛怪现象多得很。康有为能在维新变法时大谈男女平等,转头就纳了六个小妾;辜鸿铭捧着茶壶大讲"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林纾硬是守着寒窑译完184部西洋名著。他给谢蝶仙的诗里那句"清霜杀物不言愁",倒像是给自己写下的判词——任你满城风月,我自冷眼观之。 青楼文化这面照妖镜,照出多少伪君子的丑态。多少道学先生白天骂着"商女不知亡国恨",夜里摸进花街柳巷。林纾这招以诗拒美,看似迂腐,实则藏着大智慧。他太清楚自己若真赴了这场风月局,明日街头巷尾的谈资就会从"译界鬼才"变成"狎妓老手"。 谢蝶仙终究没等到才子赴约,倒是这段轶事在福州城传了三十里。有人说那首回诗里藏着"鲛绡"典故,分明是拿曹植《洛神赋》打哑谜;也有人发现送去的鱼是四鳃鲈,暗合"四柿"之数。文人骚客的游戏,玩到最后连当事人都成了戏中人。 看客们总爱追问:林纾当真不动心?他晚年给弟子讲学时漏过口风:"美人恩重最难消,不如留个清白身。"这话说得轻巧,可翻他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字字血泪哪里像没动过情?无非是看破红粉骷髅,宁可在笔墨间造个干净世界。 如今再看那四个带齿痕的柿饼,倒成了晚清文坛最妙的隐喻。新旧思潮碰撞的年代,礼教枷锁与人性欲望撕扯得火星四溅。林纾这场无声的风月对决,既守住了士大夫的体面,又给青楼女子留了三分尊严,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强出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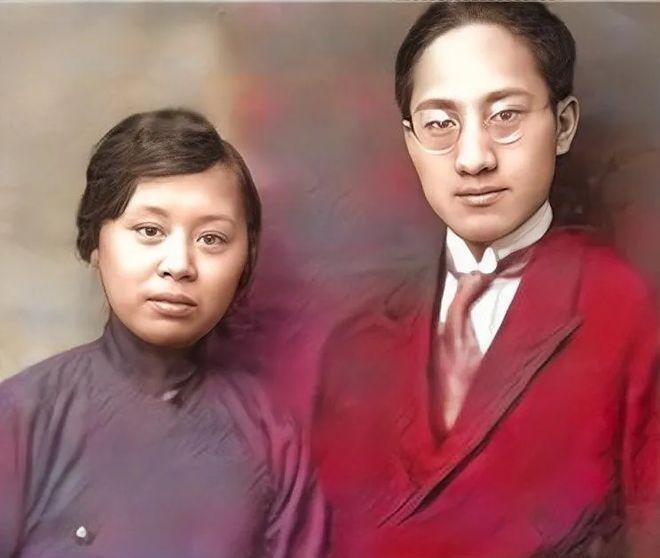




寇力
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