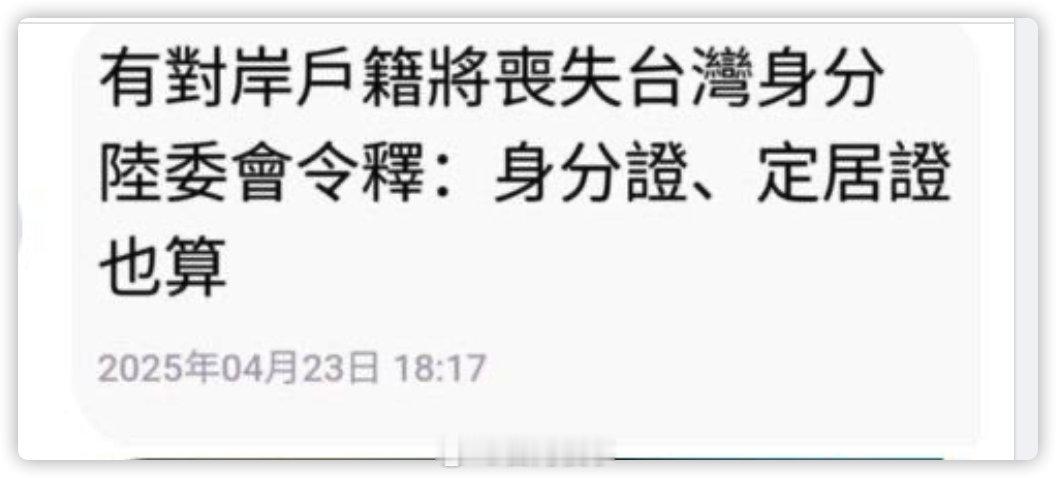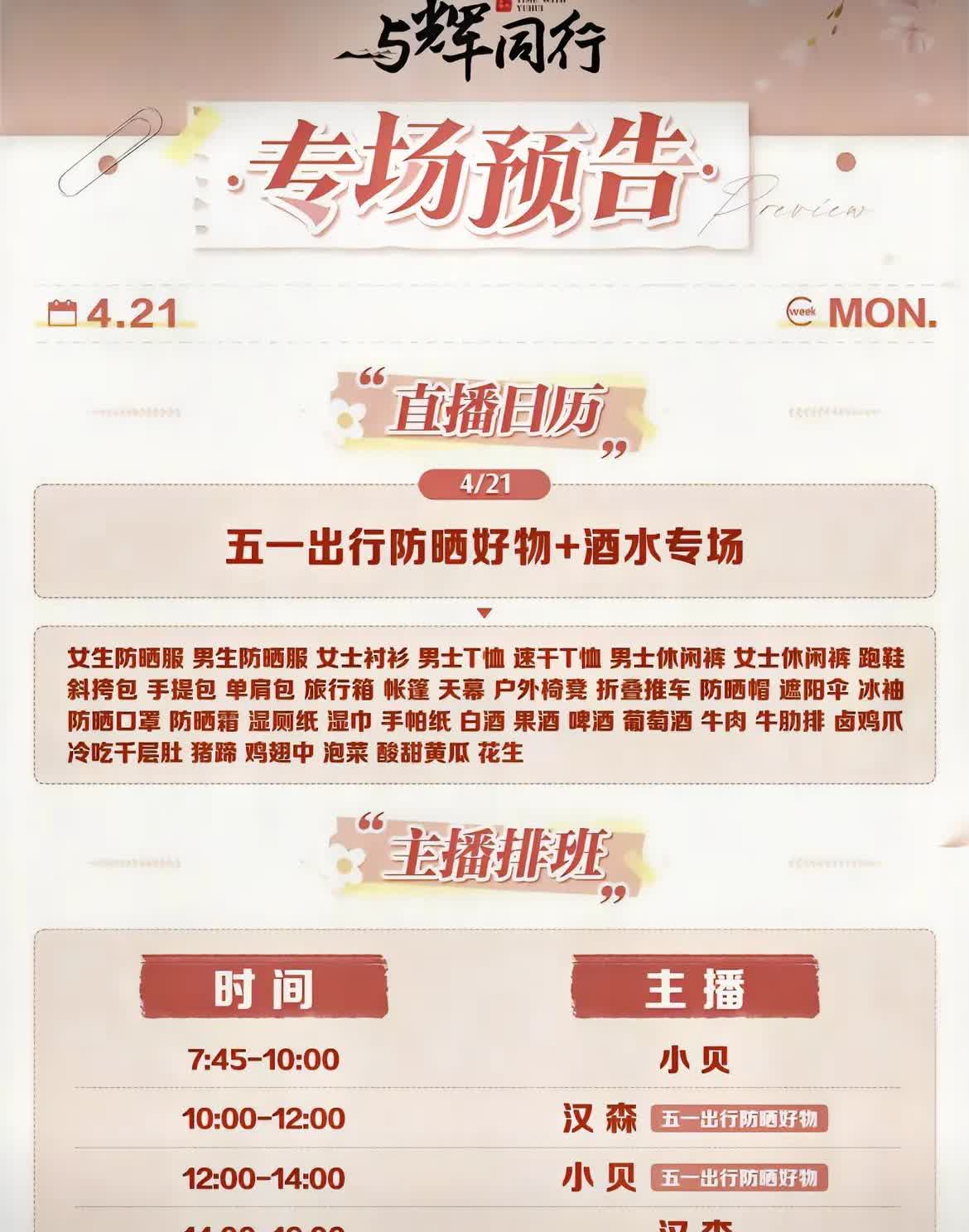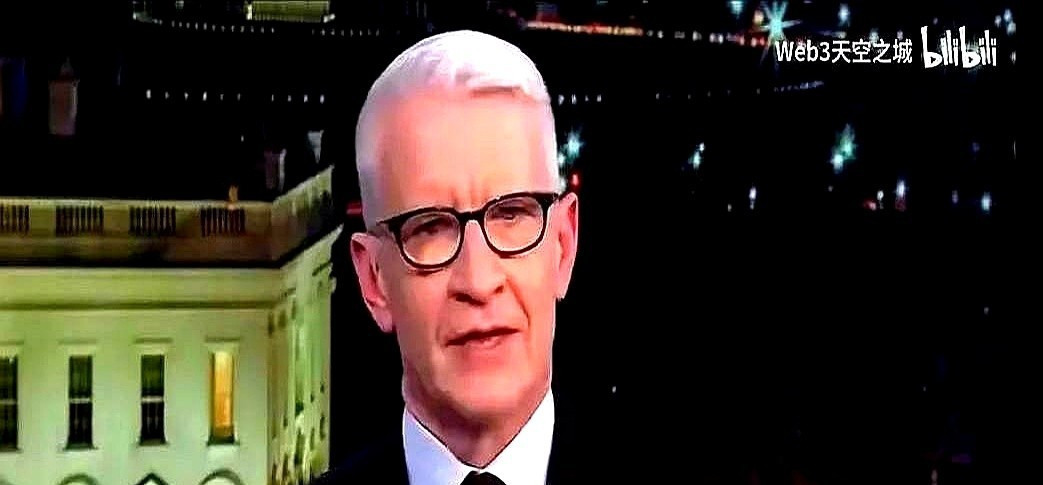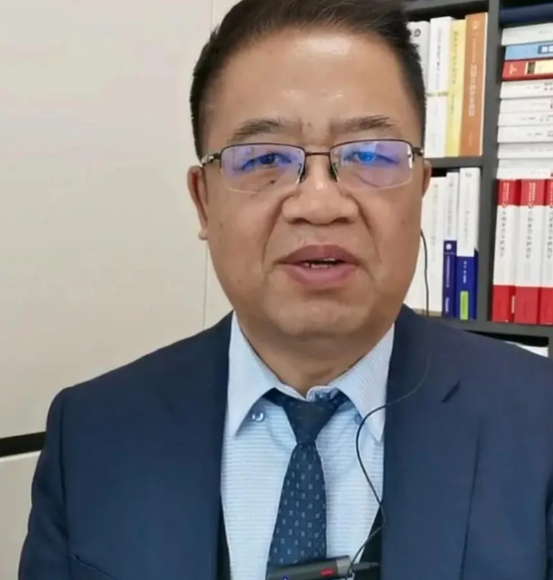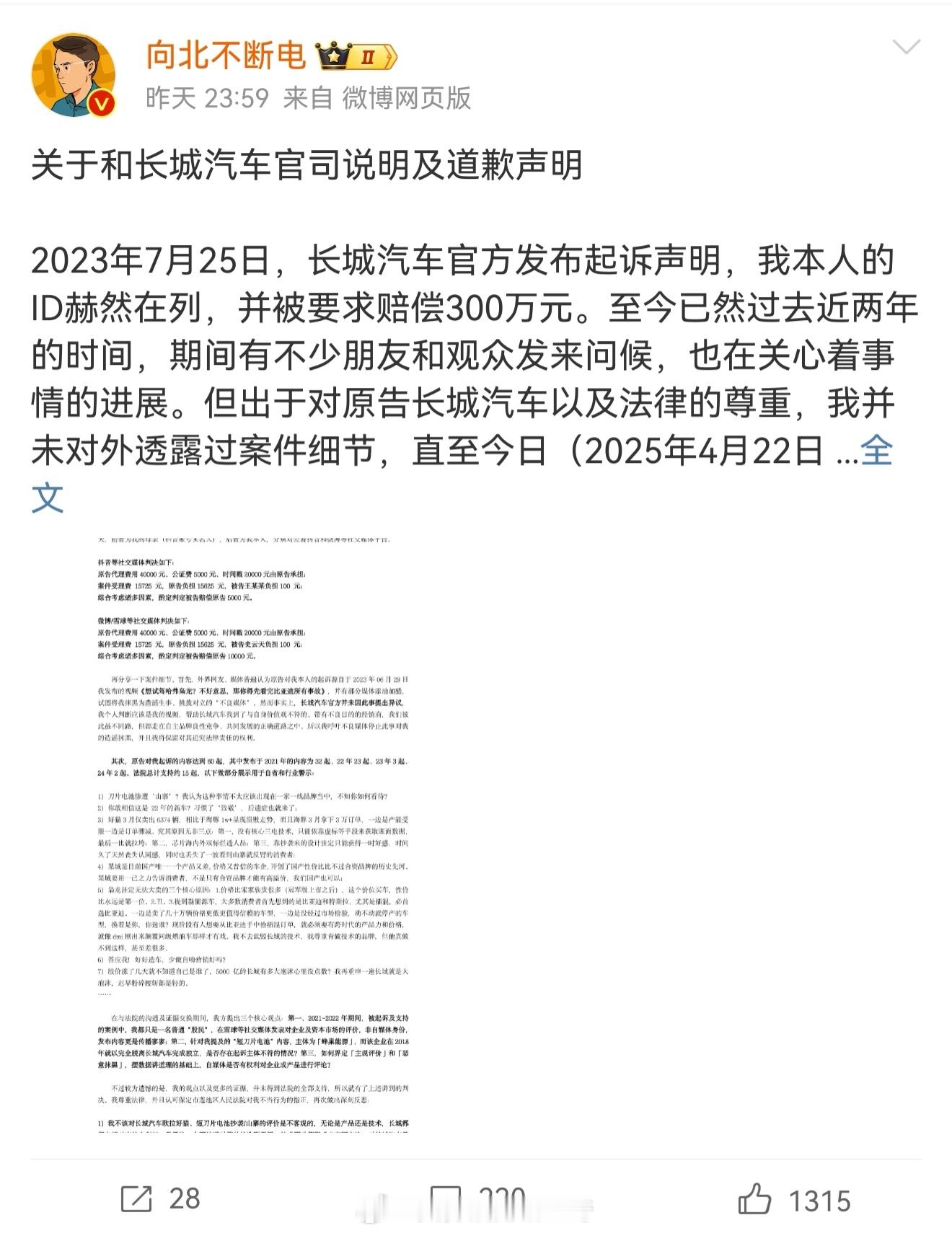1950年的重庆,晨雾还未完全散去,十八梯的青石板路上已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卖声。52岁的叶兰英挎着竹篮往菜市场走,鞋跟敲在石阶上发出细碎的响。作为在山城生活了半辈子的老街坊,她熟稔每一个摊位的位置,却在转过拐角时,被菜贩摊位前那个低头称菜的身影绊住了脚步——藏青色粗布衫洗得发白,手腕上有道浅褐色的烫疤,尤其是开口时带出的河南固始口音,像根细针扎进她记忆的最深处。 叶兰英攥紧竹篮边沿,指甲几乎掐进掌心。这个声音她永远不会忘。三年前的某个深夜,国民党特务冲进她位于石灰市的家,领头的正是此人。当时她的丈夫作为地下党交通员,刚送完情报回家,就被特务用枪管抵住胸口。灯光下,她清楚看见对方左眉梢那颗带毛的黑痣,还有笑时露出的金牙——此刻正在菜贩子低头称土豆时闪过。 “大姐,要啥子?”菜贩子抬头问道,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四目相对的瞬间,叶兰英感到太阳穴突突直跳,那对三角眼里闪过的阴鸷,和当年在刑讯室看见的一模一样。她认得这种眼神,那是渣滓洞刽子手看犯人的眼神,是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前,在白公馆松林坡见过的眼神。那时她作为洗衣妇,曾偷偷给狱中同志传递过布条,亲眼见过这个外号“猫头鹰”的徐贵林如何鞭打革命者。 喉头突然发紧,叶兰英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解放后政府一直在清查潜伏特务,上个月街道还开过动员会,区长说“特务就藏在咱们眼皮底下,老百姓的眼睛就是天罗地网”。她深吸一口气,指尖摩挲着竹篮边缘的缺口——那是去年冬天帮解放军缝棉衣时,被竹篾划破的。如今新政权刚站稳脚跟,决不能让这样的刽子手继续逍遥。 “来两斤莴笋。”她故意把声音放粗,假装挑剔地翻动菜叶,余光却死死盯着对方的手。当看见那道从虎口延伸到手腕的刀疤时,记忆突然清晰:1948年秋天,她在江边洗衣服,曾看见几个特务殴打一名船工,带头的徐贵林正是被船工用刀砍伤了手。此刻菜贩子下意识地把伤手往回缩,这个细微动作让叶兰英更加确定。 称菜时,她故意算起了糊涂账:“你这秤不对头哦,前几日老张的莴笋才八分钱一斤。”菜贩子不耐烦地摆摆手:“爱买不买,老子这儿不赊账。”河南口音混着重庆话的尾音,像块硌牙的石子。叶兰英心里一惊,看来对方为了潜伏,特意学了本地话,却改不了乡音。她佯装生气转身,却在拐过街角后立刻加快脚步,往解放碑方向的派出所跑去。 当民警带着叶兰英返回菜市场时,菜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摊位上的莴笋滚落在地,竹筐里压着半张旧报纸,边角处印着“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组”的字样。叶兰英心里一沉,正要说话,忽听见巷子里传来动静——转角处,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贴着墙根疾走,腰间鼓起的轮廓分明是手枪形状。 “就是他!”叶兰英大喊一声,竹篮甩出去砸中对方后腿。徐贵林慌忙转身,眼中闪过狠厉,伸手就要掏枪。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小王一个箭步冲上前,将他按倒在地。扭打中,徐贵林的帽子掉落,露出额角那道三指长的旧伤——正是1949年逃亡时被游击队打伤的痕迹。 这场发生在菜市场的抓捕,很快成为重庆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人们这才知道,这个卖了三个月菜的“老实人”,竟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在随后的公审大会上,叶兰英作为被害人代表出庭作证,当她指着徐贵林控诉时,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枪毙凶手”呼声。那一刻,她忽然想起丈夫就义前说的话:“等到天亮了,老百姓都会睁眼过日子。” 从历史的维度看,这个看似偶然的识别事件,实则是新生政权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必然结果。1950年的重庆,刚经历“镇反运动”的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通过潜伏破坏新生政权,而广大群众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叶兰英这样的普通市民,或许不懂深奥的革命理论,却分得清谁让他们在深夜担惊受怕,谁让他们能堂堂正正走在阳光下。 徐贵林的落网,折射出新旧时代的根本分野:在旧政权下,特务横行无忌,百姓敢怒不敢言;而在新社会,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再是被压迫的沉默多数。当叶兰英敢于直面特务并大声揭露时,她代表的正是亿万翻身群众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新政权对“人民至上”理念的践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每个普通人都意识到,保卫新社会就是保卫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