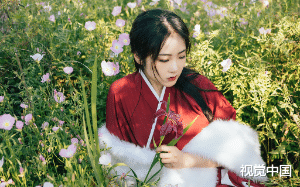夫君是名动京城的第一公子,我只是一介卑微的采药女。
隆阳公主一次出游,偶然遇见我夫君,从此对他一见钟情。
公主觉得是我挡了她位置,在夫君再一次拒绝她的「好意」后,她彻底疯了。
趁夫君外出办公的工夫,她派人绑架我,活活折磨至死。
高高在上的公主,站在我的尸体面前,故作吃惊:「这就没了?好没意思。」
01
血肉绽开的声音,以及我脸上的惊恐取悦了她。
直到我咽了气,隆阳公主才堪堪放开了我,缓慢地擦拭不染纤尘的手:「死了?好没意思。」
她说,好没意思。
一条鲜活的人命,在尊贵无双的公主眼下,不过低贱如一只蝼蚁。
人死往生,我的身体却变得很轻,身上的剧痛渐渐退散,就在以为要解脱之际,意识蓦地一轻,仿佛脱离了躯体。
此刻好像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轻飘飘浮上了空。
我瞪大了双眼,先看了看自己半透明的手,又忍不住向下张望。
原本的身体还躺在地上,血肉模糊作一团,没有一丝生息。
我游荡在隆阳公主和她侍女面前,竟无一人察觉出异样,她们谁也看不见我。
就在我困惑,到底算死了还是没死之际。
门外的侍卫扣门进来,及时提醒公主,京城大门即将落匙。
寺庙外的天渐沉,隆阳公主应着,毫不留恋地迈脚离开。
上马后,她不忘回头叮嘱手下:「尸体丢到乱葬岗,所有痕迹务必处理干净。」
我还在怔愣,却被隆阳公主带离了原地。
原来不能离开她太远。
我尝试过奋力挣扎,仍旧无法摆脱这股莫名其妙的吸力。
它将我紧紧禁锢在隆阳公主身侧,不管我有多么排斥、抗拒。
我心内惨凉,隆阳公主,就是做鬼也不肯放过我啊。
我麻木地被扯着走,随着马车回到装潢奢靡的公主府。
02
隆阳公主不惜杀了我,不过是因为看上了我的夫君。
我夫君,他曾是京城连中三元的瞩目才子,亦是金龙殿上被陛下钦点的状元郎。
夫君还偏爱干净的白,做素色打扮的他,气质脱俗又清皑,浑似覆雪下的高岭丘壑。
他眉眼淡漠锋利,不掩绝代容姿,生于寒冬,恰如其名寒雪。
然而这样一个名动京城的翩翩公子,他的原配夫人,却只是一个不入流的采药女。
也就是……我。
京中许多人不解,寒雪为何会娶我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妇,相貌平平,粗鄙寡陋。
还对我这般好。
他们岂知,我与夫君相逢于微末。
我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相濡以沫,在最阴霾的日夜里依偎取暖、不离不弃。
我们两个孤独的灵魂,一起走过贫困、迈过孤独。
与寒雪素来琴瑟和鸣,他亦待我温柔至极,其实很大的缘由来自从前,我无意中救过他一命。
当时他衣着褴褛,满身狼狈倒在西街的乞丐巷口,是我捡了他回去。
那时醒来的少年,一双倔强眸子里唯有极端的厌世,眼里没有一点光。
他后来说,是我点亮了他。
寒雪的母亲是不入流的妓子,所以他自小在勾栏长大。
但随年岁渐大,母亲的恩客对他这张脸起了心思。
母亲护不住儿子,于是他只能逃。
一路被人追杀,由于受伤体力不支 ,他晕倒在乞丐巷子里。
寒雪在我破败小茅草屋里住下来,那时他伤的很重,我在旁悉心照料。
他伤好了却不肯走了。
只说自己如今孑然一身,无以为报,除了一张绝色倾城的脸。
我开玩笑似地说,无以为报,那便以身相许吧。
没想到寒雪定定地看向我,好。
我那时没反应过来,寒雪却失笑欺身靠近我。
「念娘,要求是你提出的,难不成现在要抵赖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居然还有一丝明显的期待。
我红着脸将他推开,「谁抵赖了。」
反正吃亏的不是我。
乞丐配采药女,谁不说我们是正好一对。
我是孤儿,他亦无长辈,我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郑重拜了天地。
——以苍天为证。
日子平淡幸福地过下去。
后来他携我一并入京,我才知道夫君凭借本事做了官,我亦是个官家夫人了。
褪去乞丐的狼狈,在容貌与气质的加持之下,寒雪整个人容光焕发。
正当他以满腹才学名撼清流圈,以出色的相貌风靡整个京城的时候,我还在捡他的墨纸烹水烧茶。
偶尔听到旁人议论,我也会陷入懊恼,深感自己配不上他。
可他总能一眼看穿出我的小心思,带我走出府邸,再大大方方把我介绍给他的知己好友。
乱花渐欲迷人眼,君誓不忘来时路。
03
记得那日,他被调出省的圣旨下来的突然,那时我正挽着袖子,躬身翻晒熨好的草药。
寒雪卷着秋霜进门,月牙白的褂子上的凉意还未全褪去。
一进来,他便迫不及待将我揽入怀中,语气欢喜:
「念念,为夫要出远门一趟,圣上命我速去西墨地区,钦点那边的粮草账目。」
君上肯将如此重要之事交予他,代表了一种莫大的信赖。
只是此去一行,恐怕要半月之久。
我让他放宽心,在保证会给他写信后,夫君依依不舍地走了。
然而我也不知道,这一别,竟会成为永别。
夫君离家后三日,我便被人绑了。
那日我照常上街,给卢侍郎家的夫人送去草药,光天白日下突然涌出一群土匪。
他们杀光了所有丫鬟与侍卫,只独独留下我一个。
我被胡乱塞入一辆破马车,蒙上脸带走了。
马车开出京城,在一间京郊破庙前停了下来。
在这里,土匪无情撕碎了我的衣裳,恶狠狠地凌辱我。
我在绝望中无法哭喊、无法求救,下三滥的笑骂声、乱七八糟的怒吼充斥在耳畔。
终于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土匪从我身上起来,在以为噩梦即将结束时。
听脚步声又来了一人。
蒙着我眼睛的布条被揭开,一个衣着华贵的女孩,居高临下地站在我面前。
她睨着我的眼神,带着赤裸裸的鄙夷与嫌恶。
我认得她,当今陛下最宠爱的妹妹,隆阳长公主。
我身份低微,没资格去见这种身份贵重的人,自然与她也从未有过交集。
但是一次春日踏青过后,公主殿下被我的夫君深深吸引,自那以后一直追着他跑。
谣言四起,我便是在深居后宅,也听去了两耳朵。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烂在地上的样子恐怕太狼狈,攥紧的拳头透着莫大的恨意与不甘。
公主的丫鬟上前狠狠撕扯我的头皮,朝我脸上疯狂扇巴掌,清脆又果断。
「下贱的东西,竟敢用这种肮脏的眼神看公主,简直找死!」
我几经挣扎,大声说我是正经官家的夫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隆阳公主笑吟吟,眼里淬出恶毒的光:「春梧,给我好好招待她!」
接下来的两个时辰,她们让我尝尽了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被打断双腿,挖去双目,割去了舌头。
各种严酷的刑罚在我的身体上走了一遭又一遭。
到最后,我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没有一处不在流血。
隆阳公主用行动告诉了我,她不但敢,甚至还能更加狠毒。
鲜血染红了整座破庙,血光侵天,我微不可闻的抗拒被更响亮的棍棒声掩埋,鼻息渐渐微弱下去。
我死了。
合上眼最后一刻,眼前是隆阳公主染血的裙摆。
04
几天后,第一公子的妻子被歹人掳走,乱刀死于马下很快在京城传遍。
流言蜚语不断,作为始作俑者的隆阳公主趁机加了一把火,称这群土匪并非普通歹人。
他们是我的相好,我自己作风不检,才招致的灾祸。
桃色绯闻最是好闻,更别提本就不喜我的世家小姐。
企图为我寻说法的卢侍郎夫人,出门差些遭人抢劫。
她的丈夫莫名其妙被远调他乡,官场上还屡屡收到排挤。
我清楚,这不过是一个开始。
隆阳公主对他们的警告。
她对所有知情者立下马威,谁若是胆敢告诉我夫君真相,便是卢侍郎一家的下场。
长公主府的日子实在无聊,我逐渐从起先的反感、不适应,到后来麻木无感。
我盘旋在隆阳身侧,看她每日只做两件事:白日里与男子调笑言情,晚上则换成另一个,床上孟浪。
我不解却又困惑。
虽没读过几年书,但我眼中的夫妻和睦,合该是男女琴瑟和鸣、恩爱和睦。
而不是如隆阳公主这般,痴恋我夫君的同时,身边围满数不尽的男人。
得过且过的日子来去,时间一晃来到初冬。
一日雪夜,我又盘旋在横梁之上,无它,公主与男宠的房中动静闹得太大。
我麻木地翻身,认命闭上眼。
「公主,寒雪公子回来了,在外面求见。」
听闻夫君提早回来,我心下一惊,差点从梁上掉下去。
底下的反应比我更甚。
隆阳公主匆匆披上外衣,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留给床上的男人。
我跟着她飘出门,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
夫君应当是听到风声后,连夜赶回京城来的。
此刻眉宇间染上薄薄的霜,衣衫还是出事前日我寄出的那件。
寒雪眼下是乌青的淤,下巴生了细细的胡茬,明显好久没睡好了。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几欲要垂泪,扑上去想与从前一般拥抱住他,整个人从寒雪的身体间穿了过去。
我鼻子一酸,几月过去,都已经快忘了,自己俨然是一个死人了。
死人又怎能轻易接触到活人。
我只能干巴巴站在他的面前,泪眼汪汪看着他、望向他。
这一刻,数月来被我极力按捺下的委屈、思念倾泻喷涌而出。
原来人真的只会最亲的面前脱下面具,卸下一身沉重的伪装与防备。
夫君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他只恭恭敬敬地低着头,对款款而来的公主行臣子礼。
细雪下的淅淅沥沥,我的拥抱细腻无声。
「公子深夜来访,不知何事啊?」
红纸伞下,隆阳公主面容红润,笑容娇媚,丝毫没有杀过人后的心虚慌乱。
反倒批下三千青丝的她,只披一层薄薄的纱,身段窈窕得楚楚动人。
05
夫君的眼眸幽深,在我面前他永远温润谦和,溺于人间风与月。
或许今晚夜太浓,总觉得与平时不大相同。
「臣的妻子遭人劫掳,请公主替微臣讨一个公道。」寒雪抱拳低眉,声音里满是担忧。
我一怔后,露出苦笑。
他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啊。
凶手还是眼前这个女人。
我多么想要告诉他真相,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隆阳公主勾起他的下巴,语气轻佻而放肆:
「怎么办呢,本公主只替自己人做事,——就算是寒雪公子你,也不能破例。」
夫君身躯明显一僵,隆阳公主笑眯眯地放开了他,赤裸裸声音里满是勾引:「那日和大人说过的话,仍旧作数,公子不妨好好想一想。」
春梧大步上前,无情逐客道:「寒雪公子请回吧!」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从前公主对他承诺过什么。
只是在我跟前,寒雪几乎从未向我提起过这些。
我心里不知是何等滋味,这一瞬间仿佛自己才是他们之间的外人。
灵魂被隆阳公主扯回屋,她被一群丫鬟簇拥在当中伺候,心情好不惬意。
不多时,送我夫君出门的春梧回来了。
隆阳公主抬眼,眼神探着征询。
「恕奴婢直言,公子他没发现什么。」
春梧捧着一脸笑容,满是奉承地挤开了小丫鬟们:「殿下放心,咱们的人办事利落,就算给公子瞧出来了,他也拿不出实在的证据。」
「真要依奴婢看,寒雪公子也没多喜欢那乡野丫头,说不定只是碍于礼法不能休妻,她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哪还有什么感情。」
隆阳公主听得心神愉悦,褪下腕上一只镯子,「赏你了。」
角落里,听到一切的我失魂落魄地瘫软在地,喃喃不会的,不会的。
相识多年,寒雪怎会不在意我。
我失踪数月杳无音讯,他如今……怕是急疯了,不然岂会日夜兼程地赶回来,这般狼狈地出现在长公主府。
忽尔,隆阳公主抬起脸,旋即绽放出一抹残忍的笑容来:
「是啊,念娘那个贱人,居然配让本公主脏手。」
她唇角勾起冷酷残忍的弧度,死前种种非人折磨浮现眼前,战栗恐惧顿时席卷了我全身。
我害怕得不住哆嗦,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06
一旬以后,第一公子主动请缨成为隆阳公主入幕之宾的消息,成了整个京城最火爆的话题。
说是做公主幕僚,可连我都看的出,怎么可能只是幕僚那么简单。
底下人戏称我夫君为「那位」或「公主的那位」。
——再不是京城第一才子,翰林学士寒雪公子。
隆阳公主那夜言及,她只替自己人办事,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些原本歌颂他才德的赞诗,转眼间带上调侃与讥讽。
我的夫君向来风光霁月,清朗明月不染风尘,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自尊与骄傲。
却在入公主府短短一年,主动披上艳丽的华衣,学起那些男人的手段,讨隆阳公主的欢心。
隆阳公主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我将一切目睹得清楚,看得出来寒雪的改变。
曾经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现在不惜废弃政务,都要日日陪她泼墨作画的,也是他。
他有多厌恶鲜艳暴露的衣裳,以及那些献媚讨欢的行为,我与他相识数年,再清楚不过。
只因这一切都会让他想起那个女人,一个总是笑脸逢迎,奴颜婢膝地跪在有钱人脚边的可悲女人。
因为需要看贵人脸色行事,把唯一的儿子推上畜牲床的母亲。
正因为深刻感受过泥潭中挣扎无果的狼狈,命途渺小又绝望,他才会格外珍惜蜕变后的现在。
现在的夫君我好陌生。
可我总抱着一丝侥幸,始终不相信我崇拜的少年,同他过去的阴暗面和解了。
07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初冬。
夫君在长公主府一住就是五年,期间鲜少理会外界的熙攘。
那座曾经七品翰林居士与他夫人住过的宅邸,朱红的大门被厚重的灰烬蒙封,油漆剥落,失去了原本的荣耀与辉煌,五年来再无人问津。
我望着眼前与公主专注对弈的心上人,充满了迷惘:「他说讨厌以色侍人,生为男子合该在官场上建树立业,可如今在以色侍人的,确也是他。」
这番话是对身旁的老人说的。
他是我死后第二年遇见的魂魄,同我一般,无法重新投胎。
唯一不同的是,老爷爷能随意来去,而我被缚在人前,困于三寸地方之间。
刚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地府来的,那会儿看够了夫君对公主的柔情,哭乞求带我离开。
他说自己不是黑白无常,不是来收我的,让我失望了。
老爷爷应该死了很多年,忽然遇见我这样的「同类」,大概是出于新奇,常常往我这边凑。
有时给我讲他生平的趣事,有时吹嘘全国各地见过的光景。
我被困在隆阳公主身边五年,若不是他在旁时常宽慰,很可能支撑不下五年,就得面临精神崩溃。
老爷爷生前是一名富商,顺风顺水了一辈子。
人到暮年,底下几个子辈因为觊觎他留下的偌大财富,便开始互相厮打争斗。
他阻止不能,子孙们变本加厉,后来更是为了他的瓜分家产,将算盘打到自己头上。
老爷爷一生走南闯北,到头来却被子女算计至死,他无法咽下这口气,心有怨念才会留存至今。
「若非对他尚有牵,你怎会苦留在世五年。」
老爷爷眯着眼睛,浑浊的眼珠子泛着通透。
一语道破关键,我无法否认对寒雪的感情,远盛于隆阳公主带来的恨。
「那么您呢,看起来比我活的更长久。」总是面庞平和,丝毫不像怨念很大的厉鬼。
是的,我更愿意称我们这样不人不鬼的,为「厉鬼」。
他说他闯过南走过北,见过边疆的戎马孤烟,领略过江南的乌巷青衣。
我撇撇嘴,表示才不信呢。
聊到后面的我们,双双陷入沉默。
那么厉害一个人,价值走尽以后,不还是没了。
更别说我,一个卑微至末的采药女,死后根本激不起半朵水花。
没有了价值,我似乎连死都变得理所当然,为活着的人让步好像成了既定的使命。
寒雪成日不苟言笑,却在五年时间里摸清了公主的所有喜好,事无巨悉地记录下来。
为她出谋划策,与她和萧抚琴。
像一对真正的璧人。
从前我在时,他对公主总是礼貌而疏离,可事到如今,他还敢承认自己没有心动过吗。
隆阳公主荒唐至极,当他的面脱光衣服跳艳舞,他却眉头也不曾皱过一下。
她放肆而大胆,新奇手段是层出不穷,与传统规矩的我完全不一样。
连寒雪自己都未曾发觉,他眼睛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她,连眼神总会追随着她的身影而去。
旁观者看的更清,正因此更窒息。
我不排斥死后夫君再娶,可这个人为什么非是隆阳公主。
是害我如今鬼不像鬼人不像人,地府也不愿收留的元凶隆阳公主!
08
今年的初雪下的早,皇宫组织了盛大的初雪宴,长公主携寒雪风光出席。
我久久注视着他们,看着寒雪为公主体贴披上大袄、递去暖炉,总恍惚忆起往年初雪,他将我冰凉的手捂在袖中的情形。
他坏笑着捉弄我:「晚上回去,为夫好好暖暖你。」
许多年前的温柔历历在目。
因为明目张胆的偏爱,即便向来畏寒的我,从不害怕冬天的来临。
那时年少没有考量过,我的夫君,有一天会属于别人;他的偏爱,也会换人。
至于我,会亲眼见证这一切。
「公子这般,还以为你对本公主动情了呢。」
隆阳公主咯咯笑道,手指划过寒雪裸露在外的肌肤,「还记得你是为什么跟着我吗?」
我的夫君,面上只是笑笑,手却按住了公主不老实的动作。
——为了失踪的妻子。
可现在,与公主十指相扣的他还能保证自己没有陷进去么,陷进这个温柔乡。
隆阳公主允他前程,允他财富,允他滔天的权势。
这些,我都不能给他。
现在,他唾手可得。
与其说是为了寻我被迫跟在公主身边,倒不如说,我失踪可以是你们发展感情的遮羞布。
我自嘲地笑笑,老爷爷企图安慰我的话,在看到他们依偎一起的身影,一个字也憋不出来了。
他深深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今年,恐怕还有一场更大的雪。」
宫宴会上的气氛算不上很好,其实年年如此。
由于常年驻守边关的宁王回来,使得本就勉强的应酬场面更加难堪。
我听隆阳公主下面的人嚼舌根,宁王乃先皇最受宠爱的小儿子,由早逝的先皇后所出。
只是在后来的夺嫡之战败给了当今的圣上,为了保命,自请去边境驻守。
谁都没想到宁王还有回来的那天,本该死在战场上的人,褪去前半生的骄矜与贵气,挂着满身荣耀重回故里。
见我心事重重,老爷爷问在想什么。
我垂下眼睑,喃喃自语:「为什么要回来啊……」
「败者食尘,本该淘汰出局的人,就是回来也会被这群人看笑话啊!」
听我评价宁王,老爷爷只是摇头:「不到最后,不见赢家。」
「笑话又如何,没人一定得为既定的使命做出让步,就算有,也不该是生命。」
从宴会上回来的隆阳公主出事了。
她的酒杯中被人下药,此刻浑身难受,面颊泛着不自然的绯红。
第二天醒来后,她全身酸楚泛痛,身旁空无一人。
隆阳公主虽然私生活不检点,可不代表她不在乎被人算计。
自皇上登基以来,她顺风顺水的日子过得惯了,还没有人敢这样算计自己。
于是隆阳大发雷霆,要求大理寺连夜彻查,到底是谁意图害她。
大理寺被隆阳公主施加压力,很快便捉到了下毒之人。
投毒之人乃一名太监,他买通宴会上的倒酒丫鬟,趁机给长公主的杯里下了药。
按照大理寺口供,那人原本要下的是穿肠烂肚的毒,被不知为何后来换成了春药。
导致隆阳公主好端端没什么事。
这件事,公主没出什么大事,皇上也不甚在意。
但那太监是曾经先皇后的人,兴许背后是受了宁王的指使。
他们在意或许可以抓住宁王的把柄,于是再无暇顾及其他。
譬如那个消失在床上的男人。
跟在隆阳公主旁边的我却知道,那夜帮她解毒的人,是我夫君寒雪。
是他,偷偷把毒换成了春药。
与公主春风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