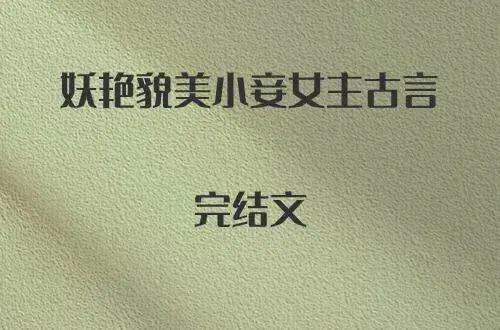父亲拥立先皇登基,以一已之力平定天下、铲除异端,成为开辟寻朝的最大功臣。
先皇去世,太子仓促登基。
翟氏一门三荣耀,甚至还飞出一只金凤凰。
大小姐位居贤妃高位,二小姐诞下长子册为昭仪,三小姐更是凤袍加身的皇后娘娘。
可是后来短短几年,翟氏很快风光不在:昭仪失宠、贤妃病故、太子中毒、皇后自刎。
活着的人,只剩下二小姐。
——也就是我。
1
新皇登基初,女眷受命入宫,一切事务繁琐。
清玉宫内,领路的公公客气鞠笑,一个劲儿问我新宫殿是否满意。
我还未说话,刚一坐下便有丫鬟掀帘进来,满脸喜色道:「前头有消息传来,陛下因娘娘诞育大殿下有功,特封为正二品昭仪!」
「太子殿下的册封礼,陛下也已在吩咐钦天监挑选吉日了,恭贺娘娘双喜临门!」
「那……安置问题?」我急急追问。
「还在娘娘这里,陛下允太子七岁过后再搬去东宫。」
一块巨石落下,我不禁松一口气,这桩心事总算是了结了。
其实不怕皇上翻脸不认,这个太子之位,先皇承诺给翟氏,他便不能不给。
我又问起姐姐那边的情况。
舒兰一下子支吾了起来:「圣上给大小姐贤妃之位,倒是封了三小姐凤位!」
我冷笑,就知道如此。
「圣上登基大典结束了吧?」
舒兰颔首,答道:「对的,听说刚一结束,陛下便往隔壁关雎宫去了。」
我连忙起身,准备重新梳妆。
舒兰不解,我言简意赅道:「皇上,马上要来。」
不过两刻钟,外头果然接到了陛下莅临清玉宫的通传。
「无乐,今日你辛苦了。」
皇上一来便要牵着我的手坐下,见我皱眉躲开,他只余下了尴尬。
「陛下可看过长姐了?」我转移话题,边问边添茶。
皇上接过茶杯,尴尬散去了大半,眉眼却是揉起烦躁,长抿一口后重重放下杯子。
「无乐,你替朕劝劝你长姐,朕许她贤妃之位,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翟氏一门三荣耀,已是登峰造极的辉煌!」
「陛下息怒。」我起身跪下,低头不多言语,眼底冷嘲尽显。
早在先皇没登基,父亲也还未发迹之前,长姐为结两家之好,才会听从家族安排,嫁给尚是一介草民的皇上。
婚后不久,他挂帅上阵,在战场奔波劳走;长姐替他坐镇后方,任劳任怨,不曾有半句怨言。
感念长姐的付出,君许以中宫之位厚之。
可后来当他真坐上九五至尊的高位,早已忘了两个人相携于微末的日与夜。
对曾经的糟糠妻,最后只草草给了个听起来高贵的妾位。
贤妃贤妃,让长姐做尽贤良淑德的宫妃,却闭口不谈曾经说给她的誓言。
似是看出了我的不满,皇上挠了挠头,胸中郁结更甚:「你与长乐均是一样,倔,太倔!皇后之位,许谁不是许,到底不还是你们翟氏的!」
絮絮叨叨过后,他似乎还不满足:「你们姊妹俩,到底不似徽音贴心可爱。她温柔小意,深得朕心。」
「无乐,你不要逼朕。」
皇上叹气说完,便要起身离开。
舒兰给我递眼神,希望皇帝晚上留宿清玉宫。
我视若无睹,心思不在这里的男人,再如何强留也无用。
皇上走后,舒兰跺跺脚,气我不争不抢。
我望向那杯没喝完的茶,「收拾了去吧。」
本就对那男人没什么感情,我自是无所谓的,倒是长姐,怕又要伤心。
她是那样细腻感性的人。
被亲妹妹抢走后位,位份在之下,宫中还不知有多少看她笑话的人。
少年夫妻从相知相守的走到形同陌路,其实长姐不是没想过挽回这段关系,回到他们亲密无间的时候。
可惜她不明白,岁月可以把人洗得面目全非。
自登上那个至高的位子起,日日浸润在高高在上、驾驭万民的追捧享受里。
像泡在大染缸的布条,人也会被轻易涂染成另一种颜色。
皇上总希望长姐主动折腰,就像身边其他女人一样,撒娇哭闹,用尽手段吃醋邀宠。
即使明知,她世家女的教养不容放低身段,随意跪在他的脚下摇尾、祈怜。
亦不许像市侩泼妇般,与一众上不得台面的小妾们,掰扯得分明。
长姐做不到,于是受尽冷落。
「今夜我去长姐宫里宿着。」
舒兰目露犹豫,「可万一……」
万一翻牌到了我呢?
没有万一,徽音留得住皇帝。
我坚信。
2
我带着乐宸去关雎宫。
长姐抱着小乐宸亲了又亲,欢喜得不得了。
「给姨姨瞧瞧,又长大了。」
一番玩闹过后,乐宸被抱下去喂食,我引长姐坐到案上。
长姐眼见我剥橘子,迟迟掰不开,叹了声从手里抽走,剥好后递给我。
「无乐,你不该如此心急。」
关雎宫与清玉宫相隔不远,翟昭仪犯上不敬,落皇上面子的事,自然瞒不过她。
我轻嗯了一声,将橘子放入口中,含糊解释道:「宸儿今贵为太子,我最大的心事已了,妹妹不图几分帝王薄情,只是想为姐姐争上一争。」
长姐陷入沉默,倏忽一苦笑,「终究是阿姊害了你,不若怪我身子孱弱,何须无乐你……」
我抬头,急促打断她的自责:
「长姐,进宫是我自己的主意,你切莫自怪。何况阿爹也说了,未来储君的生母,须得是咱们翟氏女。想当年情势紧迫,家中唯独我年岁适宜……」
父亲随先皇马背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无数,护国大将军的名头从边疆一路响到京城。
那年官民沸腾,权势加身,族中姐妹的身份无不跟着水涨船高。
恰逢东宫噩耗传来,族中有意送我替长姐固宠。
其实贵为翟氏嫡女,嫁予谁不是低配,进宫反倒成了优选。
我没有拒绝,心中那个少年的样貌,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绞得心头酸楚。
长姐如何不知我的为难,她亲眼见过秦王待我与旁人不同,也知道我暗中倾慕于他。
那年大雪埋路,我贪嘴出去买豆饼,是秦王撑伞护送我回了府。
少女的惊艳,是少年眼底落的雪。
正好的懵懂撞上相当的青涩,发酵在浓密的夜里,偏倚的伞偏说少年暗恋,有人红脸佯装不知话外音。
西街巷口的豆饼摊子,成了我与他相遇,但不宣之于口的默契。
直到有一次,我们与父亲撞了一个正着。
父亲没有怪我,我一向懂事明理,他长长叹气,宽大的手掌按在我头上,眼中尽是复杂。
「秦王与太子最近斗得厉害,你可知太子殿下,已有两月没有踏过你长姐的院子了。」
我怔愣原地,一时间,耳边只剩下呼啸而过的风雪,不得不从少女幻梦中挣脱,直面一个残酷现实——
秦王生母与皇后乃是死敌,长姐作为准太子妃,在外界看来,翟氏早已是板上钉钉的太子派。
我与秦王走的近,难免让翟氏背上摇摆不定的嫌疑,冠上贪权的罪名。
父亲没有立刻厉声喝责,逼迫我与秦王斩断关系。
一边是谋筹多年的大女儿,一边是二女儿的毕生幸福。
我看懂了父亲眼底的踌躇,看到为找出一个两全之法,他书房的烛火燃了一夜又一夜。
若此题无解,我不愿看他夹在两个女儿间为难,看他华发添鬓进退维谷。
于是我告诉他:「父亲,女儿知错。」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
其实我早该做出决断。
父亲誓死追随先皇左右,立下翟氏子辈永生永世效忠江山的诺言。
一句话,折进去长姐的一生。
可这不是他的错。
他是我们的父亲,亦是守护边关数万百姓的将领。
只是江山更替,新皇上位,外姓王权势滔天,注定不是一件好事。
先皇考虑得长远,父亲手中的剑,可以守护大寻江山,也会被当作下一代帝王的眼中刺。
长姐一早便清楚,她嫁给的不是婚姻,而是两位长辈部下的百年棋局,为翟氏、为大寻。
正因此,当先皇莅临翟府,亲口问长姐,是否肯嫁给太子。
长姐神色不动,没道愿意与否,而是恭敬叩首:「此乃民女之幸。」
棋盘纸上,她甘愿以身入局。
父亲深深地凝视我的样子,抚摸着我的脑袋,竟是哽咽:「吾儿命苦。」
我摇摇头表示不苦,身为翟氏女,享受多年的富贵荣华,必要时便该有所牺牲。
苦得是长姐,她从始至终就没有选择,嫁入皇室,配给未来储君,每一步皆是出于非已。
我回到自己的院子,断断续续哭了一宿,以慰葬这段短暂的感情。
再醒来,是一个全新的翟无乐。
3
「妹妹哭了。」
长姐将我揽在怀里,问我是否忆起了家中旧事。
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她不松手,语气故作松快:
「没事的姐姐,我这是做梦,梦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好事啦。」
枕头润湿,话尽曾是。
姐姐她懂,但无法言语,圈着我久久不语。
「倒是姐姐,昨日夜里听见你频繁咳嗽,」我皱起眉,「你没有好好吃药么?」
一旁的侍女欲言又止,被长姐温言阻拦,「真的不是什么大病,老大惊小怪的,老毛病了。」
我拉着脸,在长姐保证下次一定好好吃药以后,才终于缓和脸色。
「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是姐姐呢。」她朝我吐吐舌头。
我嘟起嘴,「谁让你身子老不大好,总叫我担忧得紧。」
是啊,长姐身子从来便不好,以前养在家中还好,后来嫁给太子,奔波不断。
长姐连夜操劳,没时间调理身子,等到后面发现已经晚了。
尤其是冬除春来,仿佛雪一消融,她也要跟着化去,脆弱如一只枯蝶。
记得有次随太子北上布粥,事必躬亲的长姐因体力不支晕厥,太子匆匆召集随行御医,竟查出姐姐已有一月身孕。
但因为母体孱弱,这个孩子终究未能保住。
小产过后,长姐自责不已,精神状况受到打击,身子一下子垮了下去。
御医甚至放话,姐姐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孕。
所以,我才会进府。
这是他们商议了许久的结果。
实际就算他们不开口,我也会主动要求,因为这是迟早的事。
毕竟先皇重诺,未来的国母只能出自翟氏;而未来储君,须得有一半翟氏血脉。
太子不会允许我嫁给其他皇子,我啊,也不会任由长姐凋敝于东宫。
我会像小时候,她耐心教我走路一样,扶她站起来,重新走过来时的路。
任何一种情况看来,我都不可能嫁给秦王。
在下定决心从这段感情中挣脱后,我便主动疏远了他。
听到我即将入太子府为良娣的消息,秦王不死心地追上来,他语气激动,甚至要带我私奔。
我拒绝了,将背后利益剖开给他看,告诉他我们没有一丝可能。
离去之时,他在背后质问我,是否有过片刻的心动。
怎么会不喜欢呢,少年伊姿飒爽,我又不是真的木头,岂会无动于衷。
被一顶小轿抬入太子府那天,帘子被吹开一道缝,我看到疑似故人的身影。
后来秦王大概是懂了,不再萎靡不振,自觉退出了我的生活,选择离开京城,就好像从没有存在过一般。
长姐愧对于我,生生折磨着自己,躲着不见我。
直到我踢开了她紧闭的大门,撞见她泪眼婆娑,脸上泪痕未干:「妹妹,我毁了你的一生。」
我摇头,抓着她瘦成骨头的手,逼她直视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哪怕没有她,我也绝对不可能嫁给秦王。
「只因我是翟氏女。」
只要我生下带有翟氏血脉的孩儿,姐姐的太子妃之位,就可以坐得稳稳当当。
婚后三月被诊出有孕,我摸着肚子感到庆幸,庆幸自己有能力,为翟氏脱离困境,挽救姐姐于水火。
而我的幺妹,不会再受限于翟氏大任,困于大门大族的联姻压力。
我们三姐妹,至少有一个可以获益于翟氏贵女的光环,嫁给自己如意的郎君。
「父亲,不要逼迫妹妹的婚姻。」
父亲答应了我,其实我与长姐的苦,他何尝没有看在眼里。
我放心入了东宫,转月太子便多了一位小翟氏。
东宫事务繁重,长姐身体不好,我帮她主持大小要事,确保协理之权不旁落。
与那些女人斗得你死我活,每天战战兢兢地过,生怕行事踏错一步。
彼时我不知,那个在我身后哭得眼圈红红的小女孩,被我与长姐呵护在掌心的幺妹。
摘取了我与长姐胜利的果实。
就那么轻易的。
3
待梳洗差不多的时候,外面有人通报,翟皇后来了。
我还没说话,徽音便从外头大阔步走进来。
她金色的华裙煞是好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忽闪忽闪,灵动而俏皮。
从前被这种眼神看得有多心软,现在我便有多么的避之不及。
「二姐姐也在啊。」
翟徽音见到我,不十分在意,只草草打了声招呼,便把目光放在了一身素衣的长姐身上。
毕竟在她眼里,同皇上青梅竹马长大的长姐,才是最大的威胁。
「长姐昨日可毋要怪我,听说皇上原本是要歇在你那儿的,不知你是说了什么话,把皇上气成那样。」
长姐面色惨白:「帝后恩爱,臣妾不敢妄言。」
翟徽音娇俏地呵斥道:「莫非长姐还在怪音音,抢了你的皇后之位?」
「可是陛下说了,他现在最爱的人是我,你已经是过去式了,长姐。」
翟徽音摆出小女儿情态的姿态当然可爱,皇上就喜欢她这副样子。
长姐能忍,我却没有这样的好脾气。
直接上去反手给了她两耳光:「皇上是被我气走的,妹妹不来说教我,一个劲牵扯上贤妃做什么!」
把翟徽音扇懵了,她尖叫一声:「我的脸!」
我反唇相讥:「你也说了,我们是姐妹,做姐姐的教训一下妹妹,有什么问题吗?」
幺妹从前在家中,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惧我,因为我冷脸的时候,真会抽她。
翟徽音哭哭啼啼地捧着脸跑了出去,她向来最珍惜这张脸。
她带来泱泱一众人跟着追出去,关雎宫再次安静下来。
长姐忧虑地扯了扯我。
「你心疼她?」我气呼呼。
长姐摇头,「徽音圣眷正浓,你这般招摇她,恐怕要吃苦头……」
我冷笑连连:「她要闹闹,我既敢打她,便想到被责罚的后果。」
身为翟氏嫡女,不尊亲姐;身为皇后,言语轻佻礼仪全废,合该教训教训她。
便是父亲今日在此,也不敢多说我半句。
4
皇上找上我是必然的。
他怒气冲冲地踏入我宫殿,朝服都未换去,张口就是指责:
「翟昭仪,谁许你对皇后动手的?」
我正埋头刺绣,闻言穿针引线的动作一滞,不徐不疾地推开了绣架,抬头望向盛怒的男人,这就是我的夫君。
与姐姐不同,我不爱他,也不惧他。
「陛下单凭皇后两句话,便要定了妾身的罪,那臣妾确实无话可说。」
我声音泠泠,平静得没有一丝情绪。
望着那个男人俊朗的脸庞,心里真心为姐姐不值,诧异一个人变化竟可以如此之大。
从前与姐姐感情好时,他亦经常照拂我。
长姐不许我吃乱七八糟的零嘴,太子就会悄悄对说:「无小乐,姐夫带你吃好的,别告诉你姐姐。」
被长姐发现以后,太子抱头鼠窜,我在一旁开心捧着热乎乎的豆花,看他冲我滑稽地眨眼睛。
那些暖融融的回忆,好像一并消失在了过去。
我曾多次提到过去,可姐姐总说不太记得了,次数多了我便不问了。
现在回忆过去的甜,太苦也太过于残忍。
太子登基成为了帝王后,也不记得这些了,一同连着这份偏爱,转移给了旁人。
这个旁人,还是我们的亲妹妹,翟徽音。
这段感情兜兜转转走到最后,好像只有我一个局外人,困在其中走不出来。
皇上终究没有重罚我,毕竟需要顾及太子颜面,但他要我在殿下跪上一夜,明日才起身。
如此,不过为了给徽音一个交代罢了。
我无所谓,从命跪下。
皇上刚走,长姐后脚便携乐宸匆匆赶到,见我跪在大殿一动不动,立时红了眼。
她原先想带乐宸来,希望皇上看在嫡长子的份上放过我,只是没想到还是晚来几步。
「母妃——」乐宸扑上来。
长姐命人给我膝下垫上毯子,语气不容拒绝:「秋寒露重,倘若真跪上一夜,你的双腿怕是要废掉。」
她少有这般疾言厉色的时候,向来温柔示人的姐姐,坚强却是为了维护自家妹妹。
姐姐坚持要跟我一起跪,乐宸也是。
我不肯,姐姐便沉默地看着我,乐宸则是泪眼汪汪。
我无法,只好央宫人准备了保暖的衣物,我们在敞开的宫殿里仰望着星空聊天。
乐宸在窸窣的谈话声里睡去,我把他交给宫女,抱到侧殿睡去。
「姐姐——」伸展酸胀的胳膊,我搂着长姐的脖颈,撒娇起来。
长姐怜爱地回摸我的头,从前在家中被罚跪,她也会因为担忧溜入祠堂陪我说话。
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我闭上眼想着。
如果时间能回到以前该有多好。
一切还没有发生。
回到我们三姐妹感情还和睦的以前。
5
可我忘记了,皇宫不是翟府。
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父亲,以及真心疼爱我的母亲。
徽音第二天来「看望」我,发现长姐与我跪在一处,发了好一顿脾气。
她不敢待我如何,从前在闺中惧怕我,现在当了皇后还有阴影。
徽音虽没对我们动手,却在皇上下朝过后,适时来凤仪宫后提了一嘴。
碍于我太子生母的身份,皇上明面上不太怪罪我,只是,他还是将关雎宫与清玉宫的待遇下降好几等,罚了我与长姐禁足。
不少妃子上门明里暗里地嘲笑我,非要自不量力与皇后作对。
次数多了我嫌烦,索性后来直接将宫门关闭,倒是落了一个清净。
数月一晃而过,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宫里打发。
在闺中我就喜欢看书,读各地民俗,浏各方人物。
隔绝外界纷扰后,我更加能全身心投入这份宁静,滋滋有味拜读起来。
可是天总是不遂人愿。
在初冬第一场雪纷纷扬扬到来之际,听说长姐再一次病倒了。
一解除禁足,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关雎宫,整座关雎宫冷得出奇。
皇上虽是降了两个宫殿的待遇,却也完全不到毫无炭火可用的地步。
「为什么不与我说?」
除了心痛,我还有一种不受控制的崩溃。
长姐的手好冷,她又瘦了。
丫鬟告诉我,禁足期间皇后曾多次来寻贤妃不快,内务府惯会见风使舵,关雎宫的炭火份额,拨分给了凤仪宫和几个宠妃那里。
他们就是看准贤妃性子软、好欺负,不会主动去与我说道是非,更不会与自家亲妹争论长短。
我气急拍案,怒其不争:「翟长乐,你把嫁妆分出来给了下人,你自己怎么办,你没有想过自己吗?」
长姐朝我凄然一笑。
「无乐……这身子我早知道的,老毛病犯了。」她如枯条般的指尖拂过我的脸,在触到温热的泪时候愣了许久,不知所措地找词安慰,「二妹,你不要难过,姐姐真的没事。」
我肩膀颤抖,强忍情绪站起来,「我宫里还有剩余炭火,这就叫人支来,等我一下。」
见我执拗如此,长姐便不再言语,她疲惫闭上眼,眼下淤青明显。
宫内第一场雪,皇上偕同后妃赏初雪,长姐病倒的消息传到皇上耳朵中,没有激起一丝水花。
长姐眼里最后一点光熄灭,她拽过我,苦苦恳求道:「无乐,你不要怪他。」
「他是一国之主,有自己的难处。」
我死死咬唇,在长姐近乎哀求的神色下,微不可微地点头答应了她。
长姐放下心,再次昏沉沉地睡去。
我替她拢好被褥,附在她床侧休息,睡得不十分安稳,一会儿便会惊醒过来。
只有听到长姐安稳的呼吸声,我才能重新安心下来。
半夜起身掌灯,侍女为我盖上披风,声音充斥担忧:「娘娘,贤妃的病只怕是……」
我猛地看向她,侍女不敢往下说,低下头去。
屋外飞雪重重拍打在窗柩,闷得我心头微窒。
我艰涩开口:「不会的。」
声音充满了恐惧,控制不住发抖,几乎站不稳。
我不愿意接受,长姐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一个小小的伤寒,她怎么会……挺不过去啊。
像是在说服我自己,更像自欺欺人,我一遍遍告诉自己,她一定会好起来。
「昭仪娘娘,外头……」长姐的贴身侍女匆匆赶来,面色不安,「皇后娘娘来了!」
她惊恐狐疑,压低声音:「这个点,这么晚了,还来关雎宫做什么?」
我让她不要惊动里头安眠的贤妃,自己出去应付。
「二姐。」
翟徽音一席红衣站在盛大的雪地里,美得触目惊心。
好像是早知道我在,没有问我为何会出现在关雎宫。
我与她,似乎也有大半年未见了。
「皇后娘娘深夜造访所谓何事?」
我态度冷淡,翟徽音只是怔愣了半晌,声音听起来闷闷的,「听闻贤妃有疾,本宫带了一些物品看望她。」
「多谢皇后娘娘恩赐,贤妃身子不便,臣妾代她谢过娘娘关心了。」
翟徽音咬牙,似不很甘心,「二姐非要与我如此生分至此么?!」
「臣妾不敢。」
我退后一步,将头埋得更低,姿态更加恭谨。
「翟无乐!」翟徽音甩袖愤愤离去,却不忘回头叫身边的人留下,把所有东西抬进去。
「娘娘这般对皇后娘娘,会不会……」
长姐的丫鬟生怕皇后一个不高兴,再次向皇上告状。
「不会。」
我打断了她。
翟徽音在愧疚。
长姐生病的消息早就传入养心殿,不过当时徽音陪在身侧,三言两句把皇上缠了住。
幺妹向来视长姐为最大的威胁。
她在怕,长姐用一个生病的借口,重新做回皇上的心上月。
太恐惧失去,才会尽力挽留,阻拦一切发生的可能性。
当长姐被彻底他们抛却脑后,凤仪宫歌舞升平,温暖似新春。
关雎宫寒若冷宫,内务府这才敢放肆无法,欺辱克扣到长姐头上来。
等病拖得愈发严重了,徽音这才慌了。
她将翟贤妃视作劲敌,却从未想过真要害她性命,更何况还是与她一母同胞的亲生姐姐。
帝王无情,我与长姐好不容易脱离出来,可她一脚深陷了进去,爱得不可自拔。
徽音将一切系于帝王恩宠,她看不到长姐早年奔波坏了身子,我入府后应付不完的宅斗内斗。
这大半年来,新入宫的嫔妃如娇花般一簇簇盛放,三宫六院逐渐被填满。
她总是很忙,忙着与越来越多的女人争宠,忙着计较帝王不平均的真心,忙着管理他的六宫四院。
我们三个,总是有一个在汲汲营营。
徽音最近与新入宫的美人斗得厉害,对方是邻国进献给皇上的公主。
眉眼风情异种,别有一番风味。
尤其是那一双勾魂眼,我曾远远见过一面,堪称倾国倾城也不为过。
皇上十分迷恋她,甚至为此冷落了皇后。
翟徽音从前喜欢红衣,但只限于重大场合穿。
因为其他活泼靓丽的颜色,她依然可以驾驭得很好。
只是现在,徽音开始不确定了,不确定皇帝是否真心待她。
曾几何时,她再没了以前的自信,华丽无双的凤袍焊在身上,凤冠沉得她抬不起头,却还非要挤出得体大度的微笑来。
一点没有了当年的游刃有余,轻松与自在。
只有这身衣服,可以一遍遍告诉她,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你看,其实徽音也迟疑了不是。
向来不需要证明身份的那股劲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不确定了起来。
徽音的落寞。
何曾不是下一个长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