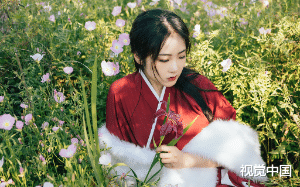二十七岁那年,未婚夫出轨白月光的晚上,
我魂穿古代,附身于一位相府嫡女。
接管她的身体,共情她的感情,扭转她的宿命。
唯一敬而远之的,是上辈子错杀她的少年将军。
后来,白月光声名狼藉,未婚夫浪子回头。
我却永远停留在了二十七岁。
1
韩锡生日那天,鲜少下厨的我费力做了一桌好菜。
然后满怀期待等到了午夜十二点。
直到手机弹出娱乐新闻:【新晋小花薛姗姗曝光恋情,对方疑是韩氏集团太子爷。】
我点开新闻图片。
迷离夜色中,黑衣黑裤的年轻男子将衣裙暴露的妙龄女子压在跑车门边,抚摸亲吻得激烈。
呵呵,韩锡从不会这么对我。
他情绪最激烈的一次,莫过于沉重的车轮轧伤我脚的那天。
他也只会在我鼓起勇气索吻时,将头嫌恶地撇过去。
「许绫映,我愿意听从安排,娶父亲战友之女,只是愧对于当年车祸害你留下残疾,但这儿...」他指着胸口,「有别人了。」
【韩锡,太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忙,先回家好吗?】
【你的生日已经过了。】
【没关系,再过几个月我也过生日,到时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韩锡,我们快结婚了,我多么开心能做你的新娘啊!】
讨好的短信如石沉大海。
我将手机丢开,一头倒在沙发上。
回想起韩氏主业明明是地产,韩锡却心血来潮做起了娱乐经纪,三天两头以公事为借口推脱婚礼筹备。
薛姗姗回国短短数周,就在舆论无脑吹捧下,从十八线飙升为流量小花。
我喜欢韩锡整整十年了,从青葱校园到职场社会,校草和学霸加持的他,始终是我心中难以企及的月亮。
可他也有自己的明月。
若不是偶然得知,我父亲与韩叔叔有出生入死的战友情,曾为后辈定下娃娃亲,高高在上的韩锡也许永远看不到我渺小的爱意。
墙上的时针还在不知疲倦地滴答,睡意也随着这催眠白噪音变得深沉。
2
「小姐?小姐!」
我被人从黑暗中唤醒,一个丫鬟模样的小姑娘急地满脸通红,见我醒了,扯住我衣袖就往外拽。
「哎哟我的小姐啊,教坊司舞女们早已等候多时,你怎么还躲在此处偷睡?」
低头瞅着自己身上那薄若蝉翼、轻若烟纱的红舞裙,我茫然不知今夕何夕。
「出门前老爷特意交代,太后寿宴,百官齐贺,小姐献舞可千万不能出乱子,不然咱们相府的脸面可没处放了!」
教坊司?寿宴献舞?相府?
每个字都听懂了,连起来就...什么玩意?
我摸了摸发髻,下意识说道:「小禾,那只镶红玉银丝头钗被我落下了,你快去拿来!」
小丫鬟愣了愣,然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叮嘱我原地等候,又急匆匆跑了回去。
我也呆在原地。
她真叫小禾?我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忽然之间,一些记忆碎片冲进脑海,令我知晓了这位小姐的身份——
苏静鸢,苏相嫡女,擅舞。
寿宴设在御花园,四面挂满了琉璃宫灯,整幢楼被映得金碧辉煌,锦衣华服的群臣围坐于舞池边觥筹交错。
正对舞池端坐的,是面容温和的太后,和雷厉风行的皇上。
好像身体自带肌肉记忆,宫乐一响,我就自然而然随着优美旋律翩迁起舞,红艳的舞裙在宫灯照耀下轻柔飞扬。
记忆告诉我,苏静鸢这一身舞艺是她母亲教的。
母亲舞姬出身,承蒙她父亲不弃,做了十多年丞相夫人,却在多年前生幼弟时大出血去世,苏相再未续弦。
苏相深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却执意偷教了她十年舞技。
十年苦练,足够惊鸿一瞥。
扭腰踏足之际,我抬眸向舞池下方望去,瞥见角落中一位男子似乎眼熟。
男子面若冠玉,英姿勃发,看向我的眼神,深情得几乎要将我溺毙。
我顿时打了个寒颤。
下一刻,新鲜而凌乱的记忆再度浮现脑海——
雕刻「鸢」字的玉佩被砸碎在地。
苏静鸢胸前汩汩涌出鲜血,浸透了雪白的衣衫,也染红了执剑人的掌心。
苏静鸢心神俱裂,一字一句艰难问道:
「沈松寒,娶我这些年...你爱过我吗?」
对面的男人脸色惨白,语气却比九天之上的霜雪更加无情:
「若不是你,我父亲不会死于非命。苏静鸢,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娶你!」
可怕的眼神,恶毒的话语,我被吓得脚步失衡,下一刻,就踉跄跌倒在舞台中央。
乐声骤停,群臣唏嘘。
3
原来,苏静鸢是重生的呀。
台下目光炽热的那位男子,就是记忆里的沈松寒。
沈松寒是镇国公独子,也是苏静鸢前世的夫君。
上一世的苏静鸢,是死在这位夫君的剑下,死在镇国公的灵位前。
当年,一曲惊艳的红衣柘枝舞让她名动京城,有臣子赞她「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后来,又不知谁作诗「静鸢美若斯,何不早入怀」,上门求亲之人便纷至沓来,令向来镇定的苏相看傻了眼。
而沈松寒亦在求亲之列。
此后一年,旁人都因苏大小姐的冷淡而偃旗息鼓,独沈松寒锲而不舍,镇国公与苏相在朝堂对峙的关系因此迅速缓和,苏静鸢也最终嫁给了沈松寒。
记忆到此暂停。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沈松寒与苏静鸢恩爱多年,最后为何会发展到刀剑相向的地步?
但冥冥之中我感觉,寿宴上我无心跳砸了这支舞,断了沈松寒的念想,也许就能斩断这场姻缘,并逆转苏静鸢惨死的下场。
在苏府祠堂跪了两个时辰,我膝盖酸胀,肚子也唱起空城计。
趁没人,我脱力瘫坐在地,身后却突然传来耳熟的呵斥:「你给我跪好!咳咳咳!」
我扭头看去,刚入知命之年的男人,已为朝廷倾力至两鬓斑白,听闻前段时间南巡防涝,他又染上风寒,久咳不愈。
许是这具身体还残留原主的情感,我忽然就觉得眼眶发酸,起身冲上去紧紧抱住他:「父亲!」
苏相怔了怔,待缓过神又不耐推开了我:
「好生跪着,今日尽给我相府丢脸。」
我撇撇嘴:「这不也没出什么事吗?」
「你可知太后寿宴,多少王公贵族等着讨好?你这一摔实属失了大礼,圣上仁慈才未降罪。」
我表现乖顺,实则心中腹诽:这封建时代的君为臣纲,实在荼毒人心。
又好似早已懂得如何拿捏这位父亲,我俏皮笑道:
「出丑了也好,省的被那帮只会赌博狎妓的王孙贵族惦记,指不定改日就上门提亲,可女儿还想多陪陪父亲呢。」
苏相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终于流露一丝慈爱表情。
深夜,幼弟苏彦抱着一只热乎的烧鸡,偷偷来祠堂找我。
他放低嗓门:「阿姐,今日你回府后,小王爷来找过你。」
「小王爷?」我再次在脑海搜有关此人的记忆,然后恍然,「平南王,江祁?」
苏彦点点头,又瞪着眼睛不满:「他说阿姐跳舞摔跤,可是奇观,千年难得一遇,这狗贼想上门瞧瞧,阿姐是不是正蒙在被子里掉泪蛋蛋。」
我轻拍他脑袋:「狗什么贼,被皇上听见你这样称呼他亲弟,不把你屁股打烂!」
苏彦撅起小嘴嘟囔:「江祁这浪荡子,对你肯定没安好心,阿姐实在要嫁人,我觉得只有国公府的沈松寒配得上你,文武双全,长得也不错。」
「可那镇国公在朝堂上总与父亲针锋相对。」
我哭笑不得。
4
古代数日,在现代的梦境中不过短短一夜。
清晨转醒,头脑昏沉。
我拿起手机,发现韩锡仍未回信,倒是一直待我如亲女儿的韩叔叔打来无数通电话,最近的是一条短讯:
【小映,别管记者怎么写,叔叔心里的儿媳只有你一个。】
我感动不已。
不一会,失联一天的太子爷打来电话,语气冲得像在问罪:
「有什么事咱俩不能好好沟通解决?动不动就拿我爸压我,许绫映,没想到你是怎么不懂事的女人!」
我掐着掌心,努力平复情绪:
「我从没主动找过你爸,你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就别怕被人偷拍。」
「好好沟通?我昨晚想等你回家好好沟通来着,可你给过我机会吗?」
「结婚前夕,你和别的女人吻得难舍难分,韩锡,你懂事?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他好像被噎住,语气弱下来:
「绫映,我告诉过你的,我爱的是别人。这婚可以结,只要你胸襟够宽广,不嫌膈应。」
我啪得挂断电话。
搁古代被人杀,搁现代还要被三天两头玩失踪的未婚夫出轨到无怨无悔。
老娘是肉包子,活该受倒霉气吗?
结果还有更气的。
没过几天,薛姗姗公然发布了一条微博,信息量满满:
阳光,沙滩,比基尼。
戴着墨镜笑容魅惑的大美女,回眸牵着一条半出镜的男人手臂,配文【你是我的!】
IP是千里之外大洋上的一座岛屿。
粉丝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姐姐好美!】
【这男的就是韩氏集团少东家韩锡吧,据说两人校园时期就是明星情侣,郎才女貌,养眼得很呢。】
【祝福姐姐!】
为数不多的质疑声,在浩如烟海的评论中被抨击、被淹没:
【韩锡貌似有未婚妻呀,许绫映,那个瘸腿的女画家,他父亲接受采访时还向公众推荐过他儿媳的画呢,大家失忆了吗?】
【什么年代了,还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残废画家,和我家唱跳皆佳的仙女姐姐,谁更有魅力,你眼瞎看不出吗?!】
【就是,韩锡默许姐姐公开亲密照,说明他压根没把未婚妻放眼里。】
【韩氏未来接班人要是这副喜新厌旧的德性,那我对他们企业的信誉深表怀疑。】
呵呵,我也觉得可笑。
订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缠着韩锡去旅行。
可随着他一而再再而三拒绝,我心仪的度假胜地,从遥远的爱琴海,就近变成了马尔代夫、巴厘岛,甚至让步为国内的三亚、鼓浪屿。
韩锡说,他对旅行没兴趣。
他不是对旅行没兴趣,是对我没兴趣罢了。
心不在我这,那就快刀斩乱麻,我拨去电话:
「解除婚约吧,下周一上午九点,老地方见!」
他回得倒是爽快:
「好!」
5
不出所料,是夜入睡,我又魂穿古代。
罚跪了一天,苏相允我出门。
我上街游玩,顺便想好好领略一番古朝都城的繁华盛况,一扫现实中被绿的阴霾。
一辆富丽堂皇的马车忽然从道路尽头御风而来,车轮扬起的尘土惹人直呛。
正腹诽那个大户人家出行如此高调,马车就在我身边缓缓停驻。
一个醇厚又漫不经心的男音穿透车帘:
「河对岸开了家新酒楼,厨子来自江南,擅甜,不知美人可愿赏脸同行?」
我莞尔一笑,掀开车帘,就着对方手劲蹿了上去。
「昨个儿还和苏彦聊起你,即便受过你的美食贿赂,他也坚决不认可你,直言你心性不正,祸害良家女。」
江祁摸着鼻尖一脸懊丧:「至于吗?本王形象就这般差?」
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我朝他一笑:
「你的自知之明怕是沉在定安河里捞不起来了。」
平南王江祁,与苏静鸢年龄相仿,是当今圣上同父同母的弟弟,亦是太后与先帝最宠爱的小皇子,全城百姓皆知他玩世不恭,举止轻佻散漫。
十二岁那年,苏静鸢随父出席宫宴,恰逢江祁在后花园调戏小宫女,苏静鸢道是谁家登徒子在此撒野,冲上去就将人暴揍一顿。
直到小宫女哭哭啼啼求她停手,苏静鸢才看到身后抱臂看好戏的皇上与气红了脸的父亲。
此后,他们不打不相识成为知己,太后甚至亲赐玉佩作为订婚信物,二人却并未如众人所料,掺杂过半点儿女私情。
江祁带我来的酒楼叫临江月,门面不大,但宾客盈门,生意兴隆。
自江祁踏入酒楼起,就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时不时瞟过舞榭,直到一面拢薄纱的姑娘怀抱琵琶翩然出场,他紧攥的手心才逐渐释开。
弦音切切动人心,而女子垂首凝眸抬腕撩弦的姿态,亦如那幻梦中走出的仙子,赏得人如痴如醉。
云烟然…
我心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
在苏静鸢上一世的记忆里,这位无数名门才子奉千金难求一面的京城头牌艺伎,却在我与沈松寒大婚当日,被贼人强掳至京郊欺凌了三天三夜,最后衣衫不整,被丢弃于闹市街头。
醒来后,云烟然只是默默走回妓馆清洗了身子,绾好发髻,笼一身素衫踏入血色残阳里。
第二日清晨,一具苍白的尸体漂浮于定安河面,如一朵凋零的栀子。
一年后,江祁郁郁而终。
我正发愁该如何阻止他这一世的悲剧,二楼倏忽传下来几个公子哥儿嬉笑声。
「我道苏相正经古板,调教出的女儿也必定寡淡无趣,没想到那苏静鸢跳舞的姿势,甚是撩人啊。」
6
江祁眼神一冷,握拳就要起身为我出头。
我赶紧按住他,劝道:「太后寿宴本来就是我错在先,别再为我将事态闹大。」
可楼上的大嗓门还不收敛:
「可惜学艺不精,我看倒不如那青楼花魁…」
我闭目强忍怒火,指甲却已掐进桌沿三分。
「哟,张公子怎知他不如青楼花魁,莫非你也品尝过,哈哈哈!」
「我倒是想尝,也得看苏相给不给机会呀,你看她那扭起来的勾人模样,腰若无骨,肤若凝脂,床上伺候男人的功夫怕莫也不会比青楼妓子差哪去。」
心头的火噌地一下冲到了天灵盖,我抓起茶盏正想动手,只听楼上骤然传来桌子被掀、瓷制杯盘噼里啪啦破碎的动静,旋即是重拳之下的呜呼哀嚎。
只见刚才还污言秽语的纨绔,此刻头上被淋漓浇下滚烫的汤菜,脑袋冒着热气,正狼狈地抱头鼠窜。
「他妈的哪个不要命的敢暗算小爷?知不知道我姨母是皇太妃,我父亲是靖恩侯爷,我母亲是——」
怒骂戛然而止。
待那小爷抹开头上的腌臜,瞪眼看清眼前之人时,立马胆寒噤声。
他唯唯诺诺低下头去:「沈…沈将军?您怎么也在这?」
沈松寒拿起身边小厮递上的毛巾,将手指上沾染的油渍一根根擦拭干净,正眼也不瞧对方。
「你姨母是被贬冷宫无皇嗣的皇太妃,你父亲是墨守成规无建树的最后一代靖恩侯,你母亲…是谁?」
对方脸上五光十色,正欲答话,沈松寒故作恍然:
「哦,莫不是当年太皇太后身边那个因为多嘴,差点被杖毙的大宫女?」
围观人群发出一阵嗤笑。
纨绔脸色发白,握拳敢怒不敢言。
沈松寒眸光一紧: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鼠辈宵小,也敢在本将军眼皮子底下口出狂言?」
「滚!」
那群人便连滚带爬逃出了酒楼。
江祁意味深长看了我一眼,一条手臂习惯性搭上我的肩。
「沈松寒向来孤高自傲,今日肯出手,莫非对我家小鸢儿有意?」
我嘿嘿尬笑:「有没有可能,沈将军一腔正气,眼里容不得人滓败类?」
蓦然间,感觉脊背一阵森寒。
回过身,只见二楼的沈松寒长身玉立,一道凌厉的目光正好落在我肩上。
7
第二天,苏彦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他说临江月的事已传遍京城。
可他却对沈家颇为厌烦:
「众人赞他沈松寒冲冠一怒为红颜,沈老将军却嘲讽我们苏家女人是红颜祸水,显得咱们上赶着贴他冷屁股似的。」
我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镇国公曾有意让老部下的女儿齐樱当他儿媳,老部下多年来随他出生入死,齐樱自幼在军营长大,是有巾帼风范的将门虎女,与沈松寒亦有同袍之情。
这些事,都是前世的苏静鸢在婚后听说的。
我劝苏彦:「沈将军年少有为,是人中龙凤,他父亲自然眼界甚高,平常女子入不了他老人家的法眼。」
「何况沈老将军与父亲在朝堂上势如水火,但历朝历代,这种文武重臣相制衡的局面,帝王未尝不喜闻乐见。」
等等!
一道精光闪过脑海,我好像明白了前世苏静鸢被杀的真相!
没错,文武制衡!
苏静鸢与沈松寒的姻缘,打破了这场制衡之策,为稳国祚,疑心深重的帝王宁可错杀一千。
「阿姐?阿姐!」苏彦摇晃着我,「你发什么呆呢?」
我心不在焉道:「没、没事,不久以后,边境可能要打仗了。」
苏彦难以置信:「几十年都风平浪静,哪来的仗打,阿姐说胡话吧?真要开打,咱们兵强马壮也不怕!」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
在前世,沈松寒的父亲就是惨死于这场漫长的战役。
向来深谋远虑的老将军,仿佛一夜之间被敌人熟悉了作战计划。
他信心十足地领五千精兵深入风平浪静的山林,却不知已被诱入敌军腹地,数万人的埋伏和突袭,让他们全军覆没。
老将军被敌军实施车裂之刑,头颅挂在边境城门上时,那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落魄而凌乱。
取回父亲首级那天,沈松寒枯坐了一夜。
后来,他将苏静鸢请进了书房。
苏静鸢刚踏进门,一把冰冷的长剑就抵在她脖子上,随即是被抛掷在地、碎成几块的玉佩。
举案齐眉多年的夫君,此刻眼神杀意凛凛:
「出征前,我与父亲连夜商讨制定的军事布局图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窃图者落下的这枚玉佩。」
碎玉上,「鸢」之一字赫然在目。
她噙泪哽咽:「沈松寒,你怀疑我?」
沈松寒嘴唇讽刺般勾起:「这枚独一无二的玉,我多年前就见你贴身佩过,苏静鸢,你嫁我,当真不是为你父亲出气么?」
她震惊地望着沈松寒,有太多话想说。
比如,这玉世上不止一块,死去的江祁也有一块,因寓意特殊,出嫁后我再未碰过
比如,这「鸢」之一字,并非我苏静鸢的鸢,而是江祁生母、当今太后——陈婉鸢的「鸢」。
比如,父亲已有意退居朝堂,明日还想邀我们夫妻与沈老将军,一块去府上团聚。
比如…
可沈松寒沉浸在丧父之痛中,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
长剑贯胸,恩断义绝。
她回握住染血的剑锋,千言万语凝成最后短短一句:
「沈松寒,娶我这些年...你爱过我吗?」
下一刻,她倒在血泊里。
除了恨之入骨的眼神,苏静鸢到死都没等来他一丝迟疑与怜悯。
记忆到此截止。
抽身出来的我仿佛溺水鱼有了氧气,难以承受般剧烈喘息。
8
这一世,苏静鸢应该远离沈松寒。
不光要自救,顺便也挽救竹马江祁。
所以,当江祁听说我要嫁给他时,刚入口的热茶全喷了出来。
「苏大小姐,你抽的哪门子疯?咱俩这么纯洁的友情,你现在要把它上升为不纯洁的爱情?」
我提壶将他杯中茶水续满,笑得谄媚:「谁和你谈爱情?你不是喜欢那云烟然喜欢得紧吗,我这是替你想办法。」
他脸上飞起一片红云,全然没了往昔混迹风月的吊儿郎当。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我把所有顾虑一股脑吐露了出来:
「你与云烟然地位悬殊,皇上为了皇家颜面,定不会允许一个妓子做堂堂平南王妃。」
江祁蹙眉:「皇兄与我兄弟情深,母后向来任我予取予求,若我执意,他们怎会不答应?」
我凑到他耳边,悄声说:「江祁,你相信我,我能洞悉未来,你若执意,云烟然只会死得很惨,你亦不得善终。」
「咱俩相知多年,知根知底,你先假意娶我,给云烟然换一个干净的身份,日后我以正妃名义为你纳她入府,会比你硬碰硬来得顺利。」
他突然把那张勾魂摄魄的脸凑上来,眼神幽深不明:
「洞悉未来这种胡扯就算了,你为我做这些,是图我的人还是图我的钱?」
切!
图啥都跟我没关系呀,我许绫映纯粹路过,就喜欢助人为乐,积德行善。
我将一块桂花糕塞进嘴里,拍了拍手,满不在乎:
「姑奶奶我见过太多辜负真情的渣男渣女,不光要我的心,还想要我的命。与其如此,不如不谈感情,只寻一处避风港,平淡安稳度过女子的一生,未尝不好。」
江祁盯了我许久,最终想通了似的,向椅背舒坦靠下:
「既然小鸢儿在乎本王生死,那这一番来之不易的善意,本王姑且笑纳了吧。」
「明日我就禀告皇兄,让仪制司用心操持你我的大婚事宜。」
…
我与江祁的婚事很快传遍京城。
第二天,上街采买的小禾带回另一个消息——
与齐樱的婚期将至,沈松寒却迟迟不愿迎娶,齐樱无意间闯入了沈松寒书房密室,被赶出来后,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沈松寒当即向镇国公提出要解除婚约,气急败坏的老父亲狠抽了他几十鞭子,可即便抽得皮开肉绽,沈松寒也咬牙不愿改口。
沈父气急攻心,倒床不起,沈齐两家关系降至了冰点。
一时间,京城百姓疯传,功勋卓著的沈将军竟视感情如儿戏,人家齐姑娘倾心相许多年,还是被始乱终弃,沈家引以为傲的高风亮节,被践踏得稀碎。
9
苏醒时,大理石地板反射的太阳光亮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手机铃响个不停。
接通后,那头传来韩锡的咆哮:
「许绫映,你玩我呢?三天了,我每天都在咖啡馆等你,可你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我告诉你,欲擒故纵这一套对我没用!」
劈头盖脸一阵骂,让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排斥与厌倦。
连知书达理的古人都不如,我以前怎么会眼瞎看上他?
等等!
他说…三天?!
我再拿起手机看,惊讶地发现距离我第二次魂穿,果真已经过去了三天。
难道每一次魂穿,停留在古代的时间会越来越久,在现实世界昏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么?
…
肚子咕叽又叫了,我拿起叉子将眼前的蛋糕五马分尸,大快朵颐。
韩锡指着咖啡馆外的街道,若有所思:「当年机车失控轧伤你的脚,我很抱歉,但感情的事无法强求。」
我嚼着蛋糕若无其事:
「我懂,医药费也赔了,还出钱给我办画展、出画册,韩叔把我当亲女儿对待,你们不欠我什么。」
我又抹了把嘴角的奶油,灌下一杯美式咖啡:「出来就想和你说清楚,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爸接受不了揍你出气,那是你的事,可别再冤枉我。」
韩锡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像一潭幽池藏着看不清的东西:
「媒体都知道你许绫映才是我未婚妻,现在分手,不辨是非的舆论只会把脏水泼姗姗身上,对集团也会造成负面影响,拖低股价,所以…」
我皱眉盯着这个男人。
「我希望你能再配合我,演一段时间的戏,等风头过去,我会补偿你一笔钱。」’
我气笑了,挑起眉梢:「行啊,韩总出手阔绰,想必补偿款比我卖画赚钱来得更快吧,成不了阔太太,分手前狠宰你一笔也是极好的。」
他没为我阴阳怪气的态度气恼,反倒是从身后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
「你答应就好,明天有场重要的商务宴,我将携你出席,力破舆论对韩氏不利的传闻。」
我缓缓揭开盒盖。
一条紫色晚礼服,散发着高贵冷艳的气息。
这种光彩的礼服,自然要配高跟鞋,可自从脚部落下残疾,我就碰不得高跟鞋了。
韩锡似乎忘了这一点。
这不是给我的礼物,这是以我的痛苦为礼物,献祭他光辉的前途。
10
晚宴上大佬云集,还有多家国内知名媒体。
眼尖嘴毒的记者自然不会放过韩锡。
「韩总,早先传闻您始乱终弃,与女星薛姗姗在酒店共度春宵,您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韩锡低头浅笑,将我一把揽住:「真相就摆在大家眼前,何须解释?」
然后在我耳边压低嗓音:「许绫映,别死人脸,好歹笑笑啊。」
我也降低音量,郑重威胁:「笑可以,但事关韩氏股价,得加钱。」
他瞪了我一眼,「加多少?」
「十万,笑一次。」
他咬牙:「成交!」
我这才乖乖挤出假笑:「韩锡怕我误会,连夜跪搓衣板求我饶恕来着,在我眼里,他是妻管严,可不是秦湘莲哦。」
记者们起哄鼓掌。
酒过三巡,韩锡撇下我去谈合作,我独坐角落,揉捏着强忍多时早已酸胀的残脚。
一位西装笔挺的年轻男子走过来,笑意良善:
「许小姐,我是您的粉丝,我一直很欣赏您的画。」
商宴中的曲意逢迎早见惯不怪,我礼貌回之一笑,举杯道:「谢谢您。」
「我参观过您的画展,您学的是西方油画,也偶尔涉猎国画,但恕我直言,您的国画反而比油画更传神。」
我愣了愣,国画只是业余之外寥寥几笔,未曾上心,更从未有人像他这样点拨我。
「先生过誉了,比我有天赋的画师比比皆是。」
「我研究国画多年,不会看走眼。」他越说越激动,「您的笔触、色调、留白都浑然天成,细节更是令人惊叹!」
韩锡忽然大步走了过来,挡住男子炽热的视线,好似宣誓主权:「周先生,宴会已结束,我要带我的未婚妻回家了。」
男子不肯罢休,递来名片:「许小姐,您的天赋不该被埋没,有空一定联系我!」
回去的车上,韩锡脸色不善。
「姓周的是圈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你脑子清醒点,别被他几句花言巧语迷惑了心神。」
酒气上头,我捂住熏红的脸噘嘴反驳:
「他花花公子?有你花?老娘倒追这么多年,你韩锡就像块捂不热的臭石头,浪费我宝贵青春,与其竹篮打水,我还不如招惹些个花花公子,反正都是虚情假意,分手也不会伤心。」
话音未落,我点个按钮,车顶天窗徐徐打开,清凉的晚风迎面吹来。
我笨手笨脚钻了出去。
韩锡大惊:「许绫映你疯了!快进来,很危险知不知道?!」
我不屑一顾,踹了一脚开车的男人:「滚你丫的!我的死活你关心吗?我被谁拐走你会伤心吗?你心里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女明星,你还陪她出国旅行,我的安危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以手扩音,朝寂静的夜空大喊:
「韩锡,你个王八蛋,有钱了不起吗,辜负我的真心,你要吞一千根针——!」
下方的司机哭笑不得,一手握住方向盘,一手紧拽我的裤腿:「吞,我吞!你赶快下来好吗,乖,听话!」
我顶着惺忪醉眼,俯视这个又眼熟又欠揍的男人,忽而委屈大哭起来。
男人将车靠边,一把将我拉回副驾驶,上下打量:「受伤了吗?撞到限高杆没?」
我只是哭,眼泪像不要钱的兰州拉面,哗啦啦淌了满脸:
「我踩了一天高跟鞋,我脚疼死了。」
男人低头一看,顿时懊恼:「对、对不起,我忘记这茬了,好了别哭了,今晚我陪你,满意了吗?」
我茫然点点头,就着酒意闭眼睡去。
11
再睁眼,万籁俱寂,夜色中弥漫着撩人花香。
直觉告诉我,这是苏府。
窗外突然闪现一道黑影,它轻盈越过了院墙,熟练地翻窗跳进来。
待看清来人,我蓦然呆住。
沈松寒?
他深沉的醉意吓到了我,我捂紧被子怯怯问:
「沈…沈将军,您是不是走错地儿了?」
他醉醺醺凑身上来,温热的酒气喷洒在我的脸上和颈间:「苏静鸢,我不娶齐樱,你也别嫁给江祁好不好?」
我浑身一震,内心莫名而来的悸动,如密密麻麻的针扎。
「将军与我本无交集,于情于理,都不该说出这般荒唐的话吧。」
「本无交集?」
他苦笑一声,无意间用手指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尖。
「三年前的暮秋,你在城郊为流民施粥布善,虽一身素衣未施脂粉,却明眸皓齿,温婉动人。」
「几个小乞丐为抢一个馒头扭打在一起,你毫不介意他们身上的污浊,冲过去凭一己之力将他们分开,还抱起一个最小的孩子,亲自喂他一碗热粥。」
「那日晚霞红得夺目绚丽,夕阳洒落在你背上,你整个人仿佛在释放温润的暖光。那一刻我就在想,若是我未来的夫人,也这般抱着我们的孩子,沐浴在绯红的暮色下,人生便在没有比这更美好、更令人心动的景色了…」
「若说交集,那便是我与你此生的第一次交集吧。」
仿佛被一道闪电劈中。
自魂穿苏静鸢以来,凭着她残缺不全的记忆,我一直以为沈松寒是在那场宫宴上看中了她,原来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动过心了。
见我脸色瞬息万变,沈松寒不由得舒展愁眉,如云开雾散后映入凡尘的一缕明光。
「你说荒唐,若三年前对你一见钟情算不得荒唐,那么此后我意愈浓情愈怯,害怕被你拒绝而迟迟不敢表明心意,甚至你在宫宴上跳舞,也忧心你被他人看中抢了去,便已是荒唐至深了。」
胸口诡异地泛起灼烧般的痛楚,怎么都压不下去。
苏静鸢啊苏静鸢,在你面前倾诉情意的,是那个十六岁就一骑当先击退敌军、名满京城的大将军,是月下击缶高歌、花间举樽豪饮的爽朗少年,是那一身铁骨柔情、剑胆琴心的前世夫君。
可他也曾是质疑你、怨恨你,为父报仇而错杀你的凶手啊!
你的深情,他已辜负过一次,你与他家世的对立,注定了这场姻缘以悲为底色。
我捂住胸口,强装绝情:
「静鸢心仪平南王多年,沈将军此番告白已然迟了。」
「怎么就迟了?」沈松寒浑身的凌厉比那酒气更甚,他箍紧我的双肩,怒到颤抖,「你与江祁只是君子之交,何谈心仪?我真不懂,这一次你为何要——」
我打断了他:
「沈将军未免太过目中无人,平南王是陛下亲弟,神采英拔,权势滔天,他敬我、护我、信我,亦能护我苏家周全。何况镇国公在朝堂与我父亲剑拔弩张,我是宁做王爷的妾,也绝不愿做将军您的妻!」
沈松寒错愕地盯着我:「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