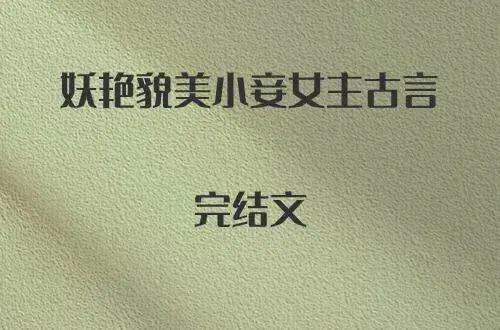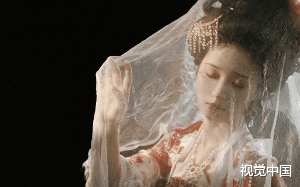我是丞相的姨娘。
可是却与太监日日偷欢。
他在门外站了一夜,两眼通红。
“芩娘,何必作贱自己?”
呵,娶了我嫡姐还强要了我!
以为我是什么贞洁烈女吗?
绿不死你!
一
我是丞相府上的宋姨娘所出。
虽为庶女,可主母仁慈。
到了蒙读年龄,主母特恩准府中的子女一同读书。
这年,我六岁。
我小娘总对我说做了主母是顶顶好的尊荣,不必每日晨昏定省,也不必日日讨好卑贱,若是有了子嗣,也不必……
每每说到这里,总是偷偷掉眼泪,又赶忙用帕子擦掉,扭头看我,说道:
“愿我的芩芩嫁个好人家,清贫些也无大碍,只要夫妻同心,平安顺遂,就好。”
我嘴上应是,心里却恼火的很。
我可不做那穷酸书生的糟糠妻。
我将来不仅要做主母,还要做顶富贵的主母。
承蒙主母恩德,府里不论嫡庶,吃穿用度别无二异,这才养的那时的朱清芩心高气傲、不知尊贱。
…
朝中民风开放,男女同席早已是常事。府中教习的温太傅为了省事,总是带他儿子温惊河与我们一同上课。
温太傅早年丧母,中年丧妻,独自一人养育儿子。男子又总是粗心,温惊河总是饿着肚子来朱府。
于是我日日藏着点心,寻着机会就递上去。一来二去,我与温惊河就熟悉了。
那时,我也是打心底里爱慕他的。
身量修长、剑眉星目又满腹经纶,满京城谁不夸他一句好儿郎!
可没想到,好儿郎志存高远,暗嫌庶女背后微薄,竟直接与丞相府的嫡女下了婚书。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竟敢跑去嫡姐房中问罪,简直昏了头了!
幸好嫡姐贴身侍女的话先冲进我的耳中,止住了我的脚步。
原来我与温惊河通信时,他刚与我嫡姐游河归家;原来我送与温惊河的点心时,他早就吃了嫡姐送的烤鸭……
也是,他从未向我承诺过什么。
这年,我十五岁。
我的小娘早已离世,我只能独自回屋抱着玉枕哭泣。
我哭了两天两夜。
只哭两天,过后,再觅如意郎。
……
可如意郎君没来得及找,我就“白”捡了个姨娘的名头。
我那好姐夫借着醉酒,认错了厢房,宿了一夜。
第二日我就被一顶小轿抬入了温惊河府中。
嫡姐为主母所生,与主母一道的黑心肠。
因我进府一事,外人谁不赞嫡姐一句温柔贤惠、得体大方?可关起门来,多的是法子折磨人。
我的小娘就是被主母磋磨的早早走了。
如今她的女儿又跪在下方,忍受着同样的痛苦。
日薄西山时,我那攀龙附凤的主君将将下朝,我才得以回那个连婢女都没有的小院。
……
夜半时分。
我的背后涌来一股凉意,惊醒起身后,立马给了来人一巴掌。
声音清脆,听起来甚是神清气爽。
温惊河顶着脸上的红印,毫无恼意。
“芩娘,我是心悦你的。”
“忍一忍,来日我定让你做正头娘子。”
今日清早时,我去给嫡姐请安。
侍女死死按着我,嫡姐亲自捻针,将细长的绣花针朝着指尖全部埋进去,过个一刻钟,又用东西朝着小口将针夹出来。
我的小衣都被汗湿透了。
可我一点都动不了。
我的嫡姐满意地告诉我,日后若是像我娘那样安分,就算有了子嗣,她必然也会好生相待。
可怜我的小娘,死去多时,我才知不差于嫡姐的吃穿用度是如何得来的。
二
那夜我伏在温惊河的肩头控诉着嫡姐的所为,企图换取一点怜惜。
眼前的男人柔声哄着我,保证以后不再让我受这样的委屈。
我低声应承着。
心里却快恨疯了。
若是再信他的话,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
不过月余,便有下人来通知我梳洗一番和温惊河去赴宴。
我一个姨娘,哪有资格跟着主君去抛头露面,除非是酒场逢欢的场面。
姨娘在酒场上不过是其中一道点心,哪家官人看上了,知会一声,春宵一过,就物归原主。
于官人们而言,不过是一桩黄粱美梦;可于姨娘而言,是无间地狱的开始。
……
马车里。
温惊河握着我的手,连声保证定不会让我出事。
我柔声应是。
上次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的小娘当年闺中时,就是十里八乡的美艳女人,连见惯酒场的丞相父亲都说难得一见。
我更是承了两人的优点,生的狐目花唇、身姿窈窕。
如今我站在温惊河身后规规矩矩为他布菜,周围还是投来不少的淫邪目光。
宴会上,当朝最大奸佞九千岁坐在主位,众多官员奉承敬酒,连温惊河也不意外。
我不觉哂笑。
十三岁的温惊河当初可是骂了九千岁姜执许久,下定决心将来必要除奸佞,肃朝纲,争做千古第一名相。
如今走了裙带关系做了丞相,却还要向一个太监弯了脊梁。
果然,日光催人老,权势压人腰。
……
宴席过半。
温惊河才发觉朱清芩不见了。
一个小太监,引着他来到京城只手遮天的九千岁房门外。
破碎的呻吟声冲破房门奔入温惊河的耳朵,这声音他再熟悉不过。
似忍受又似愉悦的热浪点着了他赤红的眼。
芩娘啊,何至于此!
……
翌日。
我起床的时候,温惊河还站在房门前。
看到来人,他眼前一亮,声音嘶哑道:
“芩娘,回家吧!”
瞧瞧。
瞧瞧这破碎的声音。
爽到我了。
“功夫不错。”
清冽的声音从屋中传来,引得朱清芩脸蛋羞红。
九千岁的话是容不得人反驳的,当朝天子年幼,先帝托孤于九千岁姜执。如今朝纲皆把持在姜执手中,明面上他是辅佐帝王,暗地里天子小儿都要听他训诫。
更不要说一小小丞相。
院中的男人听到此言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转身离去。
晨日曦光从远处拂过他的背影,送走了那个昔日将她从一众纨绔救出的温惊河。
这是温惊河的离别。
这是我的新生。
……
我入九千岁院中时,是十六岁。
九千岁的住所距宫门最近,每日辰时不到进宫,夜半沉沉才归来。
再次见到九千岁,是七天后了。
彼时我正在看新淘来的猎奇画本子,好为某人的到来做些准备。
“呵!”
一声蔑笑传来,我赶紧把书合上,下床行礼。
也不知他是否看到。
“之前答应咱家的事,可能开始了?”
……
那夜宴会中途。
在房中,我站在床边肆意吟哦,姜执斜躺在床休息。
烛光昏暗,白色亵衣下透着肉色,连劲瘦腰身都隐隐可见。
可惜了,是个太监。
床上的男人翻过身,左手撑头,眼睛发亮地盯着我,道:
“你当真有法子使我恢复?”
“若是骗我,你应当知道后果。”
惹了当朝九千岁的人就算被做成人彘也要恩德,没砍了全家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
可我有什么办法?
不骗姜执,我被嫡姐折磨死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骗了姜执,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其实我与姜执早就相识。
早年温惊河面冷,我送的点心从来不食。
气恼了的我将点心全都扔在后院门口,一个小乞丐总是伸出带有红斑的手从地上抓食,看他那滑稽模样,我还笑他是个贱种。
如今姜执模样早已看不出当年狼狈,手背上的红斑却仍是独独一份。
我不敢以此事相识,亦不敢赌。
不敢赌姜执认得是饱腹的恩情,还是嘲讽的恨意。
在今天之前,我以为是前者。
但此时,我知道我错了,大错特错。
……
我的小娘是位姨娘,白日里侍奉主母,夜里伺候主君。为了留住主君,让日子好过些,学了许多权贵女子看不上眼的手段。
幼时,那些书我全都偷偷看过。
为此,掌心挨了不少打。
每每挨打过后,小娘又把我抱在怀里,低泣道:
“娘是为了你好,我的芩芩一辈子都用不了这腌脏手段。”
我伸出通红的小手抹掉小娘的泪。
“小娘,这不是腌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