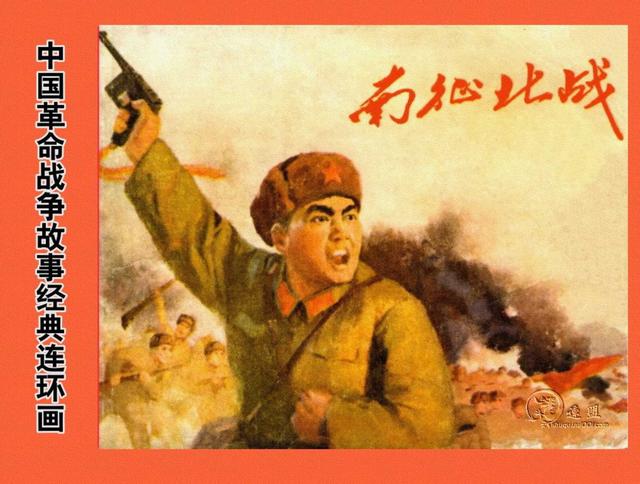我出生于1939年3月。母亲生我时,父亲不在身边。为了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的“大扫荡”,父亲正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与日军激战。
收到母亲的报喜信,父亲高兴极了,立即给母亲回信说,孩子就叫“太行”吧。后来父亲告诉我,按照刘家的家谱,我是“太”字辈,又出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为“太行”。
我一岁多时被送到延安,交给朱德总司令代养。当时我生活在延安保育院里,一到周末,朱总司令就乐呵呵地把我领回家去。朱总司令和康妈妈十分疼爱我,让我感受到父母般的爱,我亲切地叫朱总司令为“朱爸爸”。
我的大妹妹刘华北出生后也被送进延安保育院。小华北长得胖乎乎的,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十分可爱。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常常迈着不稳的步子,跟在我屁股后面“太行哥哥”、“太行哥哥”地叫着。
1943 年 10月,父亲和母亲从太行山回延安。他们第一次来延安保育院看望我和妹妹,没想到我和妹妹都不认识他们了!我们瞪着眼睛望着两个陌生的大人,局促不安。我小声嘟哝道:“我们的爸爸是刘伯承,还有朱德爸爸,你们是谁?”
父亲笑呵呵地走过来说:“我就是刘伯承啊!”我摇摇头:“我刘伯承爸爸在前线领兵打小鬼子,没有时间来看我们。”一旁的母亲听到这话,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我执意不跟父母走,还是朱德爸爸发了话:“先在这里住一段吧。”后来我们兄妹在朱总司令家住了一段时间,才被父母亲接回家。开始时我还是不习惯,总是有点生疏地叫他“刘爸爸”。
不幸的是,1945年8月,5岁的小华北在保育院被混进来的敌特残酷杀害了。接到保育院的电话,父亲和母亲立刻赶了过去。
保育院里一片低低的呜咽声。小华北静静地躺在那里,脸色苍白,那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再也不能睁开了。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父亲脸色铁青,手微微颤抖着,额头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
父亲强忍悲痛镇定下来,他神情刚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太悲伤!敌人以为对我的女儿下毒手,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就会六神不定,听从他们的摆布。他们打错了算盘!”
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前夕的紧要关头。妹妹遇害没多久,父亲就接到任务去了前线。这个悬案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破获。虽然父亲从来不提妹妹的事,但妹妹的死是父亲心中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痛。
1946年,我跟着父母离开延安到河北涉县,父亲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那年我七岁,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找学校成了难题。有的同志向父亲建议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
父亲把我送进了武安县冶陶镇的一所农村小学。农村小学的条件落后,一些土砖和木板搭起来就是课桌和板凳,我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启蒙阶段的学习。后来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了,我才转入了该学校,但父亲时常教育我不要搞特殊,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从小到大,我很少和父母在一起。后来父亲率部进入大西南,把我转到北京读书,开始时我还是住在朱爸爸家里,可是朱爸爸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20多个孩子打地铺,实在住不下。父亲又让我寄住在邓小平叔叔家。
1951年,我们全家搬到南京,之后弟弟妹妹都出生了,家里十分热闹,我们也一天天长大。
因为家中人多,住房显得有些紧张,营房部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给我们家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父亲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父亲外出,在我们家后院加盖了两间平房。
父亲回来后,把营房部的负责人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坚持把这两间平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父亲很欣赏这句话,从小父亲就让我们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当时全军实行供给制,父亲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
父亲常常对母亲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搞特殊。”
父亲的专用车一般不准家属坐,母亲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风雨无阻。我们兄妹不管是放寒暑假回家,还是开学返校,父亲一律让我们自己坐公共汽车。
在我们家的电话间里贴着一张母亲写的告示:“儿女们,这个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个电话。假公济私的坏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兄妹都严格地遵守着告示上的“家规”。
父亲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建国初期,在苏联编写的《大百科全书》中,提到父亲的词条是这样写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父亲看到后,毫不犹豫地把“军事家”三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两个字。
父亲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个人主义是父亲一直反对的。
父亲有句口头禅:“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父亲曾经说:“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1949年,父亲出任新中国的首任南京市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兄妹去参观中山陵。我们到了那里,才发现中山陵出了告示,说因故不接待参观者。我正觉得扫兴,中山陵的负责干部已经闻讯急忙赶来,请我们进去参观。
父亲客气地拒绝了,转身带着我们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对我们说:“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我心里十分佩服父亲。
父亲武将名声在外,实际上他自小就酷爱读书。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在公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父亲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会带着书。读书已成为父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父亲看得最多的就是历史、军事、俄文书籍。他一看起书就完全沉浸在书里了。有一次,我们在楼上闻到一股橡胶烧焦了的臭味,下楼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电线短路了,可在楼下看书的父亲却浑然不觉。
父亲博闻强识,口才一流,我很喜欢听父亲讲故事。我们向他请教问题时,他都非常认真、耐心,从来不发脾气。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他给我们开了一张必背的书单,小时候,《史记》、《古文观止》、鲁迅的散文集等都是我们兄妹必背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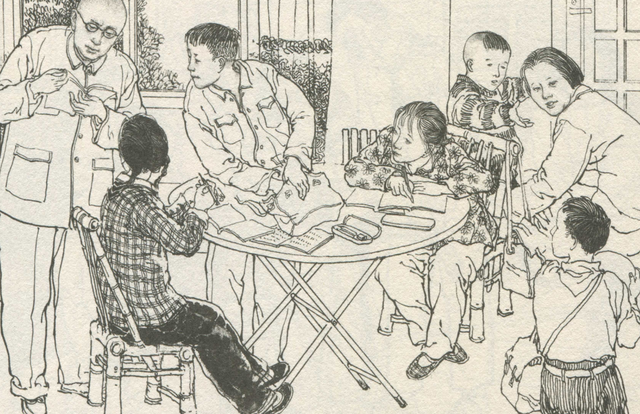
我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边背书边玩,一不小心就把一本新书撕了半页。父亲在抽查我的背诵时发现了,却没有发脾气,只是对我说:“书是个老师,而且是个百问不烦的老师,随便你问它多少次,它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你要爱惜书。”
父亲从书架上拿出几本书递给我,那些印在褐黄色土纸上的书一看就有不少年头了。父亲告诉我这些都是他抗战时读过的书。这些书非常平整,甚至连一个折角都没有。我随手翻开一本,书的每一页都有父亲密密麻麻的批注,有些地方写不下,还贴了纸条。我的脸一下红了。
父亲看我知道错了,微微笑了笑,拿出浆糊和白纸,小心翼翼地开始粘书。他先把撕下来的那半页书拼好,然后用裁成条的白纸粘紧,再一笔一画地把中间有些缺掉的字写上去。父亲那屏气补书的神态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父亲不爱讲自己的辉煌历史,在家里,他从来不给我们讲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小时候我没少缠着父亲讲长征故事,父亲说:“你去看看我那本《回顾长征》去。”我找来一看,发觉书里没什么故事。
有时候吃饭时试着问问,父亲顶多说个一两句。比如,我问他:“爸爸,您和叶挺是怎么认识的?”他就说:“我们是在南昌起义时认识的。”然后就不说了。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血战,负伤十一次,其中重伤九次,那些伤疤也是父亲戎马一生最忠实的记录。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想让父亲讲讲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父亲却说:“太行,你知不知道,你每次一问我这些,就让我想到多少白发苍苍的老人找我要孩子,多少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我只是一个幸存者!”
父亲厌恶战争的残酷。他一直不愿意看打仗流血的战争影片,只要电视上出现了战争情景,他立刻就关掉电视或者换别的频道。
有一次我和弟弟妹妹们把他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让他看拍摄打仗时坦克怎么轰炸,人怎么死,说明拍电影都是假的,结果他还是不愿看战争影片。
生在军人的家里,在部队中长大,我自小就有当兵的梦。初中毕业后我嚷着要去当兵,但父亲说:“初中文化程度太低了,建设新中国要有文化,你先好好学习,今后干什么再说。”
高中的时候,我理科学得不错,但更喜欢文科。当我和父亲说起今后考大学想学文科时,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我对孩子没有大的要求,还是学技术吧,自己能自立就好。”
父亲性格内敛,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不随波逐流。我是一个话很多的人,父亲幽默地教育我说:“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乱说话是臭狗屎。”
1951年,父亲向毛泽东主席辞去一切党政军的领导职务,请缨办学。父亲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为创建解放军的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干部的正规学府劳心劳力。
父亲自命为“教书先生”,给学生上课是他最开心的事。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材料,他不但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作品,还结合自己的作战经验自编教材。
父亲当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一眼失明、一眼弱视,他就拿着放大镜伏案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也不肯休息。父亲身体本来就不好,又耗费精力潜心办学,头疼时常发作。
父亲总说“慈不掌兵”,对学生要求很严。早上的会操他必定到场监督,从不缺席;晚上还要亲自检查内务,要是不够整洁,他就会立即批评。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军事学院。因为国家刚施行军衔制,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穿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欢迎。
不料天公不作美,仪式当天下起大雨。有人向父亲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里进行。父亲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尽管雨势很大,他还是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礼服,冒雨迎宾。苏加诺一行大受感动,对父亲赞不绝口。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在军事学院里开展起来,矛头渐渐指向了父亲。
1957年,父亲因病住院治疗,承受着病痛与忧虑的双重折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运动”愈演愈烈,成为父亲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事院校建设被迫中止。
1958年5月,为期近两个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父亲被推到风口浪尖。7月,正在上海治病疗养的父亲,接到军委的指示,让他到北京出席会议,做检讨。
66岁的父亲抱病乘上火车,心潮起伏的他怎么可能睡得着呢?因为没有休息好,他下车时左眼通红。母亲想让他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是父亲还是立刻赶往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
会场座无虚席,气氛极其压抑。这些人中许多是父亲的老部下,可如今父亲却要在他们的面前检讨自己···不管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父亲,这都是一种折磨和煎熬。
当父亲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沉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时,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下来。父亲当年右眼中弹进行手术,在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都硬挺着未吭一声,此时他的眼眶却有些湿润了。
父亲从口袋里颤巍巍地取出他早就写好的“检讨书”,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当他念完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经久不息。这掌声,是对父亲无言的支持和鼓励。
对于自己在“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父亲坚强地承受住了,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他对母亲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父亲在1957年8月就曾因健康原因向中央递交了辞呈。1958年11月,父亲被免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1959年1月,父亲带全家从南京迁居北京。离开南京那天,军事学院的众多师生赶到江边为父亲送行。船开了,渐行渐远,可岸上的那些人却久久没有离去。
1959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父亲露出难得的微笑,主动问起我的升学打算。父亲说:“你不是一直想当兵吗?到哈尔滨,报哈军工吧!”父亲的建议正中我下怀,于是我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我拿到了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家里喜气盈盈。父亲提议全家照个全家福。阳光和煦,我们兄妹六人,加上一个堂姐,簇拥在爸爸妈妈的身边,在庭院里留下了一张宝贵的照片。
我去读大学后,父亲叮嘱我要每个月给他写信,汇报学习和生活的情况。父亲每次都认真地给我回信,他总是教育我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准备为祖国的国防事业服务。信的内容很朴实,但是我却从中深深地体会到父亲的爱。

我写信有时比较认真,有时就马虎一点。有一次,因为我太马虎了,不仅有错别字,而且语句也不通顺。父亲收到这封信后,就用红笔把错别字和语句不通的地方画出来,寄回给我,让我改正后再寄给他看。
我那时从学校放假回家,背包一放,就先到父亲的书房去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听得很认真,还做记录。假期结束返校前,父亲还要和我作一次长谈,反复叮嘱。
父亲常常和我分享他的学习心得。他曾经说起他当初留学的经历:“刚到苏联的军事学院时,我连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可是到了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一般学员都好。”他说他的诀窍只有两个字——刻苦。
父亲早就立下规定: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他多次告诫我们:“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我刚结婚时,和我爱人两个人就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小平房里,那房子又矮又潮。
一些跟随父亲多年的同志都是看着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会上给他提意见,说:“首长太不近人情,子女结婚是大事,在家中暂住一下都不让,太过分了吧。”
父亲微笑着摆了摆手,说:“我的住房是国家给我的,供我学习、办公之用,孩子成人之后,就是社会的一员。他们再住我的房子,就情理不通了,那只能说是靠我这个父亲,才有房子住。试问老百姓能行吗?什么叫特殊?这么办就叫特殊。”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两国边境局势紧张。东北地区的战备工作时时让父亲牵挂于心。年逾古稀的父亲一路北上,到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考察边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情况,在25天当中,他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考察了10个县市。
不幸的是,在结束这次视察活动的返京途中,父亲的左眼病情加重,眼压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返京,入住北京医院。从此以后,他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却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1965年,父亲的左眼完全失明。他的右眼早在1916年讨伐袁世凯的战斗中受伤失明。父亲这一生为了中国的光明而征战沙场,现在他的生活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父亲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他还对医生说: “医生,我对你要求不高,你给我拿个放大镜,我只要能看地图,将来打起仗来,我给参谋部出个主意就行。”这就是父亲的敬业精神。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天天听广播的父亲忧心忡忡,他对这场运动完全不理解。年底,他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政治运动,打倒一切··唉,太行啊,我看你就别去参加这个运动啦。”
不久,掌权的“文革新贵”要把大批科技人员送到农场劳动,美其名曰“防修反修,走光辉的五七道路”,我也在名单上。我不想去,父亲说:“还是去吧,劳动锻炼也是件好事。”
于是,我成了苏北洪泽湖部队农场的一名普通的“军农战士”,这一干就是一年零十个月。之后,正好空军缺技术员,我又被调到了空军部队当机械师。可是,林彪“九一三”事件让局势更为动荡,空军面临大整顿。
1971年10月上旬,我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信笺上是妈妈的手迹,只有六个字:“家里一切安好。”我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文化大革命”让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他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让秘书把报纸和文件读给他听,还常常让我到各个学校去看大字报。我回家告诉他看到的内容之后,他只是锁着眉头,默默沉思。那段时间,父亲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父亲一直想念着老区的人民,特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河北涉县的老百姓。一想到他们,老人家的心中依然充满阳光。只要是我出差,无论去哪儿,回来后他都会问: “涉县情况怎么样?庄稼长得如何?不知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好不好?”
父亲从来不让做寿,组织上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同意;问他生日日期他也不说。直到他晚年卧病在床,家里人才为他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在父亲生日那天,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牛肉面。对父亲来说,这已经很隆重了。
我的儿子出生时,父亲已年近八旬。听到长孙降生的喜讯,老人家非常高兴。父亲对这个小孙子一样严格要求,不允许一点特殊化。孩子在普通幼儿园长大,在普通学校读书,口袋里揣着公交月票,脖子上挂着家里的钥匙。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七中全会肯定了包括父亲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功勋,还发表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这是对父亲革命的一生,对他卓越功勋和军事才能的高度肯定。
1986年10月7日, 94岁高龄的父亲因病与世长辞。10月14日是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1500 多人前来为父亲送行,现场哭声一片。徐向前元帅以诗寄托对父亲的哀思,一句“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写尽了人民群众心底的悲痛和对父亲最诚挚的怀念。
1986年10月21日,我和四妹、小弟遵照父亲的遗嘱,把父亲的骨灰分别洒到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和开县赵家场的黄桷树林。父亲在他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长眠了,与他所挚爱的热土永不分离,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