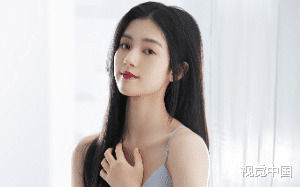夫君范衡的外室葛月烟挺着孕肚找上门,逼我自请下堂。
范衡却不愿意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妄想娶平妻。
我直接将他扫地出门。
外出办公差时,却不甚和葛月烟的表弟一夜荒唐。
从此牵扯不清。
她恶劣地嘲笑我被她表弟玩弄了身子。
1
夫君的朱砂痣葛月烟从外埠回了长安城。
她登堂入室,告诉我他们曾经如何两厢情悦。
她说她和我的夫君是青梅竹马,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替身。
现在她回来了,希望我能成全他们,不要自私地霸占一个不爱我的人。
我觉得她说得挺对,谁愿意做别人的替身呢。
于是我很好说话地开始着手与夫君和离的事宜。
为了感谢葛月烟救我出水火,我亲自向亲朋好友们解释。
并给众人派发了他们即将大婚的喜帖,让大家如期来参加夫君的婚宴。
而且我还在婚礼当日给他们准备了些礼物:“月烟妹妹,由于我们初成婚时便约定过,彼此会珍惜这段姻缘,不得纳妾养外室。如今他言而无信在先,那么除了他的坐骑和些许现银,其余我们名下的地契、宅子、庄子、铺子,他都主动放弃了。”
我笑的和善,“你们成亲后大抵得住在你那处,毕竟他是我们赵府的上门女婿,我不便继续留他住我的府邸。”
我不厌其烦,“最后,这个是前阵子府医给范衡日常请平安脉时开的方子。没什么大碍,就是肝疾而已,应当不妨碍你肚子里的孩子。”
看到葛月烟惨白的脸色,我心里格外舒坦。
2
我叫赵宛瑜,夫君范衡曾是我父亲麾下一名近卫。
父亲战死沙场后,我悲痛欲绝。
他带回父亲遗物,贴心安慰我,并向我提亲。
我答应了他。
算是他趁虚而入吧。
不然我一个将军府嫡女,怎会下嫁给一个侍卫。
现如今我们已经成婚五载,感情一直还不错。
范衡待我甚好,主动跟我发誓此生绝无二心。
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日常讨我欢心,帮我撑起偌大的将军府。
从不给除我以外的女子任何眼神。
饮酒后也不外宿,所有行程皆会跟我仔细报备。
连同僚送的西域艳姬也不收。
我不甚小产,他也毫无怨言,细心服侍左右。
还会帮我在婆母面前粉饰。
我曾为得此真情而庆幸。
所以,在听到葛月烟说她已有孕时,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那个让她有孕的男人,确实是我的夫君范衡。
我并不识得葛月烟,也不晓得她是夫君的心上人。
如果不是她主动找上我,炫耀她和范衡以往的甜蜜情事,我还一直蒙在鼓里。
因为他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即将要同我和离,与心上人破镜重圆的迹象。
那么,他这是要违反自己的誓言,想左右逢源啊。
我花了几日时间,弄明白了他们之间的事。
他们两家曾是邻居,到了年龄后,两人情窦初开,彼此许下终身。
但范父死后,范家门庭冷落。
本就不高的门第彻底衰败。
葛月烟没有和他终成眷属,而是嫁到了外埠。
由此,他们之前的许诺便不了了之。
各自婚嫁。
几个月前,成了年轻寡妇的葛月烟回来长安城。
她开始勾搭昔日情郎,也就是我的夫君。
于是两人很快纠缠到一起。
一个背着我偷情,一个没羞没臊地当外室。
也就是说,这段时日他那些所谓的外出办公差和去军营,其实都是在和葛月烟通奸。
重续属于他们的前缘。
坦言说,我是极不服气的。
毕竟范衡平时也表现得很是爱我,又要仰仗将军府的权势。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如此背信弃义。
若他平日的柔情蜜意皆是假的,只能说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戏子!
与骗我成婚无异。
如今想来,无非是贪恋将军府的门第,想走个捷径,从而飞上枝头。
我的心情极不好,倒不是有多留恋这个人,就是感觉被当作傻子般耍弄了。
愤怒大于伤心。
但看到府医给我的范衡那张药方,我的心情便没那么差了。
3
下晌,我去了郊外军营,见了几位副将。
刚回府,便在门外看到葛月烟,“赵宛瑜,我求你放过阿衡好不好?”
她声音哽咽,像是被我欺负了一般。
“我晓得我们这样不对,可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而且我现在有了身孕,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是个外室子。”她哭得情真意切。
外室子的身份连庶子都不如。
听到她变了路数,开始伏低做小,我的心情瞬间开怀。
前几日她趾高气昂找到我的时候,是何种姿态来着?
呵,那时她傲慢地扬着下巴,以胜利者的姿态挑衅我、鄙夷我。
她说:“赵宛瑜,你就是我的替身!当年我们年轻气盛,各自都不愿低头,若不是家父把我嫁去外埠,我们才不会分开。如今我不再是人妇,阿衡马上便和我旧情复燃了,你还是自请下堂吧。”
我气结,“你以为你是谁,你想让我们和离我就要和离?”
她嗤笑,“我劝你识相点,主动把位置让出来,莫到时被阿衡休弃,还得当个令人耻笑的弃妇,成为长安城的笑话。”
那时她多目中无人啊。
此时此刻,我抑制着怒意。
云淡风轻道:“可是阿衡还没有休弃我,你说这是为何呢?你当初可是很威风的呀,说假以时日他准会同我和离。但你瞧瞧,他到如今什么也没同我说,只说明日要带我去游湖玩乐。”
葛月烟那边哭唧唧的声音顿住。
她装不下去道:“贱女人!你如此死缠烂打有意义吗?!你明知我们相爱,明知他是出于对你父亲的敬重,才不忍直接同你提出和离!”
她言词激烈,“你是将门之后,若是真有你父亲那样的风骨,知晓此事以后,便应该主动同他提和离!”
我忍着心里的膈应故意说:“葛氏,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不舍得同我和离?男子嘛,无论在外面怎样偷嘴,皆是过场而已,终归是不敢宠妾灭妻的。”
“只可惜了你这样的无名外室,无论怎么筹谋,就是得不到正室的位置,连个妾都不如。永远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上不得台面!”
“赵宛瑜!”她怒吼,“你骂谁是老鼠呢!”
我不屑一笑,“当然谁败坏道德,就骂谁,比如你。”
“你!”她尖叫撒泼,“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妇!夫君心里根本没有你,你还死皮赖脸不放手,你可真是卑贱!”
“不如等你把孩子生出来以后,咱们问问你那孩儿,你我到底谁贱?”我咬牙切齿。
我眯眼冷哼,“问问他,是你这个丧夫后不安于室,出来勾缠有妇之夫的人贱,还是我这个受害之人贱!”
她抚着腹部,“你休要提我的孩儿!”
她骂一通污言秽语,“你自己不能给阿衡生孩子,还不允许我生吗?!你这个歹毒的恶妇,居然妄想算计我的孩子,你不得好死!”
我冷笑,“我可不会算计你的孩子,我巴不得你生个外室子呢,分明是你想利用孩子离间我们。”
葛月烟咬牙切齿。
碍于门口有侍卫,才没扑过来与我撕扯,“赵宛瑜,你这个不得夫心的贱妇,把男人当私有物,专横地像个母大虫!善妒是七出之罪,你莫得意,阿衡早晚会休了你!”
我们就在大门外。
门里门外的人都听到了她的脏污之词,也见识了她的无耻行径。
府里的侍卫、下人和走过的路人,个个目瞪口呆。
皆是惊讶地看着我们。
我理了理衣襟,抬步入府。
把无耻娼妇关在门外。
“众等继续做自己的事吧,莫被外人扰乱。”我保持着当家主母的风范。
将军府自我父亲战死后,其实已不再如往日那样权势滔天。
我虽也自小习武,但成亲后便主动安于后宅。
范衡在我的帮扶下,现已成为三品荣远将军。
并接管了将军府的府兵。
其中大部分将士都是曾跟随在父亲左右的。
郊外大营的那些副将,也都与父亲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
可以说,若不是范衡娶了我,那些人根本不会效命于他。
这辈子他拼死也得不到现在的地位和荣耀。
让他们都听听范衡通奸的事,届时赶他出门时,形势于我有利。
既然他不仁,莫怪我不义。
非我霸道善妒,当初是他主动立誓对我忠贞不渝的。
4
到了夜间,他还没回来。
我令一府卫给他传话,把今日发生的事告知他。
既然他装死,我便把事情挑开。
莫耽搁他喜迎外室子,也莫耽搁我脱离人渣。
岂能任那个小人为所欲为,妄享齐人之福。
他把将军府的脸面置于何处?
约莫一小时辰后,范衡骑马急匆匆赶回来。
我坐在软榻上看着沙漏,快子时了。
他一进来就撩袍蹲在我面前,捉着我的手,“对不住宛瑜,我未想到她会找上你。”
我嗤笑,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他满脸忏悔道:“宛瑜,你莫难过,我一定会处理好,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恶心地抽回手,“是么,你想如何处理?”
“我……”他似有口难言。
“好为难,舍不得你的心上人是吗?”我想了想包里那张药方才压下怒意。
也许这就是天意。
如果他没有背叛我,我看到那张药方可能会难过。
现在我只觉得解气,恶有恶报。
我面色从容,“非我独断专行,容不得她,当初是你一再发誓此生绝不纳妾养外室,只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不然我也不会嫁你,也不会同意你入赘。”
他重新抓住我的手,把脸埋在我手里,“宛瑜,我那时候心里积郁甚重,每日忙于公务军务。不小心一时晃神,便铸成大错。但我和她说过,不会同你和离的。”
我听得瞠目结舌,无语至极。
按他说这意思,还真打算一直左拥右抱,享齐人之福来着。
哪里来的脸啊。
既要这,又要那,还厚颜无耻为自己开脱。
他怎么不看看他算个什么东西!
同样支撑着将军府,就他满腹积郁。
我每日忙里忙外,为他屈于后宅,我说什么了吗?
有积郁就得通过与旧情人通奸排解?
无耻小人!
我压下愤怒,讥笑开口,“恭喜你啊,要当爹爹了。”
“宛瑜,别这样。”他愁眉苦脸。
“有人助你步步高升,有人乖乖给你生孩子,范衡,你可真是贪得无厌。”我皮笑肉不笑
范衡急切解释,“孩子是意外,我们就那一次……”
我站起身,轻叹一声,“范衡,就此和离吧,以后桥归桥路归路。”
“宛瑜!”他拉住我,“我错了,你原谅我可好?我不想同你和离。”
我回头直视他,“那你是打算迷途知返,和她恩断义绝?”
他噎住,“她现在已有孕快三个月了,此时落胎对身子不好,往后便不能生养了。而且孩子是无辜的,我做不到对她们那样绝情。”
我直接气笑了。
他做不到绝情,合着我才是那绝情之人。
不想同我和离,也不想和葛月烟一刀两断。
他这是不隐藏了,想明目张胆一妻一妾依红偎翠。
舍弃不了将军府给他的权势,也舍不得旧相好,就我是个多余的。
“范衡。”我叹笑,“你咋不上天呢!”
不过,很快他就快上天了,上西天。
5
当晚我直接搬去厢房,和那种脏人同榻而眠太恶心。
我怕我直接吐在床上。
本朝男人纳妾司空见惯,除了驸马,但凡有些权势或富贵的男人都妻妾成群。
葛月烟说我专横,的确,在此事上我确实眼里容不下沙子。
范衡当初就知道这点,所以才会提亲时发誓此生只有我一人。
可葛月烟就大方宽容吗?
她想要的绝不是给范衡做妾室,屈于我之下。
她想要的是正室之位,是将军夫人的名头。
那么,即便我宽容大度同意把她纳进门,与我共侍一夫,她也不会满足的。
而范衡就更卑鄙了,他什么都想要。
笑话,我堂堂功臣之后,岂能任他们践踏尊严。
接下来,我和几个家将商议过后,准备和离事宜。
我把和离书摆在范衡面前。
他是赘婿,没有什么私产,就连这平步青云得到的军职也是仰仗将军府。
我能分给他的也就是一些现银。
谁让他忘恩负义在先呢。
他红着眼睛注视我,一副深情不渝的德性,“宛瑜,我们不和离好不好,的确是我对不住你,但是我爱你。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尽力把她和孩子的事情处理好。”
我心里鄙夷,表情则故作伤痛,“所以,你到底想怎么处理?”
我不至于有洁癖,但他确实脏了,确实恶心。
我才不会捡别人用过的腌臜货。
他小心翼翼开口,“先让她生下孩子再说好不好?毕竟孩子没有错。”
又是这样,呵呵。
他们都没错,那是我有错?
世界上怎么有这样恬不知耻之人!
他和葛月烟真是绝配,当初做什么要分开,出来祸害别人呢。
我轻蔑一笑,“然后呢范衡,说来说去你还是想家里一个,外面一个,然后称心如意地一妻一妾?”
我冷漠眯眼,“你不会异想天开认为我会愿意把她给你抬进门吧?你还记得这是镇国将军府吗?还记得自己是入赘的吗?还记得你那可笑的誓言吗?”
“还是说,你打算到时候把孩子抱回来,让我给你们养孩子,然后把一个外室子名正言顺当作将军府嫡子?”我语调尖锐。
他愣住,再说不出一句话。
显然是我猜中了他的心思。
他是觉得自己太能耐了,还是觉得我好哄骗啊。
我磨着后槽牙,“范衡,做人不能太无耻自私,做事之前也要先设身处地换个角度想想。人有脸树有皮,树若无皮,必死无疑。”
我就好心提醒到这了,不枉夫妻一场。
他垂着头,抹一把脸,就是不松口和离。
见他那个死样子,我琢磨着他是不是不甘心放弃将军府这个大树,以及府里的钱财。
左右不可能是真爱我、真舍不得我,才不肯按手印。
不甘心他也得放弃。
我已为他蹉跎好几年,不多为自己筹谋,我还不甘心呢!
利用将军府和我扶摇直上,从一个无名侍卫成为三品将军。
他得到的够多了。
而我得到的只有他的背叛,还有他那旧情人的辱骂。
越想越气,他已经踩着我的肩膀拥有荣华富贵。
竟还不满足。
那我也不会让他轻易好过,必然要他也受些折磨。
眯眼转了转心神,我在眼里硬挤出几滴泪花。
轻叹一声,“我先去灶上给你做些可口的饭菜,你慢慢想吧。”
6
晚膳依然摆满了桌案,皆是他平时爱吃的。
我们面对面坐着用饭,没用下人布菜。
我给他夹了他喜欢吃的炙羊肉,虚情假意道:“多吃些,我亲自看着火候的。”
初成亲那段时间,为了能让他尽快得到将士们的认可,在军中立威。
我时常陪他出入军营,与将士们同吃同宿。
他怕我不惯,偶尔会亲手给我烤羊肉吃。
我嫌他火候掌控的不好,不是半生不熟,就是烤得太柴。
于是自己动手烤,他吃后连声称赞鲜美多汁。
后来,我也会在府里给他做。
眼下同样的人,同样的饭菜,却丝毫没有往日的情意。
范衡吃着吃着,忽然眼眶泛红,“宛瑜,我对不住你,我不能没有你,我不和离。”
让他怀念过往的好,增加他的负罪感,这才是我的目的。
我暗暗勾唇,范衡某些弱点是可以利用起来的。
谁说女人就得心软,就得乖乖被男人哄骗?
一连几日,我都在他面前表现得贤淑温婉。
日常出入我也故意不抹妆、不拾掇自己,脸上挂着郁郁寡欢的面容。
整个人看着憔悴得不行,典型的下堂弃妇形容。
于是,府里府外的口风一边倒地倾斜向我。
被视作负心汉的范衡心虚不已,在闲言碎语的包围中愈发无法专心做事。
公务和军务皆频频出错。
他的上峰和手底下的将士都对他颇有微词。
这夜,上榻睡觉前,范衡来厢房搂住我。
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想和我行房。
笑话,瞧见他我都膈应得想吐,鬼才会和他同床共枕做那种事。
我暗掐一把自己的手臂。
泪眼里含着一个柔弱妻子盼望着丈夫回头是岸的希冀,“阿衡,你想和我做正常夫妻,是代表你愿意放弃葛月烟和她肚里的孩子了吗?”
闻言,他眼里的热情顿时散去。
他不敢正视我的眼睛,“宛瑜,我和你说过,孩子是无辜的,那也是一个生命,我不能那样做。”
在他眼里葛月烟和孩子都是无辜的,唯独我活该被他们合起来欺辱。
他不想放弃孩子,那就去生他的外室子啊。
还得寸进尺不想和离,想让孩子做正室嫡子。
这种自诩有责任心的狗男人,多活一个都是祸害。
这时,下人领着一个丫鬟过来。
是葛月烟身边的人。
一进来就跪地哭求,“将军,您快去看看我们娘子吧!”
范衡神情略变,下意识看我一眼。
在我“凄楚”的目光注视下,他咬了咬牙道:“时候晚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你回去好生伺候着。”
范衡这几日都老老实实府里和军营两边跑,没去过旁的地方。
那么,一直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葛月烟必然是急了。
那丫鬟继续痛哭流涕,“将军,您这几日没去看望娘子,她伤心欲绝,亦格外惦念您,吃不好睡不好,人瘦了许多。您就随奴婢过去看看她吧!”
这番哭诉,声音像是在安静的屋子里投下一颗火雷。
我默默垂眸。
“我……”范衡欲言又止,左右为难。
我也捂住脸,抹眼睛,抖着肩膀。
狗男人压低声音,“巧叶,我现在有事,你带话回去,就说我过几日再去看她和孩子。”
听出他在逃避,巧叶连忙哀求道:“将军,我们娘子肚子不舒服!您知道的,大夫本就说过娘子此胎凶险,若整日郁结在心,随时会滑胎!”
她抽抽搭搭,“将军,娘子眼下极为难受,说是腹部抽疼,她担心孩子,这才令奴婢连夜过来寻您,您快过去帮她请个大夫瞧瞧吧。”
明眼人都能听出来她们主仆是故意这样演的,在用孩子的安危威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