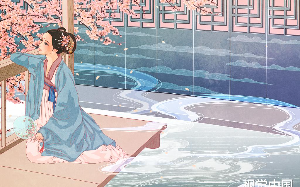我是个穿来的粗使丫头,被大夫人指给少爷做了通房,
少爷终年苦读,腼腆纯情,风光霁月,像极了帮我脱离苦海的救世主。
我使些手段便爬了床,
他迷上了,今天要,明天也要。
我拿着他赏我的金银细软,刚做上丫鬟变主母的美梦。
隔天他就对我的身体腻味,寻了个更放得开的新丫鬟替了我榻上的位子。
我才明白他不是天定的男主,他是男人,是主子,而我不过是最卑贱的奴婢,随意打死发卖了
和猫儿狗儿也没什么两样。
……
1
我名桃红,她叫柳绿,都是通房丫头,就连名字都是大夫人一道赐的。
少爷的床榻不大,整个院子里的丫头都盯着,妄图爬床做个主子。
昨天我勾了少爷的身,今日就有比我更卖力的上位。
夜里少爷捧着春宫图,想要全试一遍。
我含糊推脱,得了一句寡淡无味的评价。
今日的柳绿便化身成了妩媚动人的妖怪,引导少爷登上极乐云梯。
从我这角度望去,只看到散在地上的衣物。
我看得心口发涩,可又能怪得了谁呢。
是了,得怪我那没心肝的爹娘。
一穿来便是穷苦家里的幼女,没有金手指、系统,更没有梦中的预言,有的只是一对敲骨吸髓的爹娘。
娘生了个女儿,爹立马盘算着能卖几两银子,前头两个姐姐一个进了窑子,一个送到八十富商家里做妾。
我侥幸活到了八岁,能走能跳。
刚跑出村子三里路,便被逮了回去,打了半死。
我九岁那年,大哥要娶媳妇,爹盘算着卖了家里的驴子和我。
他拉着我和驴子,走了几十里,舍不得草料,硬生生将驴子饿瘦了几斤。
到了府前,管家不愿要奔波疲倦的驴子。
爹急了,大手一挥将我推到前。
“俺这女娃也一道给你,吃得少,干活最卖力。”
“大人可怜可怜俺,家里男娃要娶媳妇哩。”
女娃是财产,男娃是壮丁。
我跪在地上,朝爹重重嗑了头。
今年娘又生了个妹妹,求爹莫要再将她卖进来了。
爹没理我,反而捧着五两银子,笑得皱纹堆到一块。
他庆幸,没真将我打死,还破了管事的刁难。
进了府后,我只能做粗使丫头,冬日冻疮夏日中暑。
终于熬到了及笄后两年,大夫人听闻我娘三十出头生了五个娃,将我纳到了通房里。
少爷模样生得好,终日苦读,称得上风光霁月四字。
我心里泛起了波澜,若是攀上了少爷做了姨娘,便能算得上半个主子。
不用生冻疮,不用被打骂,更不会被整夜罚跪。
姨娘一月月钱三两银子,送回家,那爹娘也不会再卖了妹妹。
于是我心一横,起了一个勾了少爷苦读的心。
内屋的榻上动静未停,少爷不知看到了什么,拿着图册直皱眉。
然后眼一横,望向门口。
“桃红,你也进来。”
我愣了下,反应过来后骨头缝里都在泛着寒意。
过去和柳绿一道脱了衣服承宠吗?
我摸了摸心口,到底卖不了灵魂,找个借口便低下了头。
我不去,有的是丫头去。
后面的鹅黄挤开我,扑到少爷床上。
木塌被压得吱呀作响,我的眼睛泛酸,犹疑地一瞥。
胃部猛地翻腾。
我再也忍不住,呕了出来。
2
那日后,少爷偏爱鹅黄柳绿。
她们放得开,能想法子哄少爷开心,院子里有丫鬟开始学她们的法子,也去献宠。
只有我躲得远远的,悔恨将少爷看成了真命天子,早早将身子交了出去。
可不承宠,通房便没了用处。
旁人不做的重活脏活全落到了我身上。
鹅黄和柳绿被新丫头追得紧,使了银子向窑子里的姑娘学手段。
为了做上姨娘,斗得头破血流。
还没分出胜负,就捅到了大夫人面前。
大户人家生怕沾上了窑子的风尘气,要打死她们。
大雨倾盆,沾血的板子将她们的后腰上打着,几下便晕死过去。
我看得心惊,头一次见自己的命放在了脑后。
淋着雨,冲到大夫人面前为她们求情。
“大夫人,她们已经知错了,您就饶过她们一命,哪怕是卖出府也好。”
我一下下地嗑着脑袋,染红了面前的石板。
大夫人冷笑声,让小厮将我一道处理了。
那重得能打死人的板子落在腰上是要断了的痛。
在我意识渐渐模糊,以为要就此命归黄泉时,翁嬷嬷替我求了情。
我捡回一条命,而她们两人丢到了乱葬岗。
大夫人敲山震虎,好好警告了次少爷,让他用功读书,成家立业。
少爷表面装得跟白兔似的,白天捧着圣贤书念着之乎者也,夜里又央着我陪他上塌。
我半推半就地允了。
毕竟如今我的银子和未来全系在他身上了。
夜里,少爷就搂着我的肩,念鹅黄柳绿的好,恼母亲随意打杀他院里的丫头。
这话说了没几天,我就没机会上他的塌了。
刚入夜,少爷便只让奶娘进门,其余丫鬟仆役全都离得远远的,莫要干扰他考功名。
大夫人叹少爷终于转性,揩着眼角让翁嬷嬷送来糕点。
只有我紧皱着眉心,想起白日里奶娘腿脚虚浮,腰根发软的模样。
少爷宠何人我不在乎。
可若被发现,奶娘必死无疑,而为了避人耳目我怕是也会被一道打死。
我憎恶少爷是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又叹息自己只是个小小的通房。
贱籍奴身,跑不了,只能在府里一日日熬着。
就在我期盼着他们小心些,莫要被发现时,少爷患了风寒。
大夫人让奶娘多看顾着少爷,莫要过于操劳。
奶娘双颊泛红地应了。
可夜里大夫人被噩梦匆匆惊醒,让人去看看少爷的门窗可有关紧。
动静要小些,莫要干扰少爷读书。
东窗事发,大夫人气得当夜围了院子,将奶娘五花大绑,当着少爷的面施以鞭刑。
可怜奶娘身上还带着交欢留下的痕迹,几鞭下去就翻出了血肉。
少爷看得害怕,想跑却被大夫人捉回来,让他亲眼瞧着。
我吓得满脸是泪,躲在角落,看着被火光围着的奶娘。
从脑袋到脚底,没剩一块好肉。
少爷吐了好几遍,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后来的几年,少爷见到嬷嬷便恶心作呕,想起那夜被打得没人形的奶娘。
大夫人雷厉风行治好了少爷的毛病。
我将当初少爷给的赏赐拿出来,求管事给奶娘买了一口薄棺,将她的尸首葬在了风景优美的京郊。
夜里我悄悄给奶娘烧纸钱,终于后知后觉。
少爷不是男主,是主子。
他踏错一步,丢的是下人的命。
哪怕他烂到了根底,也有这偌大的家族为他兜底,将他伪装矫正成正人君子。
而我是猫,是狗,是畜生,唯独不是人。
3
风波过去后,少爷不知是怕了,还是倦了。
每日要么读书,要么逗弄我和大夫人新拨过来的通房白雪,瞧着是走上了正道。
新来的白雪明显是被敲打过的,整日板着脸,话一句也不多说。
少爷常看着她娇俏的脸,主动挑起话题,却没个回应,最终讪讪将目光丢向我。
几次过去,我和少爷的关系倒是亲近了许多。
除了榻上的关系,白天竟能打趣些闲话。
我站在桌前,伺候着他用笔墨。
他说什么,我就敷衍着应着。
直到他随口说了句大夫人正给他相看姑娘。
我一惊,墨渍溅脏了干净的纸张,他也不恼,洋洋得意地说那几家姑娘出身高,相貌好,又是京中一等一的才女。
可大夫人全都瞧不上,要为他选个最好的。
我嗓音颤颤,问出了声。
“那少爷可有中意的?”
他屏息想了会,道:“模样都不错,可惜却都是古板守礼的,哪里有我房里的丫头讨人喜欢。”
他又啧了声,埋怨着大夫人为何这么早要让他成家。
我没心思再听,整张脸惨白着回了房。
没穿成闺阁小姐,没有系统,更没有预言金手指,
我成了古言小说的炮灰丫鬟,身子搭给了风流浪子,等新夫人进门,这条命也要没了。
我捏紧掌心,将攒了几年的积蓄全掏了出来,请了翁嬷嬷吃了顿好酒。
酒色醇厚,嬷嬷的脸也慢慢涨红,结巴着说些主子的闲话。
我没心思听老爷的风流韵事,慢慢诱着她说了少爷的婚配。
少爷再混不吝,也有大夫人的母族和老爷相帮,再加上相貌生得不错,在京城还是块抢手的热饽饽。
这几日,大夫人从上见到了郡主女儿,下到朝中有实权的尚书。
随便挑一个都是良配。
我又问那我们这些通房丫鬟怎么办,翁嬷嬷咽下嗓子里的酒,嗤笑出声。
“挑两个乖的留下,其余全发卖出去,可不能让新夫人笑话。”
我急了,攥紧翁嬷嬷的袖口问:“那我呢,大夫人可说过什么?”
她不说话了,踉跄着站起身离开。
我苦笑着,擦干眼角淌出的泪。
没想到领先了几千年的我到了这里,连活命都困难。
房里的白雪倒是坦然,似乎去留对她来说完全无所谓。
我瘫软身子躺下,问她不怕被卖出府没有生路吗。
她声音淡淡,只说大夫人给了她救命钱,帮她爹娘度过难关,命早就不是她自己的了。
白雪也是家里穷困被卖进府的,爹娘与我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她却仍存了孝敬的心思。
我哑然,以往可能会嘲笑她愚忠蠢笨,可现在却羡慕她什么都不用想,将灵魂交给旁人就好。
几日光阴过去,院子里的丫头都知道少爷将要婚配,个个想着做姨娘。
熄了的心思又活络起来。
这个端了些鹿血酒,那个学以往鹅黄柳绿的老路子。
少爷被哄得迷晕了眼,躺在女人身上忘了要考取功名,成家立业。
头一次,我起了向主子邀功的心思,以翁嬷嬷为引线到了夫人面前。
将这几日院子里的荒唐情况和盘托出,话里全是为着少爷身体和府邸名声考虑。
又道若是夫人进府后,一下处理了整院的丫鬟到底不雅,不如现在赶到外院做粗活,也算是能保住她们的性命。
夫人沉默,沉默到我的腿都在发抖。
终于她抬抬手,翁嬷嬷给了我赏钱。
我拿着赏钱,惴惴不安回了院子。
作乱献媚的丫头们已经被绑了起来,管事让人记下她们的名字,新夫人进门前全部赶到了外院做粗活。
我挤出笑,将赏钱全塞给管事。
“少爷的婚贴已经定了?”
他睨我眼,慢悠悠开了口。
“定了,朝中林大员家里的长女,是个厉害的,以后啊,缩紧脑袋过日子吧。”
我颤颤巍巍躬身应着。
交换庚帖前,那位贵女亲自来了趟少爷的内宅。
丫鬟仆役全围着,争相讨好未来的主母。
贵女身旁的嬷嬷眼一扫,却全都是大夫人姿色平平的丫头,嘴角扬了起来。
“听说未来姑爷房里有不少丫头,有哪些是被少爷开过脸的?”
有想冒尖的立刻谄媚上前。
“只剩下桃红和白雪了,白雪姐姐是大夫人特意派来的,那桃红是前半年爬床上来的……”
她适时地闭上了嘴。
闻此,嬷嬷不说话了,而是躬着腰站回了原位。
贵女轻笑着,端起香茶饮了一小口,“爬床?那就是魅主的玩意儿,我嫁进来之前便仗杀了吧。”
她的话轻飘飘,就像随意处置小猫小狗似的,帮我定了我的命。
4
我进去奉茶的脚一顿,浑身涌上一阵阵冷汗,差点踉跄着跌倒地上。
可几瞬后,我平缓着起伏的胸口,故作无事般去了少爷的书房。
因着男女大防,少爷一人在书房里避着。
我喘了口气,颤着手端茶,隐约露出了雪白的肌肤。
一推开门,我便倒在地上,双目泪水莹莹地仰头望向少爷。
他立刻丢下手中的圣贤书,哑着声问我发生了何事。
我哭得梨花带雨,手却不经意碰着他。
“少爷,有人要杀我!奴婢是您的人,您救救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