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 有一个专节讨论盛唐诗、边塞诗, 题为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s。所谓the High Tang, 就是“盛唐”;所谓Poetry of the Frontiers, 就是“边塞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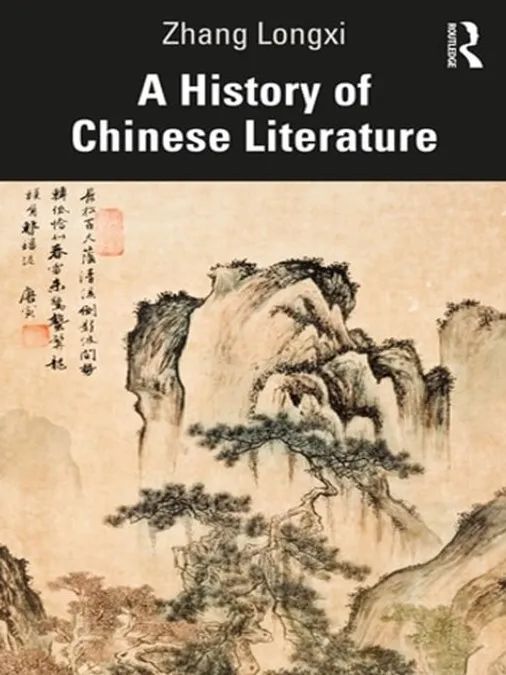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1904─1977)为盛唐诗归纳出“王孟”“高岑”两大派,这样“分成两大派”后来几乎成为唐代文学史论述的定式。说白了, 就是史书中唐代这一段多数跟着说盛唐有此两大派。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曾被易名为《中国文学发达史》在台湾印行,那么,台湾的文学史书有没有受到刘大杰的“分派”所影响?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中,哪些诗人属于“边塞诗派”?哪些诗人属于“山水诗派”? 有一位盛唐诗人出过塞,他笔下的一些边塞诗享负盛名,却不属于“边塞诗派”。他就是王维(701—761)。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怎样论王维、山水诗?

《宋刻本王摩诘文集》
“边塞诗派”的遗珠——王维
王维出色的边塞诗在许多文学史书中不怎么受重视。为什么?唐朝“边塞诗派”的门槛,很高吗?王维不够资格成为“边塞诗派”的一员?
美国学者Victor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说:Wang Wei and Meng Hao-jan are often,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yoked together as exemplars ofa schoolof nature poetry, so Kao Shih and Ts’en Shen are usually considered the leading pair of T’ang “frontier” poets. (p.296) 王维和孟浩然被归为同类,入于“山水诗派”。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这可能是王维边塞诗被史家忽略的原因之一,因为史家的目光大多聚焦于王维的山水诗,到讨论边塞诗时,则惯性谈高适和岑参等人,很少把王维边塞诗当一回事。 “高岑”、“王孟”对举,“边塞诗派”与“山水诗派”对举,这格局在近七十年的文学史书中相当固定。然而,王维只有山水诗值得史家关注吗?
近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1949年分别出版上下册,后来又有上、中、下三卷本)使用“王孟诗派”、“岑高诗派”这样的标签。“岑高”指岑参、高适,而“王孟诗派”在刘大杰书中又称为“田园诗派”、“自然诗派”。
也许,“标签”这词略有贬义,那么,我们说成是“标榜”也无不可,因为只有文学地位够高的诗人才得以位列于盛唐两诗派之中,得到史家的标榜。
刘大杰之前的文学史是什么情况,有待查考,然而《中国文学发展史》应该是影响力较大的著作,所以我们先聚焦于此书。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认为,“王孟诗派”的诗篇是静的是退守的,后者(高岑一派)是动的是进取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 刘大杰这论点有商榷的馀地。笔者在下文将举实例呈现刘说的不妥。
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立门派”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二十世纪中叶出齐上下两册,这本书中的“诗派”名称,对后来者有影响。
据说,台湾省实施戒严令时期,台湾中华书局曾将《中国文学发展史》改名为《中国文学发达史》印行。
台湾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之中有“自然派”之名 ( 文稿源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台静农讲授文学史之时。1946年以后,台静农在台大授课,二十余年间,不断增补修订)。
台静农说:“被公认为自然派诗人之祖,生活于公元五世纪的陶渊明,受老庄的影响多而佛教的影响少;八世纪中的自然派诗人巨擘王维,却受佛教的影响多而老庄的影响少。王维虽是唐一代自然派风格诗人的巨擘,却不是这派诗人最早的作家,因为早于王维的是隋末唐初的王绩……”(下册,第四章第一节)。后来,有学者上溯到东晋陶渊明为此自然派之始祖。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
台静农笔下的“自然派”与刘大杰笔下的“自然诗派”没有什么大分别(当然, 刘大杰认为自然诗派也是浪漫诗)。谁率先使用“自然派”?待考。
有了这个“(自然诗派的)旗帜”,就可以将更多的诗人拨归“自然派”的“麾下”:例如,隋之前的陶潜、隋唐间的王绩。后来,台湾叶庆炳《中国文学史》的“自然派”还包括柳宗元、储光羲、刘长卿 (页358)。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一书另有“边塞诗派”这名称 (1997:350)。也许叶庆炳参考过刘大杰“王孟诗派”而立“边塞诗派”之名?

叶庆炳《中国文学史》
不少文学史著作沿用“边塞诗派”之称,例如: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28) 有“边塞诗派”之名。此外,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隋唐五代》(1998:76)也有“边塞诗派”。
到了二十一世纪,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撰稿者只说“边塞诗”,似乎刻意弃用“边塞诗派”之名。
台湾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称盛唐有“两股潮流特别引人瞩目”,分别是“山水田园之吟咏”“边塞军旅之讴歌”(第五编第四章第三节)。王国璎在标题上避用前人所拟的诗派名称,实际上,我们仍然能在《中国文学史新讲》内文中看到“王、孟诗派”(页447)。

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三册本
笔者认为,文学史家代作家“立派”,方以类聚,这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如果“立派”后的论述和评析落入固定的框架,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之弊。这一要紧处,下文会举实例再加剖析。
文学史家有“立门派”、“命名”之权?
陶渊明属于“田园诗派”这类说法(陈怡良《田园诗派宗师:陶渊明探新》里仁书局, 2006年),原非陶渊明自认的,陶渊明没有说自己“开了宗,立了派”。
另有文学史家立“山水诗派”,以谢灵运、谢眺为先驱人物。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现“田园山水诗派”这名称。
山水田园诗人之间关系如何?诗人之间曾经聚会发布写作主张?似乎没有。“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和名称从何处来?山水田园诗人何曾提出共同的文学纲领?
既然没有共同议定的主张,何来“诗派”?这类问题,文学史家没有详细解说。他们往往只按现存诗篇的题材来进行分类。

《山水有清音:古代山水田园诗鉴要》
由“田园派”而“山水派”,由“山水田园派”而“自然诗派”,外延越来越寛,都是唐代以后的学者在“操作”(manipulation)。
文学史家的权力就体现在“分类”“指派门派”上。这里是指史家自我赋权(empowerment),将一些作家归为同类同派并加以命名(Hope A. Olson, The Power to Name: Locating the Limits of Subject Representation in Libraries.Springer,2002)。
实际上,不大可能每本文学史著作都“创立”一些新的“门派”,因为传统的文学史论述对后来者可能产生一定的“压力”,先行者形同典范,后来者在压力下倾向于因袭前称,或者据前称稍加调整,例如: 将“山水田园诗派”调整成“山水园林诗派”。

The Power to Name Locating the Limits of Subject. Springer
新撰的历史书多袭用旧称,这就造成史学上的“层累”效果,副作用是进一步巩固了前人定立的派别名称。
“层累”效果见于何处?
上一节,笔者提到刘大杰的文学发展史在1948年写成(1949年初出版下册),后来,台湾叶庆炳撰写的文学史也有“边塞诗派”“自然诗派”,这可能是取前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高岑诗派”、“王孟诗派”再进一步扩大外延而成(特指“立诗派”方面)。
近七十年,“边塞诗派”“水山田园诗派”渐成中国文学史书中的常见环节。这也是芸芸文学史书写同质化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
有些文学史书中的用词(门派名称)虽然更新了,实际内涵仍然脱不了传统之说,例如: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使用“隐逸诗人群体”为标题,名虽有异,实际上内文仍是不离王、孟等诗人。 中国文学史家代作家立“门派”的现象并不罕见,而“立门派”所隐含的“不安因素”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岑参其实写了不少山水诗,但是,许多文学史书只当岑参是边塞诗人,罕见史家在讨论山水诗时提及岑参,也甚少史家讨论岑参的山水诗(台湾的叶庆炳实属例外,他简略谈及岑参山水诗。参看叶庆炳其书1997年版,第十六讲,页361)。
又如,孟浩然热衷于功名,与王维晚年的心态不同,但是二人仍被大多数史家判定为同属“山水派”。问题是:如果偏重注视王孟二人多写外景所以二人同归一派,那么,此派的好手何止王、孟?
史家“代立门派”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利的一面是:史家容易集中做叙述。弊的方面是:诗人因被拨归某“诗派”而忽略了另一些成就。

宋刻本《孟浩然诗集》
王维的边塞名篇
现在我们集中谈谈王维。不少史家只在文学史书的“山水诗派”部分讨论王维诗篇,忽略了王维也写过很出色的边塞诗。 王维晚年居于蓝田辋川,有诗集名为《辋川集》(也收录裴迪的诗作),其笔下《鹿柴》《竹里馆》《辛夷坞》皆为名作。这只是他晚年的事。
其实,在李林甫执政时期 (大致是从734年到752年),王维曾出任凉州河西节度使的节度判官,他边塞题材的诗篇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当然,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写边塞相关的诗。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是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创作的,后来有乐人谱曲(《渭城曲》),被称为“阳关三叠”。“三叠”或是需要叠唱之意,也可能是曲段的重奏。无论如何,现今还流传“阳关三叠”的琴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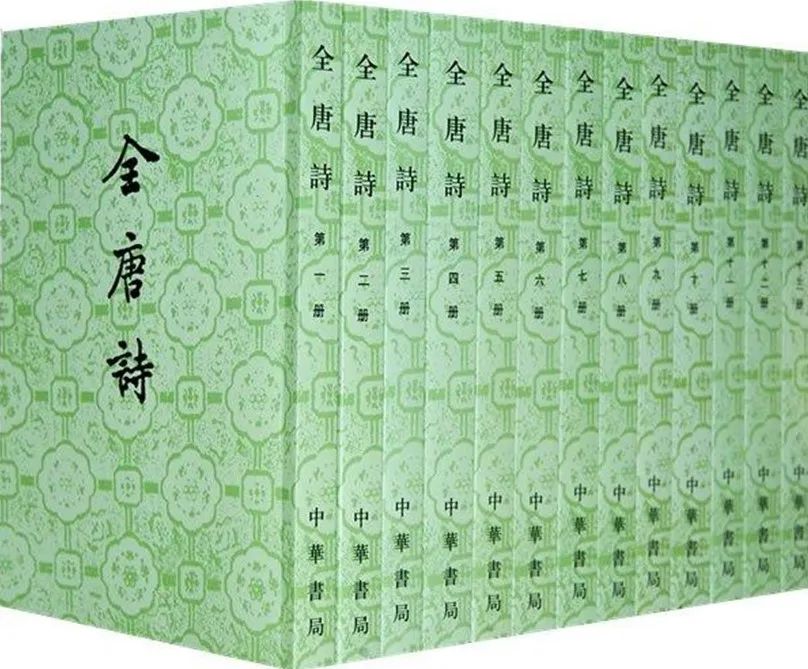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1960年版。
诗的全文如下: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全唐诗》卷128)
若问:王维真的算是边塞诗人?王维未曾自称是边寒诗人。王维归入何派,端视由谁来评断。
今人刘冬颖选注《边塞诗》(中华书局,2015年) ,有六首王维诗入选,比王之涣(1首)、李颀(2首)、高适(5首)入选诗篇还要多,足见王维边塞诗在刘冬颖眼中佳作不少――不少于边塞诗的名家高适 。

刘冬颖选注《边塞诗》,中华书局2015年版。
王维入选的诗篇除了《送元二使安西》,还有《陇西行》《少年行》《陇头吟》《老将行》《使至塞上》。
《送元二使安西》不属于“闺情”类,但是,它的内容呈现边塞诗常见的“家乡(内地)”、“边塞”二元对立:“渭城”代表内地,“阳关”代表边塞。“阳关”和“玉门关”“阴山”“楼兰”等地名在边塞诗中的作用似乎是相近的。 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之西南方,为古代通西域的要道。实际上,唐朝的边疆远超过阳关,包括了今天的新疆和一部分中亚地区。所以,虽然阳关是一个重要的边防关隘,但是它不是唐朝边疆的最外围。“阳关”象征国境。
也许会有人质疑:元二只是出使,出使与边塞战事未必有关,因此,这首诗未必属于边塞诗。 关键在于: 诗题中的“安西”当指“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640年设置于高昌(吐鲁番),648年移至龟兹(治所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主要守备天山山脉南侧的丝绸之路,防备突厥、吐蕃等势力。岑参的《过碛》写道:“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岑参诗笺注》
此外,中晚唐诗人张籍(约767—约830年)的《凉州词》也写“安西”:
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
应驮白练到安西。
(《安西与北庭》页405)
同样是写“安西”,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得到的评价明显较高,例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王摩诘诗集》卷七第一页有眉批:“更万首绝句,亦无复近,古今第一矣!頋云:后人所谓阳关三叠,名下不虚。”绝句中的“古今第一”,名下无虚,到今日许多人还能背诵出此诗。
王维的“闺怨-边塞诗”
王维《王右丞集》卷十五录有“《闺人赠远》五首”,其中第二首所表达的意念近于王昌龄的《闺怨》。

《王维集校注》
王维《闺怨》如下:
远戍功名薄,
幽闺年貌伤。
妆成对春树,
不语泪千行。
(《全唐诗》卷一)
闺人赠远的“赠”,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所写的夫妻发送书信是同一回事,只是王维单写妇人这一方如何如何,不写的远方征人怎样回应(关于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请读者参看2024年2月23日刊发在古代小说网上的《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新文类)?》一文)。从“幽闺年貌伤”这句我们知道那女子感到日久年深,自己的容貌变得苍老。

《王昌龄诗集》
“不语泪千行”不像王昌龄《闺怨》写“悔教夫婿”那般直白,而伤心凄惶之情或有过之,例如:她焦虑、伤心到说不出话来。 “不语泪千行”没有道出“不语”的原因,但是,首句“远戍功名薄”反映:女人的夫婿应该是追求功名而“远戍”,留下女人独守空闺独对春色。她能对谁诉苦?
“妆成对春树”五字,抵得上王昌龄“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这两行。此外,王维《闺人赠远》第一首:
花明绮陌春,
柳拂御沟新。为报辽阳客,
流芳不待人。

《王维诗集》
这首诗的女主角和“辽阳客”应该是情侣,二人可能还没有成婚。她为了这段感情而等待“辽阳客”回乡和她共谐连理,可是,她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她感到“流芳不待人”:自己在等待中老去,年纪不小了,也许已经过了适婚的年龄……
晚唐卢汝弼(?-921年)也写过类似《闺人赠远》的诗。卢汝弼的《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第一首:
春风昨夜到榆关,
故国烟花想已残。
少妇不知归不得,
朝朝应上望夫山。
(《全唐诗》卷七)
此诗内容和前面王维《闺人赠远》第一首相近,都是写思妇盼望征人回家,只是卢汝弼笔下的女主角似乎已经嫁人,所以她更加没有选择,只能天天到望夫山上眺望,盼能看到夫婿。

《王维诗集笺注》
这种从女方着手的写法和男性边塞诗的刚健豪迈不同。细腻的女性心理世界另有动人之处。
史家“贴标签”的幕后真相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书之中,唐代部分大多有“山水诗派”和“边塞诗派”的章节。刘大杰说这两派一静一动,又将二派统统归于“浪漫诗”(《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
这真是“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174)。刘大杰这说法(山水诗、边塞诗不同,却同为浪漫诗),激发我们对文学史“分派”问题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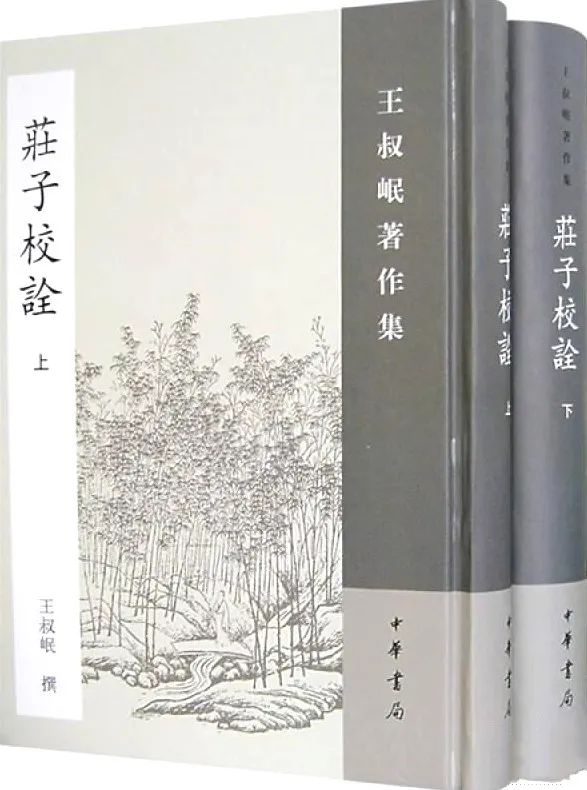
《庄子校诠》
刘大杰“浪漫诗”之说,值得商榷。
岑参、高适同属“边塞诗派”,然而,文评家向来有“岑超高实”之说。清末刘熙载《艺概‧诗概》说:“高常侍(高适曾任散骑常侍)、岑嘉州(岑参曾任嘉州剌史),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杜甫〕。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61。)
所谓“高实”,应该是指高适诗的内容、风格比较踏实。这“高实”之评和刘大杰所谓“浪漫”没有矛盾吗?
接着,我们看看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情况如何。 在张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之中,王维被放入书中Nature and Landscape: Wang Wei and Meng Haoran一节之中。Nature and Landscape实即“自然山水”诗,相当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王孟诗派”。

《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
我们拿张教授所拟标题Nature and Landscape(盛唐标题)和东晋时期标题 Tao Qian, the Poet of Nature andCountry Life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东晋之Country Life,在唐则为Landscape。
读者看了Nature and Landscape这标题,很可能得到以下印象: 唐朝的Poetry of Country Life 式微了,没有诗人像陶渊明那样写村野田家风貌,所以,Country Life 让位给Poetry of Landscape (唐代的新流派)。
然而,台湾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却表示她看到唐朝诗有Country Life (村郊、城外、郊野),她说:“爰及李唐王朝……恬澹自适的田园诗,焕发出前所未有吸引力……”(页446)。王国璎还举实例证明王维诗“洋溢着村野处安祥宁静的生活气息”。此外,储光羲有《田家杂兴》八首和《田家即事》诸作(页447)。储光羲的诗篇,题目已经标明“田家”。
据王国璎所陈史实,若有人说唐代的Poetry of Country Life已式微,能说得通吗?恐怕是说不通的。那么,为什么Country Life在张教授论唐诗部分却消失了?

《王维资料汇编》
我们看一个实例:储光羲有田家之诗引人注目。储光羲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属于“王孟诗派”,在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属于“自然派”。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了储光羲二十一首诗,都是描写田园风光的。此外,《诗籔》内编卷二对储光羲有评语:“储光羲闲婉真至,农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 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37 )。这评价实在不低:储光羲不输王维和孟浩然。因此,若说储光羲的田园诗略有名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此外,唐代有些诗人反映了“田家苦”,例如:柳宗元写了《田家》三首﹔高适有《苦雨寄房四昆季》(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页287-288)。这改变了先前山水田园诗派的基本旨趣。

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 使用 Nature and Landscape 这标题,就不能涵盖唐诗中的田家之诗、“田家苦”诗篇。 换言之,田园诗人储光羲被史书摒弃于史书外,因为史家重视的唐诗是Nature and Landscape方面的,而不是 Nature and Country Life。史家是主宰。
文学史书的“显・隐”功能
无论如何,史家一旦使用“标签”或者落入“非此即彼”的框架之中,就有机会被标签和论述的框架所囿而有所不见 (blindness),例如,唐朝的Poetry of Country Life在张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之中就不获表述。 我们只需转换立足点,便即察觉史家所用标签完全有可能被史家所描述的对象所颠覆(deconstructed),例如,“边塞派”的岑参其实写了不少山水诗;“山水派”王维其实写了不少边塞诗。又如,和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高适,笔下山园诗甚多(参看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页43)。

《许渊冲译王维诗选》
或问:高适怎可能是属于“山水田园诗派”?读者如果有这疑问,可能已受史书之惑。请读者参看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八章,第282-288页)。相对于山水诗,高适的田园诗数量更多。
总之,唐朝诗人中,没有人自称属于“边塞诗派”、“自然诗派”。史家自行将诗人分派、在史书中“贴标签”,这样做能突出作家的诗歌特点,但是,分派论述须提防“标签”附带着遮蔽性。
对比史书先后章节,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习见的标题(分类名称)在后文被摒弃,改换成新的标题,原因是史家自己有所不见(blindness),或者选择有所不见。 比较前后出版的史书,我们会发现前人的论述影响到后来者,当然有些后来者会尝试挣脱旧说的制肘。不过,上文已经讨论到:后来者纵有“命名之权”,但是,要真正做到有“立派之实”,是有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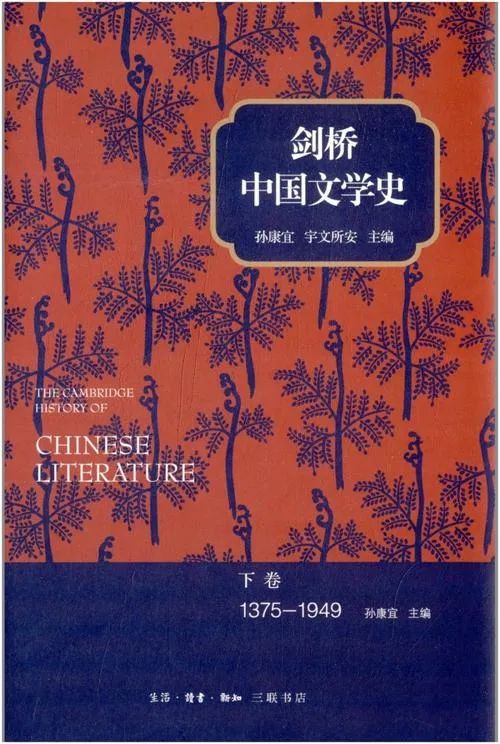
《剑桥中国文学史》
也许,这就是文学史书写的吸引力所在:史家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有制肘。
今日的史家如果要为唐朝文学史创立“怀古诗派”或者“咏史诗派”,其可行性是存在的,好比近人――主要是欧、美、港、台的学者――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抒情传统论”主要流通于大陆之外的论域,特别是台湾。这是当事人自己在文章中承认的。另参2024年2月11日,古代小说网上《屈原创造narrative and verse的混合体? 何为“名理前的视境”?》一文)。
“抒情传统”的“传统”,实际上是历时性的承传,与历史其实没有多大分别。这“传统”何时开始?有人说是始于七十年代(陈世骧),有人将“始祖”上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从效果看,文学史家掌握了“命名权”,再配以解说、论述,往往就能决定大部分被动读者(passive readers)之“所见”、“何所见”( Thomas W. McCormick, Theories of Reading in Dialogue, p.158),同时,分门别派之后,因为对作家有所删汰,这就方便了史家阐述自己首肯的文学观、阐述自己青睐的文学现象,刘大杰“浪漫诗”之论就是个值得研究的案例。笔者将另外写一篇文章来探讨。

Theories of Reading in Dialogue. UP of America
话说回来,我们读者读了某部文学史书后若要了解自己是否“有所不见”、被史家瞒过,我们可以怎样做?
读者可以先了解史家所用“标签”是怎样产生的,“标签”的外延和内涵为何、内涵有何历时变化……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王摩诘诗集》
在信息化社会,知识共享更加便利,因此,史家掌握较多史料的日子已成过去,因此,史家的权威受到冲击。笔者相信,当今史家的权威再难像刘大杰著书 (《中国文学发展史》) 时那般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