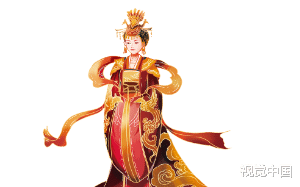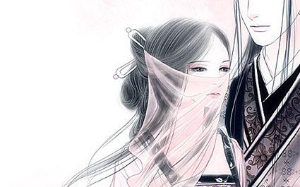新婚三日夫君就重病而亡。
公爹强迫我委身于他。
无妨。
反正最后哭的是他。

1
“尔尔,尔尔......”男人厚重的喘息声与酒味弥漫了我的感官,我就像条死鱼一般被翻过来覆过去,他宽厚的手掌一直牢牢锁在我的腰间,让我无力挣脱。
“你醒了。”一声冷漠的男音将我从昨晚不堪的回忆中拉出,随即又拉进另一个更加难堪的局面。
请问和夫君的父亲荒唐一夜后,如何优雅又不失体面的和他事后问候?
“爹爹,我...”
不得不说宋朝对公公的称呼,在这种情境下这么喊也太“刺激”了。
“昨晚是我喝醉了酒,对不住你。”李循直接把话抢了去,翻身下床,将地上散落的衣服捡起,去屏风后将衣服穿好。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全身不着丝缕,刚才说话的片刻就已经将大半胸脯露在被子外了。
怪不得李循那么迫不及待的下了床,这会儿倒是装起君子来了,在床上像个草莽汉子一样粗鲁下流。
我裹着被子小心翼翼地去够地上的襦裙,东扯西扯好不容易穿好,便看见屏风后一抹高大、压迫感十足的影子矗立在那。
难不成在等我穿好衣服?
“爹爹,我好了。”听到我的声音,屏风后的身影动一下,缓步走了出来。
不论这个恶劣的酒后失德行径,我这个爹爹长得属实是芝兰玉树,虽说现在已是而立之年,岁月却没给他留下风霜,反而打磨得更加迷人。
久居高位,宦海沉浮数十载,权力使他身上更有年轻男子所没有的执掌风云的魄力。
也许是我眼花,我似乎看见他手上捏着个白色丝绸样的物件。
李循许是见我直勾勾盯着他看,皱着眉头移开了眼。
冷咳一声,“牧之与你新婚不出三日便重病英年早逝。你虽是不详,我李家却也是乌衣门第,无论世人如何非议,你都是我尚书府的长媳。”
他停顿了会,我在心里思索着他这一番似是而非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难道是想说我这般不祥之人他都大发慈悲收留我了,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我还是尚书府的长媳?
我自以为领悟到了他的话外之音,心一狠,直接笔直地跪在地。弯下腰,行跪拜之礼。
“爹爹,儿媳自知罪孽深重,官人自离儿媳而去后,儿媳便痛不欲生。还好有爹爹怜悯,让儿媳忝居尚书府。儿媳愿为官人守节,日日与青灯古佛相伴,为爹爹、阿家祈福。”
我低着头,却始终不见李循回应。
“哼,你有如此深情与决心,真是好极。倒是牧之没有这个福气与你相伴了。”说完他便甩袖大步离开。
2
我唤来巧碧打水,一身黏黏腻腻,一想到那个恶心的男人昨晚舔来舔去就反胃。
巧碧是温尔娘家带来的陪嫁丫鬟,目前观察来看,还算是个嘴严懂事的。昨晚李循来我院子的动静不小,虽已夜深,还是怕丫鬟小子们听到了些许。
想到这我就头疼,这个朝代理学盛行,对妇女的贞洁桎梏更是前所未闻。
荒唐的是,这种近乎变态的压抑欲望的世态还是李循一手促成的。
真该让世人看看高风亮节的李尚书背后是怎样的一个人渣,不过在他身败名裂之前我可能就先被沉猪笼了。
我恨恨地将皂角在身体上使劲揉搓,不搓下一层皮誓不罢休。
来来回回洗了两遍,我才感觉干净点。刚走出去,就看见巧碧慌张地跑进来。
“小姐,刚才大人派小厮来说,让您为大少爷守节,在佛堂带发修行,不得出院门半步。”
正合我意。
“无妨,巧碧。无人打扰到也是清净自在。”
巧碧恭敬地低下头。
温尔是江南一带的巨贾独女,自从我来了这,黄花大闺女背上了克夫名声还被逼守节就罢了,更可恨还有个畜生公公。
虽然不知道温尔去哪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一定会好好地活着,有机会定会替温尔尽孝的,温尔,你放心吧。
银月高悬,万里无云。
我刚洗漱完,屋后的花儿都绽放了,我便打开了后窗,想着闻着花香入睡倒也是雅事一件。躺在云锦被子之中,我很快就进入梦乡。
“来人啊,来人啊,救命啊...”突然一阵嘈杂的尖叫声将我吵醒。还不待我反应过来,我的房门就被从外强力踹开。急匆匆的脚步声渐行渐近,直至到我床前。
“温尔,温尔?”我强睁开眼,居然是李循。
他身上披着外袍,松松垮垮地用一根丝带系着。脸色极其的难看,黑沉沉地能挤出墨水来。他一手撑在床边,一手抓住我的肩膀。眼睛黑黢黢的,目光如炬,神情复杂。
“爹爹,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我怯怯地问道。
李循没说话,只冷冰冰地盯着我看。看的我手指都要把这云锦扣烂了,他才终于舍得开尊口。
“无事,你好好休息吧。”说完便转身要离开。经过后窗时,顿了顿,又提脚离去。
看见他的背影离开我的视线,我松了口气。
这时巧碧推门进来了,端了碗安神汤。“夫人,大人说您今晚受惊了,命我煮碗安神汤给您。安神汤既安神还能驱寒呢,看来大人心中还是当您是儿媳的。”
我端过汤药一饮而尽。
可不是吗,喝醉了酒还能上儿媳的床呢。
“夫人,夜间天凉,我帮您把窗户关上吧。”
“巧碧,外面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似乎听见有人喊救命了。”
“夫人,您是不知道,可凶险了。大人半夜遇袭,有一个刺客闯入了书房。”看着巧碧惊魂未定的样子,怪不得李循刚才脸色那么恐怖,像丢了什么珍宝似的。
看来这世上还是有有识之士的,看清了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也不知道李循是做了什么缺德事被人记恨。
抱着一种微妙的好心情,我再次沉入梦乡,半睡半醒间,我突然想到,李循遇袭,那他来我这干嘛?
3
一觉醒来,我便接到尚书夫人的召见。她平日深居简出,日日吃斋念佛,与李循都很少见面,更别提主动见我了。
穿过层层叠叠的小门,绕过七八个弯,才到了正院。
这正院本是李循与大夫人同住的,后来李牧之去世后,李循便搬出了正院,一人住在书房。
“见过少夫人。”行礼的是大夫人身边的大丫鬟红苕。我记得她,新婚第一天,我向大夫人敬茶的时候就是她将大夫人的见面礼端给我的。
“红苕姐姐快请起。”红苕不卑不亢地起身,领着我进屋。一进屋,便看见大夫人端坐在上座,慢悠悠地抿着杯盏中的茶。
“温尔给阿家请安。”屋内静悄悄的,只余杯盏碰撞的脆响。
“昨日刺客逃走了,听说是朝你院子那逃的,可有受惊啊?”可能是我的错觉,总感觉她话里有话。
“谢阿家关心,托阿家的福,温尔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呵,到底是贱商出生,上不得台面的贱人。你还妄想一切都好!”
尚书夫人将手中杯盏猛的砸向我,我还未反应过来,红色的液体就从额头流入了眼睛。
我不知她为何突然发难,巧碧被拦在外面,一屋子满脸横肉的婆子虎视眈眈,看来是早有预谋。
“不知温尔做错了什么惹的阿家如此动怒,都是温尔的不是。”
居于人下,敌强我弱,我只能低声下气地先示弱。
“克死我儿,不守妇道,勾引公爹,你这个不得好死的荡妇。给我将她捆起来,立刻沉河!”
一贯不苟言笑的尚书夫人面目扭曲得如同一副怪异的画作,眼中不含半点温度,一双眼充满了戾气,活像要把我撕碎的厉鬼。
五大三粗的老婆子们直接将我摁在地上,一块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拿出来的脏抹布塞进了我的嘴中。我拼命挣扎,内心绝望至极,明明我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这么对我…
“住手!”
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这两个字,如同奄奄一息的荒漠行者眼中突现一大片绿洲,心中燃起希望的同时也担心是否是命运的玩弄。
我勉强看见一双银白色的靴子在我面前停住,随即压在我身上的女人被踢到一旁。
我被那人腾空抱起,与他雷厉风行的行为不同的是他轻柔的力度,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我的伤口,如视珍宝。
我竭力抬头想看清他的脸。
那人如幽黑潭水般的眼睛透着刺骨的危险讯息,薄唇抿成一条细线,紧绷着一张清俊的脸,眼尾却泛着嫣红。
“你怎么敢!”
4
是李循。
他来救我了。
“窦氏,我看你是得失心疯了。念在你生育有功,对你网开一面。从今日起不准踏出正院半步。”李循从始至终都不曾正眼看过他名义上的大夫人。
“哈哈哈,哈哈哈…生育有功,好一个生育有功。我和牧之不过是两个可怜虫罢了。我被你利用了半辈子,就连我儿的出生都是你算计好的。你可是一个父亲啊,你是牧之的父亲啊李循!”
窦氏泪流满面,死死地盯着李循,癫狂的像要扑上来生啃了他。
“是你上门求娶我,我本以为觅得良婿,谁知道是掉进了深坑!李循,午夜梦回,你难道不怕牧之向你索命吗?”
“疯子。”
李循紧紧地抱着我走出门,不顾背后的嘶吼咒骂。
“你才是疯子,李循,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你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她都不爱你,你才是真正的可怜虫。我诅咒你生生世世爱而不得,血流而死!”
听见此言,李循脚步顿了一下,很快又毫不迟疑地离去。
我扭头眺望,她眼流血泪,跌跌撞撞地追了出来。
但她很快又被门外的侍卫拦下,重重的摔倒在地。
李循将我一路抱回了我的院子,把我放在房内的软卧上后便直接出去了。
巧碧红着眼睛,哭哭啼啼地闯了进来。想伸手触摸我,却又不敢的样子让我不禁发笑。
笑着笑着,眼泪却不听话的流了下来。
“巧碧,我还以为要看不见你了。”
“小姐……”
我们相视着落泪,我握着巧碧的手,只感叹命运多舛,让我们两个苦命人相遇在这个朝代,让我们相依为命。
一个老年男子的出现打断了我们主仆的依依相惜。
他是府上的郎中,从宫中退下后便留在尚书府负责李循的日常诊脉。
他帮我处理好伤口便出去了。
我看见他站在门外,时大时小的人声不断从门外传进来。他像是在给谁嘱咐什么。
门外安静了。
一个身影站在门外迟迟没有进门,踌躇片刻后,还是转身离开了。
我此时心乱如麻,从前对李循纯粹的厌恶中又掺杂了些许感激,但尚书夫人的那番话字字泣血,很难让人不动容。
历史上的圣人,尚书夫人口中的可怜鬼,我眼前的李循,三者交织在一起,围成一个巨大的网,将我团团困住,不得脱身。
5
我在院子中静养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李循没来过一次,但日日会派府医查看我的情况,珍贵药材也似流水般源源不尽。
我本以为尚书夫人被软禁,李循也不来打扰我,我能和巧碧安稳地度过接下来的几十年。
一件事又将我推向了李循。
温尔的母亲病重了。
我收到了温家哥哥的信。信上说母亲病重,寻遍了民间名医也无用,想让我请李循进宫请御医救命。
母亲病重,我自然是义不容辞。可一想到要去见李循,我心中就说不清的怪异。
“巧碧,大人可回来了?”
“夫人,下面来人说大人已经在路上了。您坐下歇歇吧,您都已经走了三圈了,您不累,巧碧看着都眼花了。”
“可是...欸,算了再等等吧。”
一盏茶后,李循终于回来了。
我带着巧碧来到书房。透过婆娑的竹影,通过微弱的灯光,我看见李循坐在书桌前,不知端详着什么。
“少夫人。”这一声将我从思绪中拉回现实。
“您是要请见大人吗?”
“啊,是啊,对。”我在心中给自己鼓劲,没事的,他又不吃人。但又想到那晚他吃人般的眼神,他不吃人这个结论似乎也要待定。
我一进去,刚好撞见李循将一件帕子式的东西塞进第一个抽屉中。
见我进来,李循又皱了皱眉毛,一脸不耐烦的样子。看的我就来气,但想到他之前毕竟救了我,便又忍耐下来。
“温尔见过爹爹。”
“你过来,可有要事?”我抬头看了眼李循,他一直把玩着手中的玉件,漫不经心。
“爹爹,我娘家来信说母亲病重,想劳烦您请御医救治。”感到李循似乎抬了下头,我怕他拒绝便赶忙说,“本不想麻烦您的,实在是遍寻民间名医都没用,才求到您这了。温尔拜谢爹爹。” “起来吧,你母亲病重,当女儿的是该心急。”李循高高在上的话让我猜不透他的想法。
“爹爹,自打温尔嫁入尚书府便再未见过父亲母亲。出嫁前,母亲总说,嫁作人妇就要做好人妇的本分,侍奉双亲,寻常人家如此,在尚书府更当谨慎。
爹爹您是天下读书人的表率,温尔更是不敢放肆。温尔每每见您和阿家都会想起父亲母亲,如今母亲病重,生为女儿却无法侍奉在旁,温尔,温尔实在是羞愧。”
本是做戏,说着说着眼眶却湿润了。我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我走后他们如何了。
“行了,这件事情我知道了,退下吧。”李循说完便拿起手旁的书看起来。
“温尔告退。”我慢慢走出书房。
我不知道我那晚的话哪里触怒了李循,他将我彻底关禁闭了,还命我日日夜夜为长辈抄经祈福,送给他检查。
也不知道母亲怎么样了,看着慢慢鬼画符的经书,我的耐心逐渐被耗光了。
“夫人,大人说抄经要心与手一体,您也要诚心祈福。最后这几章,请您重抄。”
这句话,在这短短两周内,我已经听了不下三遍了。
我不想再忍下去了。
将桌上的经书一扫而光,我猛地站起身,“巧碧,你去跟他说,我要见他。”
我气鼓鼓地坐在茶桌旁等着巧碧回来。
却等来了位不速之客。
6
“你要见我。”
李循怎么亲自来了?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大人,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母亲病重,您不愿帮忙就直说,何必消遣我。”我怒视着李循。
“现在不叫我爹爹了?”李循不怒反笑,将身逼近,“在床上也一声声爹爹,我还以为你对牧之多情深意重呢,如今叫什么大人?”
他疯了吗?居然说这种话!
“我很清醒,我从未如此清醒过。尔尔,我就算是疯了,也是你逼疯的。我明明已经准备放过你了,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李循一步步逼近我,直到我退到抵在屏风上。
他的一条腿刚好抵在我的双腿间,他不怀好意地将弯曲着的腿慢慢伸直,他的大腿甚至都快靠到我的私处了。我闻到他身上有阵阵兰花香,真是个人模狗样的伪君子。
我用手撑在我们俩之间,“您冷静一点,不能一错再错了。我自认一向是守规矩的,不知道是何处冒犯了您,我跟您道歉。” 李循用行动告诉我这句话他一点都不爱听。
他直接亲了上来,我抿紧了嘴唇,不愿让他得逞。他耐心十足的地在我的唇上辗转舔舐,一手抓住我的手,不顾我的挣扎,强硬的将五指插入我的手掌,与我十指相扣。另一手也没有闲着,在我身上摸索,时不时捏两把。
“尔尔,你说过你爱我的,小骗子。”正当我还在回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他的时候,一股清凉从身下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