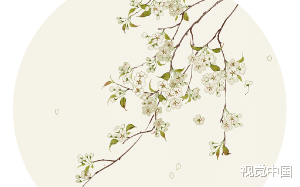我代嫡姐出嫁、替兄长出征。
爹娘害怕我将秘密抖漏,一杯毒酒要了我的性命。
后来嫡姐嫁我夫君有孕,兄长带兵立功升官,爹娘大办喜宴为一双儿女庆祝。
我的夫君却手执一杆长枪,挑翻了这场喜宴。
自此红事沦为白事。
1
裴珩渊携军打下胜仗,皇帝允他早日归家同妻儿享乐。
可三日前裴珩渊收到我重病已死的信,知道楚府中没有等待他的妻子,只有爹娘送给他替代我续弦的嫡姐江时荷。
我的魂魄飘在空中,看裴珩渊伫立着,迟迟未进府。
江时荷主动出府迎裴珩渊,羞涩环上他的腰,“夫君多日不见,怎还在府前发愣不进来,随妾身进来伺候你宽衣沐浴吧。”
江时荷与我不同,她妩媚风情更能讨男人欢心。
三日前,她在我快要死的时候对我说,“江漪,在战场上你确有本事让人诚服,可比起驯服男人,你到底是差得远了,多些时日我定能让裴珩渊忘记你、沦为我的裙下臣。”
江时荷势在必得,说的如同让我死去一样轻而易举。
她说我嫁给裴珩渊三年都没有一儿半女,可见裴珩渊对我并无多少情爱。
我想说自然是差得远了,裴珩渊定然不会拒绝她。
我看着江知荷为讨好裴珩渊,晚上特意换上薄如蝉翼的衣裙,满心欢喜给裴珩渊倒酒,只有孤男寡女的房里气氛旖旎。
哦,还有我。
我不甘心江时荷杀了我,还能如愿嫁给裴珩渊、让裴珩渊臣服于她。
裴珩渊发笑,目光如同审视,淡淡道,“江大小姐,我没下三书六聘娶你,你爹娘将你送来应是为我的妾室,你虽不如江漪,倒也勉强能入眼,那便学她的模样伺候我吧。”
裴珩渊这张嘴如同淬了毒似的,让我破天荒笑了。
我根本没正经学过女红妆艺,不懂怎么伺候裴珩渊,榻上的事好几回弄疼他,裴珩渊嫌弃说要休了我,说我根本不像女子,否则怎会各方面都奇差无比。
我明明死了恰好如他所愿。
只是,裴珩渊你如此嫌弃我,怎么叫起别人学我了?
江时荷美人计失败了,裴珩渊那些话无疑是羞辱她,她自小没受过这等委屈,转身回房发了好大一通的火气。
想了想,她疑虑道,“莫非裴珩渊当真喜欢上江漪了?不可能,娘同我说过裴珩渊出征前还与江漪争吵,又可是……他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怎会拒绝得了我?”
我嗤笑了一声。
笑她自作聪明,愚不可及。
寻常男子确实如她所言,可裴珩渊堂堂一国之首将,岂会受七情六欲牵绊。
裴珩渊接到我病死的消息已心生疑虑,他知道我身体康健,不信我是重病离世,便将我的贴身丫鬟小桃押来审讯。
小桃说我是从江府回来途中出事,同信件上说我是病重离世毫无关联。
裴珩渊用刑罚逼问出事情原本,所以,他没有直接拒绝江知荷的投怀送抱。
江知荷自作聪明,自顾自说着,“可笑!若不是事出有因,她一个庶女又怎能嫁给裴珩渊,还享受这些荣华富贵,如今一切不过是替我做嫁衣罢了,反倒要我学作她的模样!”
“若非是爹娘所致,她江漪本就不该嫁给裴珩渊,又怎会有这段孽缘。”
或许真如江时荷所言。
我与裴珩渊是孽缘吧。
2
这门婚事,原本要嫁给裴珩渊的,确实是江时荷。
可江时荷不愿嫁给裴珩渊,爹娘便说我自幼入军营同男人为伍的事,倘若事情一朝败露我被毁掉清誉,想寻到好婆家此生无望。
再严重些,若暴露被皇帝知晓,便是欺君之罪。
爹娘同我说,嫁给裴珩渊,我就不必再征战沙场,过食不果腹的日子。
可起初,我入军营就是怕被饿死。
我是小娘和爹一夜春风的代价,定是比不上大夫人和爹鹣鲽情深,不比嫡姐受关心重视,我和小娘被养在江府小小宅院里,冬日里挨冻夏日里受饥。
我病重时小娘抱着我哭,说我爹给嫡姐取名江时荷,寓意她为荷花般娇柔夺目,而我名为江漪,如同小娘的一滴泪砸进池塘,只能掀起小小涟漪。
可我不想如此简单的死去。
我亦不想只做荷花旁稍纵即逝的涟漪。
我入军营亦是想让爹娘看一眼我,关切我一句,他们却说我嫁给裴珩渊定能过上好日子,我又何尝不知,这是他们宠爱江时荷的谎言罢了。
如今爹娘亦是如此,仅是江时荷一句爱慕裴珩渊。
哪怕我已嫁给裴珩渊,就算让我死也无妨,因为我激不起爹娘心中一点点涟漪。
好在,这点涟漪像是拨动了裴珩渊的心。
自那夜过后,裴珩渊像疯魔般折磨江时荷。
他让裴时荷整日暴晒,只为与我肤色一致,让江时荷吃我喜欢的菜肴,不顾她吃完后浑身会起红疹,又会故意叫江时荷随军演练,说怕她同我一样身子弱,染病死了。
我从未发觉,楚珩渊将我的模样、喜好记得如此深刻。
江时荷承受不住,扑进裴珩渊怀里呜咽,“夫君,我不学她也能伺候好你的,我那妹妹没管束教养,如同乡野丫头,你让我学她岂不折辱我,不如让我死了罢!”
她以为裴珩渊对我是念旧,用些手段就能让裴珩渊对她痴迷。
可裴珩渊却轻笑,风轻云淡的说,“好啊,那你去死吧。”
江时荷颤巍巍抬眸,眼底闪过一瞬间恐惧。
裴珩渊捏着她的脸笑,“说笑罢了,江大小姐尊贵,你亲妹妹尸骨未寒便心生续弦之意,你莫不是忘了妾室到底不如正房,如今你说江漪是乡野丫头,那你又算什么?”
江时荷脸色一僵,旋即梨花带雨的哭,“裴郎你,你可知江漪她是染上花柳病死的!她趁你离家在京中寻欢作乐,我心疼你被蒙在鼓中,可你却这般待我。”
我被气笑了。
还花柳病,我看你跟花柳病似的。
江知荷为俘获裴珩渊当真是不择手段,可到底恨我不能辩解,裴珩渊虽知晓我不是病死,但我心中亦会担忧他听信江知荷的话。
裴珩渊却似笑非笑,讽刺她,“是么……这便是江大小姐自甘下贱为侍妾的缘由?”
江知荷本想挑拨离间,可惜裴珩渊油盐不进。
我活像是打赢胜仗的将领,我伏在裴珩渊耳边絮絮叨叨给他说谢谢,却又被自己给逗笑了,毕竟毕竟活人哪能听见死人说话。
可我却听见裴珩渊醉意失态,一遍又一遍唤我的名字。
我顿时不乐了。
我想告诉裴珩渊,我死的还挺惨。
可更惨的是,我死了才发觉裴珩渊对我有情。
我本是不敢信楚珩渊对我动心的,可裴珩渊是真真实实在帮我。
我想起洞房花烛夜时,我主动掀了红盖头坐在喜桌旁吃糕点,裴珩渊见此,盯着那块红盖头看了许久,我刚想问他那红盖头是不是寓意着什么。
裴珩渊却同我说,“你姐姐不肯嫁才让你替嫁,我想你定是不愿的,那这样相敬如宾尚可,倘若你日后有心仪男子想和离,我不会拦你。”
次日,嬷嬷收帕时未见落红,慌里慌张问我昨夜发生过什么。
我实话实说,嬷嬷却说我犯了裴家大忌。
裴珩渊祖上最信奉婚嫁仪式,江家替嫁这事本就让裴珩渊恼怒,昨夜新婚夜我还主动脱喜服掀盖头,让裴珩渊多是有些不悦。
那时我没来得及向裴珩渊解释,我是饿极了才如此。
像如今我再没机会对他说,我对他也是有情的。
3
江时荷不能忍受裴珩渊多番羞辱,回府将此事告知爹和大夫人,惹得大夫人心疼极了,用尽法子去哄她,还不忘将带我名字的小人使劲的扎。
我又多个被痛恨的理由,莫名有些委屈。
江时荷平复下来,冷哼,“裴珩渊定是恨我当初用替嫁羞辱他,如今三番五次故意拿妾室来羞辱我,可他到底是我看上的男人,想驯服他是要些时日的。”
起初,江时荷说裴珩渊家境落败,看不上他。
可当裴珩渊短短两年成为炙手可热的朝堂新贵,江知荷便又爱慕上了,她嘲讽地说裴珩渊根本不爱我,说定能取代我。
我想若是能取代我,她绝不会逃回江家的。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但大夫人总归是有头脑,派人传信叫裴珩渊来接江时荷,说切莫辱了江裴两家颜面。
可信送到好几日,裴珩渊都毫无动静。
江时荷坐不住了,她相府嫡女身份去续弦本就是笑话,有人将她回江府的事走漏风声。
外头人都说她是被裴珩渊嫌弃给送回去,说她是二嫁妇,京中达官显贵都不敢再娶。
江时荷在害怕。
我觉得可笑,她杀我的时候可是一点没手软。
可裴珩渊到底是来了,霞光万道,长街铺花,马车还镶着金边,小厮都站足了一条街。
江时荷站在府门前,得意的嘴角掩不住笑,若非是大夫人拉着她,恐早就花痴的跑过去了。
待裴珩渊行至府门前,大夫人高兴的笑道:“贤婿何必如此,和小女闹小别扭罢了,来接她如此派场可惹人笑话了!”
是啊,如此盛大的排场,也让我心中酸涩,我便飘过去暗中偷拧他的后腰。
可裴珩渊感受不到。
江时荷也跑了过来,花痴的咬着手指:“裴郎啊,你是来接我回府的对不对?”
而裴珩渊却没看她一眼,眼中寒意愈发深重,回答大夫人道:“是啊,我就同她闹了片刻别扭,代价却是再也见不到她,说来怎么不算可笑。”
“所以江夫人,我妻江漪的尸首在何处?”
此话一出,大夫人和江时荷皆是一脸尴尬,羞愧难当。
而我听见他的话先是怔了怔,接着笑了。
说来的确可笑,我同裴珩渊闹别扭,不过是他发现我一直在服药罢了。
裴珩渊知晓那药的作用后同我大吵了一架,问我为何不想要孩子,可大婚时我分明听见是裴珩渊说和我相敬如宾过日子的。
我寻思都相敬如宾都出来了,他居然还想要孩子。
我不甘落下风和他争吵不休,甚至一脚踹翻兵器架子大喊让他滚,裴珩渊眉头皱起,真就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
可裴珩渊,你明明是心悦我的。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江知荷同大夫人听到裴珩渊竟是来接我的,尴尬过后,脸色变得奇差无比。
见府外还被不少百姓围着看热闹,江时荷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去拉裴珩渊的手,目光期期艾艾看着他。
“裴郎啊,今日我们不提那个晦气的死人,我愿意同你一起回家。”
啪!
裴珩渊直接给了她一巴掌,冷道:“辱我亡妻,该打!”
接着,他又看向大夫人。
“江府送信说我妻江漪病亡,不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便来接她回家了,又有何不能提的,莫非江府是隐瞒什么了?”
我心下不知是何滋味。
江家不肯交出尸首是怕裴珩渊发现端倪,我亦是害怕裴珩渊被我尸首吓得彻夜不眠,毕竟死在战场已多时,尸首定腐烂不堪。
裴珩渊同大夫人剑拔弓弩之际,我爹回来了。
我爹交出我的尸首,恭送裴珩渊出府。
大夫人慌了神,问,“裴珩渊若发现江漪不是病死的,那可怎么办?”
我爹却是一脸从容,胜券在握。
我大抵能猜中尸首定不成人形了,我爹赌裴珩渊发现不了端倪。
而我,虽担忧裴珩渊会被吓到,可心中亦会缺憾没能让他看见完整的我。
我坐在裴珩渊为我备好的棺材上,算是跟他回家了。
而江知荷此刻还捂着脸,楚楚可怜的愣在一边,不敢动。
裴珩渊却转头,意味不明笑道,“时荷是不愿同我回府么,江大人将你送于我,那我定然不能抛弃你,时荷也不愿听外头风言风语的吧。”
“时荷不想江大人因你,在朝政上受同僚议论对么?”
4
那具尸首的确是我,可却看不出摸样了。
算算日子约莫有半月了,我恰好死在严寒的北疆,尸身还没完全腐败,可我那亲爹心狠手辣,连我死了也不肯罢休。
脸上皮肉外翻血肉模糊,身上没有一处好的,空荡荡的衣袖被风吹得荡起,露出里面又断又残的手脚来,好似都能闻见腐败血腥交杂的气味。
可我知道,死前我顶多是被插了几剑罢了。
如今这副模样,大抵是我爹怕被裴珩渊看出死因,又虐尸导致的吧。
裴珩渊淡然替我换上与他成亲的喜服,我不解他为何要这般做,便靠近倚着他的肩,静静听他絮絮叨叨说话。
“你大婚那夜吃了寓意百年好合的喜果,又早早换下喜服,如今我再替你换上,再替你放些喜果,当再陪我成一次婚。”
“但这次,就让我掀盖头吧。”
时至今日我都有些忘却了,但裴珩渊还记得仔细,我强按耐住心中酸涩,极力想阻拦他去抱我腐烂的尸首。
“裴珩渊,你谈情说爱的本事和你带兵打仗一样生冷坚硬。”
“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想说我便是对你有情,也无法宣之于口了;我笑自己有些天真,从没有死人对活人表达爱意的,可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原来百年好合,能是百年死后再好合的。
裴珩渊陪我的尸首坐了整整一夜,时而哭时而笑如同疯魔,待次日江时荷寻他用早膳,被吓得失态尖叫。
裴珩渊皱眉,冷声道,“你吵到她了,滚出去。”
江时荷是被亲爹强送回裴府的,她固然喜欢裴珩渊,但看出裴珩渊对我的疯魔程度显然不是她能够征服的,便跪着哭着祈求大夫人帮她。
可江府是我爹做主,尽管对江时荷宠爱有加,但在我爹听明白裴珩渊言外之意那刻,在他眼中江时荷这个女儿也作不得数了。
我嘲讽的笑她。
我亲爱的嫡姐啊,你不是很有把握得到裴珩渊么?不是信爹娘会将你捧在心尖尖上么?
可江时荷到底忘记,除了我与她,江府还有位真正受宠的嫡子江如飞。
而她如今是要在裴珩渊手底下讨活的,每日都唯恐惹裴珩渊不悦,用膳时她替裴珩渊布菜倒酒,将自己姿态放得极低,讨好的同他笑。
“裴郎,你答应阿娘说要给我一场婚事的……”
大夫人终究想盼她好,便以命施压给我爹,让我爹同裴珩渊商议,既是同为江家女儿哪怕是为妾室也该给场婚事,切莫失了体面。
裴珩渊捏着她的脸,嗤笑道,“很光彩么,你抢亲妹妹的夫婿外面已然人尽皆知,你甘愿为妾室还要什么婚事,若是办了岂不是叫人上门来笑话你?”
江时荷眼睛红了,眼泪渐渐溢出,“不是的,我没抢……裴郎,我是真心爱慕你啊,我是怕江漪死后你孤苦无依,有我侍奉在你身侧有何不好?”
“江漪她一个下贱胚子怎能比得上我,裴郎你信我定能把你伺候好的,你别将我赶回去好不好,若爹爹知道我回去了会打死我的!”
半月过去,江时荷早就等不及了。
她扑进裴珩渊怀中委屈的呜咽,裴珩渊唇角僵硬地顿了顿,却反常的没推开她,倒是意味深长的说了句“的确是不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