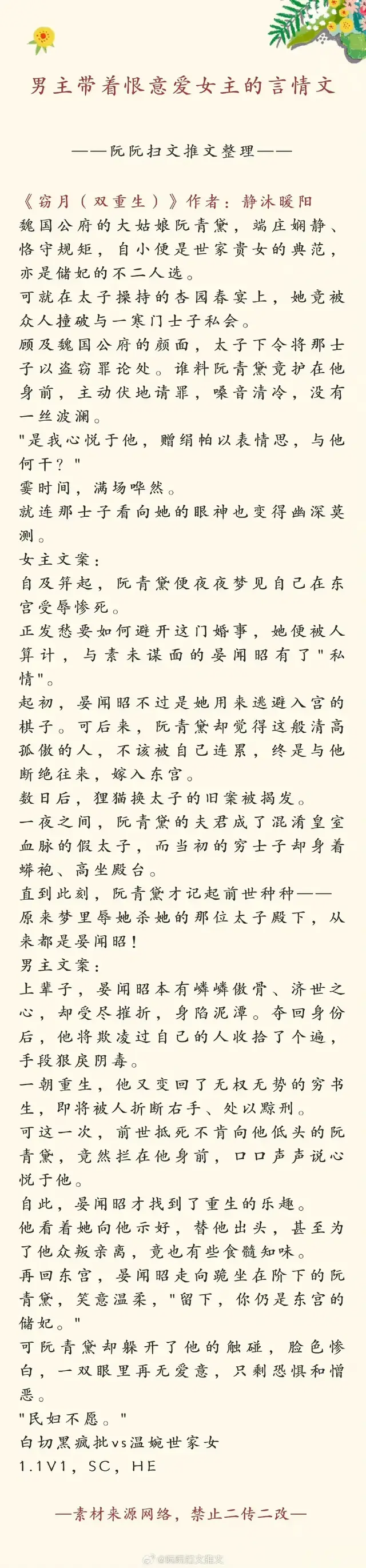文案:
于家花了二十年时间,全方位把二女儿于祇打造成京城世家小姐中的典范,但架不住她九十斤的纤纤玉体里养着八十九斤的反骨,剩下一斤全是心眼子。
于祗从小有三厌:一烦跳芭蕾,二不喜站规矩
三怕江听白。但她嫁给了江听白。
江听白时常看着自己明媒正娶的太太,精致又虚假,总有种在看俄国文学《套中人》的感觉。他也清楚,于祗心里放不下那个被逼远走的穷画家蒋玉轻,那是初恋。
后来蒋玉轻忽然回国,带着一身功成名就,可好几番试探下来,于祇的心意却好似变了。
她端端正正站在他的面前,对蒋玉轻来了个否定三连“你认为,在所有的年少心动里,属你最别具一格是吗?只要你一出场,我先生就落选?’“恕我直言,你被艺术捧得太高,晕头转向了蒋先生。”
“没事少看点这种疼痛文学,你已经不年轻了.早就过了做白日梦的岁数。”

片段:
于祗才从餐厅走出来没几步路。就看见江听白就把车横在了胡同口。
他懒散地靠在车门边,手里夹了支烟,不时就低头看一眼表。然后没什么耐心地蹙眉,隔着一长条胡同的浓稠夜色,于祗都能感受到他的烦躁。
有路过的,车技并不是那么溜的司机,生怕刮着他这辆限量版的深紫色库里南,能看出都小心翼翼绕着走。
但江听白大爷一样,熟视无睹的,不为所动地抽着烟。
有一挺直爽的大哥,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哥们儿,这不让停车,你还挡着道。”江听白听后,也只是淡淡看他一眼,表示他已阅,但这个意见不予采纳。
人大哥又好心提醒他说,“一会儿就有交警来贴单。”
江听白吐了个烟圈,“无所谓,让他贴。”
大哥小心地打方向盘,“您就非得停这不可吗?”
江听白看着朝他走来的于祗,“我媳妇儿是一瞎子,不显眼点她找不到。”于祗猜那位大哥是骂着娘走的。没有人能在江听白那张冰冷无情的嘴里保持精神正常。
她瞪了一下他,“你才瞎子呢你。”江听白说,“给你发那么多微信看不见,你还不瞎?”
“那是不想回,我还在生气,”于祗自己拉开车门坐了上去,“所以您到底是干嘛来了?”怎么每次他的示好都那么别扭?哄人不像哄人,接人也没个接人的样子,还连骂带损的。
江听白甚至有本事,把好端端一句我爱你,生生变成于祗的噩梦。
江听白在后座摸了一阵,拿出捧洋桔梗来,直接丢到了于祗的怀里,“给你。”
于祗被江听白这送花态度吓到,他还能再嚣张一点?怎么不直接丢到车窗外边儿去!她到底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别人的对象看起来都那么正常,而她要摊上江听白?
于祗矜持地清了清嗓子,‘送花的时候,要绅士一点。”“怎么?”
江听白挑了下眉,“我等你半个小时,给你买花,还不够绅士的吗?”
....够了。够够儿的了。
于祗一路上都憋着一口闷气。等快到小区门口时,前头有一辆奥迪堵着半天不进去,江听白不耐烦地猛摁了几下喇叭。
于祗把手撑在车门上瞧他,狗玩意儿长得是真好看。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像梅枝映在大雪地里的一点秾色,是折竹声中一续再续的冬夜清梦。脾气也是真大。
她抱紧了怀里的洋桔梗。这大约是他第一次等人,也是他生平头一回送花。就不和他计较算了。因为于祗没理他,也只好假装专心开车不说话的江听白,在这时候转过头。
他起初只想策略性地看一眼,于祗是不是还在生气,这很关键,决定了一会儿回家后,是不是该酝酿几句来道个歉。
所以他也没停留太久,只是扫了一下过去。但很快又回过头,因为他看见于祗正用一种轻挑慢摘的眼神,长时间地审视他。尤其她还喝了些酒,迟迟顿顿的目光里,有不自知的引逗在。
江听白被她看的不大自然,脸上微微发烫,他禁不得被于祗这样盯着。
他呼吸不畅地移开视线,故意找了点,料定于祗不敢接的话头,“这是新车,没避孕套。”于祗果然沉默了。
前头的奥迪也识相地让开了路。江听白刚踩下油门,就听见旁边传来一道晃悠悠的女声,“那还真挺遗憾的呢。”
江听白把车停在了院子里。
于祗还坐在车上不下来一双眼睛里氤氲着行行重行行的白葡萄酒香,目光一直追随着江听白。眼看着他下了车,绕到她这一边来给她开门,于祗光顾着看他,没提防手还架在车门子上。被他这突然一拉,猛地失去了支点以后,阳险些直直摔下来。
江听白伸手扶住她,略去方才的不自在,又开始跟她逗咳嗽,“我就有那么好看么?”他没想到于祗竟然点了头。
江听白发现她一温驯,什么都顺着他说,他反而就拽不下去了。他问了声,“自己能走?”
于祗有点不高兴的,在陆续开始发挥作用的酒精下撒起了娇,“这种时候你该抱我。”
江听白故作疑惑,“不是你说的要绅士吗?多问女士的意见。”
“嗯。”
她一双手绕到他脖子上,居然笑了,“但我刚才都违心夸你了,礼尚往来。”江听白把她捧了出来抱在手里,用脚关上了车门,于祗不动声色地往里挪了一挪。
江听白也没有戳穿她,把额头来来回回蹭在他下巴新长出来的胡茬上的小动作,反而把头低更下了些。
从院子到家门口还有一段弯路要走,得绕过一片湖,于祗常划的那艘小船就漂在湖面上。
江听白瞧上面堆满了枯叶,还有散不去的积水,尽量维持着平静,“改天请人来打理你这院子。”
于祗已经不老实地仰起了头,柔软的唇瓣离他的嘴角只差了一张薄纸,半张脸都贴了上来,反复不断徘徊在他的下颌处,她听不进去,脑子晕昏昏的,因为被抱着,人也很轻飘。只轻轻唔了一声。
江听白抱着她的手紧了紧,他能明显体察到自己的肩颈线此刻有多僵硬,他难耐地咽了一下,“这是在外面,没进门呢,你听不听话?”
于祗挨了训,一瞬间瞳孔睁得很大,凝视江听白,委屈且柔媚地点点头。
江听白没敢再看,他从没能在她这个眼神里全身而退,哪次都一败涂地。现在也一样,做成这条西裤的意大利顶级羊毛布料已经绷得很紧,绷得他发疼。
于祗在这上头没什么经验,但不妨碍她是一个好学生。她暗自揣摩着,江听白含咬她耳垂时的细微响动,也依样磨着他,“走快点儿。”
江听白险些脚下不稳,绊上仿青砖地面上一块凸起的石头,他后怕地深吸一口气。这一跤要摔下去,他在于祗面前丢的脸面,就再捡不起来了。等到他一脚带上门。
于祗人在混沌中,听见那咔哒一声关门的响动,像是得了赦一般,两双唇就急急地吻在了一起。
满地昏味中,江听白往后仰倒在沙发里,于祗半跪在他身上,她低声轻语抽泣着哭问他,“还不到?”
“这会子又哭什么?”江听白揉着她后颈,忍了忍,到底还是没吻上去,“不是你自己要么?”
于祗没挨住他这滚烫的气息。她低头吻他,“现在不要了。”“那可由不得你,不能好处叫你一人占全了,别人都不活了?”
江听白躲开了她的亲吻,怎么也不肯饶过她的,一下比一下要更里边。
于祗昏聩地靠在他的颈窝处,又迷迷糊糊的,再到后来一齐陷在了沙发里。江听白也渐缓了下来,他不疾不徐的,伸出玉骨扇似的指节,拨开她额前被薄汗濡湿的头发。
他嗓音沙哑着,“我们织织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想生宝宝?”
于祗的声音像随时会断,“现在就更、不想要了。”
“为什么是更?”江听白想听她回答,一再地放轻了动作,“怎么就更了?”“以前、不知道、你爱我。”
江听白恍惚笑了,黑暗中眼眸也清亮,深沉地望着她,“是,我早就爱你。”
于祗咬紧牙,逼着自己短暂忽视那股子难耐的疡热,说了一整句,“我要你就只爱我,不能多出个人来。”
江听白唇边笑意更浓,底下也越发失了控制,“就那么横?”“不喜欢?”
于祗的鼻尖抵着他眼尾,轻轻在上面落下一个吻。天知道他有多喜欢呐。这个卸下面具,自私、口娇蛮的于祗,温软里带一点强词夺理,他不要太喜欢。江听白终于舍得结束这一场流离转徙的征讨。
他捧着于祗的脸细细吻着,“我好喜欢。”
于祗刚一洗完澡被抱出浴室,不过几步路,就靠在江听白怀里睡了过去。他把人放在床上,轻啄了下她的唇,“睡吧。”江听白披了件黑色的浴袍走刚才光顾着抱于祗了,有份文件落在了车上。他指尖掐着一支烟往车库边去,却意外听见一声极不合时宜的,“江总?”是蒋玉轻。
他手里提瓶酒,“刚才在大门口接个电话,好像挡了您路。”然后又双手捧上,“给您和夫人赔罪。”
江听白皱一下眉头,他把嘴边刚要点的烟又取下来,仍旧掐回了掌心里。他肃声,“你住这。”
江听白根本不屑接他这瓶酒,直接跳过疑问阶段下了结论。蒋玉轻听不出他的惊讶,还是那种淡漠口气,天生一副上位者的姿态。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是啊刚搬来,这艘小船还在这里?”
没等江听白开口,他就开始追抚往昔,“以前您夫人还读大学的时候,受不了住寝室,常带我回这里,我们还在这一片湖里划过船。您知道,我那时候还是个穷学生,哪里见识过院子里还能划船的别墅,能交上这样一个女朋友,祖坟冒青烟呐。”
江听白听着他这一番触景伤情的回忆。
蒋玉轻这小子,一口一个的您夫人,满嘴的尊敬,心里不知怎么脏她。
江听白靠在车边微微勾着唇,手里掐着烟,也不妨往他的痛处踩实下去。
他凉笑一声,“有空就去白云寺上柱香,如果没有于二,不拿于家的钱,你也去不了巴黎学美术。”
蒋玉轻握着酒瓶的手蓦地收紧。原来这帮公子哥儿这么看他。他还以为,他能和于祗在一起,他们这群人至少会敬重他们一心一意,起码认为他们相爱。没想到在江听白口中,他完全就是个靠着于家才能读上书的,一个带着目的接近于二小姐的狗崽子。可明明不是这样的。
蒋玉轻来之前,硬撑起来的那点优越感,那点他曾得到过于祗真心的强烈的胜负心,被江听白三言两语一说,顷刻荡然无存。
但又有什么关系,江听白和于从声一样,从来瞧不起他的。
蒋玉轻低头笑了下,“确实,我一直很感谢于祗。她对我很好,总是鼓励我不要因为身世就看轻自己,还说……”
江听白冷冷打断,“我看上去这么闲?”
话里十足的轻蔑叫蒋玉轻不禁抬头看他。
江听白沉声道,“很抱歉蒋先生,我太太一个人在房里睡觉,她离不得我的。”
他那个表情一点也不似假装,只是在陈述事实,一个在于祗口中听过的事实。
她说,“我说的晚不是年纪,是我已经,无法离得开我丈夫。”蒋玉轻笑得很僵,“真希望你
们两口子的感情,永远都会这么好。”
江听白听着他这句假模假式的祝福刺耳极了。不像愿景,倒似诅咒。
“我们夫妻如何,无需你来操心,他微眯了一下眼眸,挑起下巴看蒋玉轻,“倒是你在欧洲那套,最好是不要带到北京来,当然想吃牢饭除外。”
突然被言中要害的蒋玉轻,左手一滑摔碎了那瓶好酒。五月和暖的夜风吹在他身上也
变得如坠冰窖般的冷。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他一定在诈他。蒋玉轻尴尬地应他,“江总在和我开玩笑。”
江听白留给他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我从不开玩笑,尤其,不拿国法玩笑。”
转过身时,江听白疏狂地轻笑了一下。之前他只是猜测,蒋玉轻一个出道没几年的年轻画家,哪里来这么大的名气和成就,他的画真就好到了欧洲上流竞相追捧的程度?里头八成有不为人知的勾当,听着那瓶酒叮咣落地,江听白在心里一捶定了音。
蒋玉轻有些慌乱地拿出手机打给他的助手,“最近有人去巴黎问我的事吗?”
安森说,“没听说。”
蒋玉轻略略放了些心,又问,‘画展进行的怎么样了?”
“很顺利,主要宾客都已经收到了邀请函,当天成交量应该在五个亿左右。”
蒋玉轻挂了电话。成交五亿,到他手里扣除税金,再原封不动转回去。所谓艺术家也不过是个工具。
江听白走回去的路上,将那根已经被他掐得软塌下来,露出暗黄烟丝的烟丢进了草丛。
怎么可能不介意?关于蒋玉轻和于祗过去那一段,什么常带他来这,又是两个人一起在湖里划过船。他介意的要死。
但不能在蒋玉轻面前流露出一分一毫,叫这孙子觉得自己有任何一点优势。要跌也在他家于二面前跌份,在蒋玉轻面前算怎么回事儿?
江听白把文件随手扔在了沙发越想越气,自己搬来这边这么久,都还没有跟于二划船!她提都不提。
她只跟初恋男友划是吧?他年纪大点儿就不配吗?江听白坐在客厅里抽完两根闷烟,含着一口不上不下的恶气回了卧室。
他瞥了眼床上的于祗,作为对她的惩罚,今天晚上不抱她睡觉。除非她哪天主动邀请他一起划船。
江听白掀开被子,放轻手脚躺在她身边,很快于祗靠过来。她的声音软的像一蓬烟,“去哪儿了?”
“拿、拿份文件。”
江听白揉了揉鼻梁,他把头枕在手上没动,刚立的flag还不能倒,但音调已经不自然,“你怎么还没睡?”
于祗又来贴他胸口,手扒上他的腰,“老公不在哪睡得着。”
“嗯。”
江听白在暗夜里牵了牵唇角,手放下来,把她松松搂在怀里拍了起来,“我抱你睡,我拍着你。”
于祗还嫌他,“你轻一点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