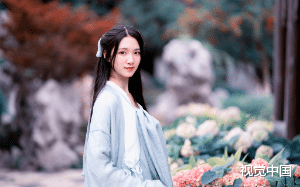新帝在登基的后一日占有了我,说会一世对我好。
我始终顶着太妃的名头,尽着妃子的义务。
一朝有孕,身边亲近之人全变作吃人的豺狼,我没了孩子,被幽禁在深宫,一夜里死在枯井里。
半年后,新帝休了皇后,封我为后,亲自扶着棺椁,泪洒千里,送我回家。
罪己诏里他好似深情款款,有诸多无奈。
史官却给他一个“厉”字做谥号。
因他是一个无情无义、暴虐无亲的亡国之君。

1.
皇帝死了。
我看着他七窍流血、死不瞑目地倒在床上,吓得失手打翻了放在床边的一碟奶糕。
我跌坐在地上,听见身边传来脚步声,只看见面前出现一双绣工精巧华丽的鞋。
视线上移,看见身为皇贵妃的岚姐姐对着死去的帝王露出一抹复杂的笑容。
她的贴身大宫女向蕊捡起洒落一地的奶糕,而岚姐姐坐在皇帝床边,用手帕拭去他脸上的血痕。
做完这一切,两行清泪从她脸上滑落,她悲伤地对着守在外面的太监宣布:“皇上,崩了——”
宣布完这个消息,她在原地失神良久,好一会儿才想起我,伸手把我拉起来。
语气是如常的温柔,令人心安:“妙音,吓到了吧?没事的,回去睡一觉就好了。”
她拉着我的手,走出皇帝的寝殿。
她的养子正雅站在门外,嚎啕大哭。
在我们经过他身边时,姐姐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说什么话。
在离开的时候,我总感觉有一道目光跟随着我。
死死地盯着。
使我想起,在将军府看仆人喂狗时,那些垂涎三尺的恶犬眼里的凶光。
2.
国丧第二日,我发现我发不出声音了。
我穿着丧服,急忙跑进岚姐姐的宫中,对着她一通比划。
岚姐姐脸上露出震惊和心疼,急忙为我宣了太医,握着我的手,细细安抚我。
太医来检查,说我是中了毒,但是因为这毒下得太阴险,我捡回一条命已是侥幸,我的嗓子是没有办法救回来了。
岚姐姐下令彻查我的宫人,最后查出是我的贴身宫女喜儿在我喝的茶水里下了毒。
喜儿被两个太监架着,哭得梨花带雨。
她拼命摇头,发髻凌乱,说不是她,请皇贵妃娘娘明查。
姐姐对付与她作对的人从不心软拖拉,下令杖毙,还要伺候我的宫人都看着。
我心有不忍,想拦着他们行刑,岚姐姐却拉住我的手,语气强硬:
“妙音,证据确凿,不要心慈手软。”
我知道姐姐是为我好。
只得闭上眼睛,不去看庭中血肉横飞的惨景。
喜儿与我,虽称主仆,情同姐妹。
宫人来报,说喜儿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姐姐拿出手绢按了按自己鼻翼,挥手让他下去。
离开姐姐宫里,我看见他们拿一张草席盖着喜儿血迹斑驳的身体,我看四下没有其他人,拿出一些金银珠宝塞到他们的手里,又放了一只沉甸甸的金钗在草席里面。
没了喜儿,我都不知道这宫里的漫漫长夜该怎么熬。
还好岚姐姐一直都在。
我入宫以来,岚姐姐身为一宫主位,对我多有照顾。
我笨嘴笨舌得罪了皇后或者其他宠妃,岚姐姐都会挺身而出保下我。
弹琴、跳舞、怎么更讨皇帝欢心,岚姐姐都一一教我。
对于她,我永远不需要怀有戒心。
3.
守孝二十七日之后,大臣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奉先帝遗诏,让新帝登基。
新帝不是皇后所出的三皇子,而是十五皇子正雅。
缠绵病榻许久的皇后,在先帝驾崩那日也随着一同去了。
前朝后宫,都是岚姐姐母子把持,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岚姐姐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后,我们其余的妃嫔也成了太妃,有皇子的太妃出宫住在王府里。
我还没有孩子,留在了宫中。
我原本以为我迁居的宫殿会比较清静,却每日都见到门前宫人往来熙熙攘攘。
我出去走了一圈,才知道我所住的得宜宫离陛下的寝殿很近。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一日晚上我沐浴更衣后,被人从背后按在了床榻上。
我看不到那人的脸,拼命挣扎起来,可我不会说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上的寝衣被剥下。
室内除了蜡烛的偶尔发出的毕剥声,就只有我抽泣的声音和那人的粗喘。
他不满这样的安静,在我耳边说:“妙音,我爱死你了,我从见到你的第一面,我就好喜欢你。可惜你从前是父皇的女人,不过你现在是朕的了。”
我昏昏沉沉的脑子里闪过了正雅的样子。
正经的样子没见过几次,次次都是他在我宫里狼吞虎咽的样子。
他生母地位低又去得早,宫人疏于照顾他,很少让他吃饱饭。
我十三岁入宫,年纪小,贪玩又爱吃,先帝宠爱我,御膳房的好东西常常会送到我宫里。
别的妃子想和我交好,也会让小厨房做好吃的给我送来。
那些美味佳肴我常常吃不完,本来是给侍女吃,侍女却常说有老鼠偷吃。
后来她们半夜守株待兔,逮住了正雅。
那时正雅还没被岚姐姐收养,我就用好吃的喂了他一年。
后来正雅在姐姐膝下,每回进宫,都会来看我。
我拿出最喜欢的玉兔奶糕招待他,他一边吃,一边看着我。
年轻英俊的面容,常常看得我面红,我举起团扇,挡住自己的脸,挡住他的视线。
正雅将我翻过身来,指腹揩掉我脸上的泪。
年轻的野兽吻住我的唇,撑开我捏着床单的掌心,强硬地与我十指紧扣。
向我承诺:“你偷偷地跟着我,我会一世待你好。”
4.
我是先帝的妃子,没有一儿半女,想必史书也不会在我身上浪费笔墨。
可如果正雅要纳我,让我做第二个武媚娘,后世一定会对他有诸多口诛笔伐。
我和他,都希望他能在青史上有个好名声。
好在我对位份并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是一双爱着我的眼睛。
只要他在对我好,他让我感受到爱,我就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我本是草原的女儿,七岁那年大将军赵赫带领铁骑攻打我的部族,逃亡时我意外跌落下马,摔坏了脑袋,正正摔在赵赫的马蹄下。
马蹄高高扬起,马儿发出嘶鸣。
赵赫翻身下马,向我走来。
他用剑挑起我的下巴,眼里有惊艳之色。
随后我被他捡回将军府中,当做一个讨人欢心的小玩意养起来。
因为歌喉动人,可召唤百鸟来朝,起初叫我“凤凰儿”,后来唤我“妙音”。
无人再记得我的原名塔娜。
我十三岁,先帝到行宫避暑,赵赫借机把我献给先帝。
春光灿烂,芳菲盛开,我在花林间唱歌,身边百鸟宛转和鸣。
先帝驻足良久,待我歌毕,当即封了我为美人,亲自拟了封号为“婉”。
我傻乎乎、不识字,没有家人,天真又爱娇,先帝宠爱起我没有一点负担。
可是先帝年纪太大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在和爷爷玩耍。
见到正雅,我才感觉到少女心动的羞涩和甜蜜。
正雅总是悄悄地来,天不亮就急匆匆地走。
走之前,也不忘说一些山盟海誓的甜言蜜语。
这样的生活,过了半年。
我越来越贪睡,身子也胖起来,胃口有时好有时不好,我只当是没休息好,并不在意。
我还是常常去岚姐姐的宫中,虽然不能陪她说话,但是和她一起做一些手工,也是打发时光的好方法。
但那日,一切突然变坏了。
也许是吃坏了,我伏在榻边,干呕了一阵。
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看着岚姐姐,她当上太后后,已经很少会露出很剧烈的情绪。
她招手,让向蕊去唤太医来。
太医让我伸出手,为我诊脉,小心翼翼地藏起脸上的震惊,在岚姐姐耳边悄悄说了什么。
岚姐姐却突然执起桌上的杯子摔在地上。
白色瓷片溅得到处都是,太医和宫女都立刻跪下,不敢去瞧岚姐姐的神色。
我怯怯地扯了一下她的衣袖,岚姐姐阴沉的脸色在转向我的时候已经散去阴霾,只是有些担忧地看着我说:
“妙音,太医说你中邪了,你别怕,我马上安排人给你驱邪。”
我点点头,表示顺从她的安排。
岚姐姐让我先回宫休息。
晚上正雅来了,见我愁眉苦脸,用手指展平我眉心的皱纹,问:“怎么了?”
我不能回答他,只好做一个诊脉的动作,又往脖子抹了一下。正雅大惊失色,又把太医叫来。
这个太医并不是下午在姐姐宫里的那个,不爱说悄悄话,衣摆一掀跪下来,直接说:“回陛下,婉太妃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
他面露难色,正雅最不耐烦这些说话说一半的人,把盘玩着的手串放桌子上一敲,责问:“只是什么?”
“只是……有喜了。”
这太医真胆小,说句话的功夫,脖子上的冷汗都滴在了地上。
我不知道有喜是什么意思,但“有”是好字,“喜”也是好字,只当他在说我的身体很健康。
正雅沉吟了一会儿,挥手让太医退下,让我先去睡。
我隔着帘子看他,他坐在榻上沉思,没一会就走了。
我心里莫名觉得不安。

5.
姐姐安排的人,穿着奇装异服,脸上红红绿绿画了一些奇怪的花纹,手上拿着男子手臂粗的木棒,让我看着无端感到害怕。
我往姐姐身侧缩了缩,姐姐却把我的手从她的袖子上扒下来,往后退了两步。
向蕊上前来扶我,她面无表情的样子令我感到很陌生。
“太妃,请吧。”
向蕊半拖着我走到那群奇怪的人中间,随后轻盈地闪身离开。
我可怜巴巴地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岚姐姐,她转开了脸,看着院中盛放的花枝。
“嘿——呀——”
那些怪人将手中的木棒重重锤在地上,口中唱着我听不懂的奇异歌谣,围着我转起圈来。
突然,我的后背被重重打了一下,疼得我向前扑倒,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第二棒已经侧着朝我打来。
这一棒打在腰上,我像只虾米把自己蜷缩起来。
他们仍在围着我的圈子越缩越小,到最后我的眼前全是他们身上晃动的衣摆和佩饰。
叮铃铃,叮铃铃。
那些佩饰晃起来,声音像招魂的铃铛。
他们的声音近在耳畔,脚下扬起的尘土扑到我的脸上,手里的木棒左一棒右一棒地击打着我的身体。
我被打得没有办法站起来,只能咬着牙,死死地护着我的肚子,眼泪不停地流。
姐姐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穿透耳边那些恶魔低吟来到我身边:“妙音,别怕,只是为了赶走你身上的邪祟,它会化作一滩血水从你的身体里面流出来,到时你就健康了,干净了,别怕,乖啊。”
姐姐总不会骗我的。
听着她一声声地说“别怕”,我也不再挣扎,只希望这邪祟能早点离开我的身体,让这个驱邪仪式早点结束。
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像一面鼓,被不断敲打着,姐姐在一旁说:“你不要一直缩起来,你要张开你的身体,你的肚子才是邪祟所在的地方……”
她的话还没说完,一声“住手”平地惊雷一样响起来。
那些怪人立刻收了手,跪在地上,说着皇上万岁。
正雅大踏步过来,把我从地上抱起来,我立刻揪着他的衣襟,想像一条泥鳅一样钻进他的怀里。
脸颊紧紧贴着他的胸膛。
我感到他的胸腔震动,听见他怒气冲冲地下了指令:“借鬼神之名行害人之事,通通杀无赦!”
那些人伏在地上磕头,一声连一声喊着陛下饶命。
正雅并不理他们,抱着我就要走。
但姐姐站在原地,沉沉地叫他:“皇帝。你可想好了,这孽障留是不留?”
“……母后,再怎么样,方法都有的是,您何必这样极端?”
正雅没有与姐姐说太久的话,只囫囵回了一句,就抱着我回宫。
路上,他摸着我的脸,告诉我:“你的肚子里有个小孩子,他不是邪祟,即使他的出生不被期待,我仍然希望你和他都好好的。”
6.
回到宫里,太医早就候着了。
正雅把我放上床,他们就过来诊脉,大大松了一口气,只说是皮肉伤,受了一些惊吓,胎像有些不稳,吃几剂药就好了。
从那以后,正雅限制了我和姐姐往来。
我也实在想不明白,一向待我好的姐姐,为什么坚持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邪祟。
想不明白,就不去想。
我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但正雅却很少来看我了。
我每天坐在窗边往外面看,只能看到窗外的竹影,行走的宫人。
新来的贴身宫女沛儿告诉我,正雅的宫中有一位越贵妃也有了孩子。
皇后前不久刚从掖庭里提了一些人充实后宫,皇上得和这些人一起睡觉,以保子嗣绵长。
肚子里的小孩子总踢我,我想它可能是想它父亲了,就让沛儿为我准备了玉兔奶糕,我要去见见正雅。
刚走到御书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一堆重物落地的声音。
正雅在里面咆哮着:“早不旱,晚不旱,偏偏是战事吃紧的时候大旱!”
里面有个人说:“陛下,天道不爽,事、事、事在人为啊。”
“听监正所言,是朕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吗?”